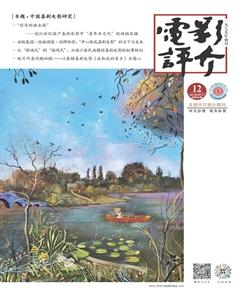敘事解構(gòu)與角色中介
劉爽

1895年12月28日,在法國巴黎卡布新街14號的咖啡館中,盧米埃爾兄弟使用其發(fā)明的“活動電影機”首次公映了短片《工廠大門》(路易斯·盧米埃爾,1895),宣告了電影的誕生。120余年后的今天,當(dāng)立于電影發(fā)展的歷史高峰回溯其發(fā)展歷程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作為科學(xué)技術(shù)的產(chǎn)物,電影的藝術(shù)屬性是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論爭中逐漸被發(fā)掘和賦予的,而電影真正意義上的誕生,不僅是指一部電影被創(chuàng)造出來,更是伴隨著一部電影“公映”“被觀看”。直至今日,電影已然從一種純粹的“工業(yè)產(chǎn)物”蛻變?yōu)橐环N集“工業(yè)”“商業(yè)”“藝術(shù)”于一身的綜合體,其審美屬性早已不言而喻。在以電影為中心的審美關(guān)系中,作為審美客體的電影,始終作為觀眾的審美對象存在,但梳理電影的發(fā)展歷程,電影“始于視覺,卻終于情感”的歷史走向躍然紙上,它作為藝術(shù)本身的獨立性也漸漸凸顯出來,其美學(xué)價值并不完全依賴于觀眾。這種矛盾性,暗含著對“對象性審美”的實踐與探討。如果說“電影放映術(shù)”是電影走向觀眾的技術(shù)媒介,那么在電影創(chuàng)作的實踐中,電影故事和角色本身逐漸承擔(dān)起了這一美學(xué)功能。在影史長河中,電影作品通過不同程度的實踐,不斷強化與觀眾間的審美關(guān)系,代表性作品不斷涌現(xiàn)。
一、審美對象的可能性及其電影實踐
1953年,法國美學(xué)家杜夫海納的著作《審美經(jīng)驗現(xiàn)象學(xué)》發(fā)表,標(biāo)志著杜夫海納理論體系登上歷史舞臺。現(xiàn)象學(xué)是杜夫海納理論體系的基礎(chǔ),也成為他美學(xué)研究的一種方向。杜夫海納將目光投向現(xiàn)象學(xué)所研究的人的意識界的經(jīng)驗本質(zhì),提出了“審美經(jīng)驗”(l'experience esthe tiqe)這一概念。審美經(jīng)驗的獨特性在于情感的先驗性,也就是說先驗性即是審美主體的確定性,又是審美客體的確定性,先于主體和客體而存在。[1]以此為切入點,杜夫海納對審美過程進行了闡述。其中最具有創(chuàng)見性的,當(dāng)屬其對“審美對象”的闡述。杜夫海納一方面認(rèn)為“審美對象”具有泛型,不僅只有藝術(shù)作品能成為審美的對象,其他自然物和人工產(chǎn)物都能成為審美對象;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一般物是先天的“審美對象”,藝術(shù)作品也并不都是先天的“審美對象”。從可能性上,他認(rèn)為相對于一般性的人工制品而言,自然物與藝術(shù)作品更容易成為審美對象,“真正的對立在于自然物和人工物之間,絲毫不在于自然與藝術(shù)之間。”[2]這是因為自然物和藝術(shù)作品從本質(zhì)上具有根本創(chuàng)造性,它們不同于一般的人工制品,不被人類已有的范疇所馴化,更不為其所束縛。相反,它具有解構(gòu)和打破已知范疇的能力,將審美主體引向無范疇的觀看,喚起審美主體前所未有的審美感受。自這一點可以看出,杜夫海納對“藝術(shù)品”的界定更為嚴(yán)苛,一個藝術(shù)作品要成為一個“藝術(shù)品”,它需要具有超出受眾認(rèn)知范疇的獨立性和創(chuàng)造性,并且要擁有足以引領(lǐng)受眾審美體驗的吸引力。杜夫海納將高層次的藝術(shù)和自然物并列,側(cè)面強調(diào)了藝術(shù)品的“自發(fā)感”,所謂“渾然天成”大抵如此。
據(jù)此,當(dāng)我們重新審視電影的開端,無論是《工廠大門》還是《火車進站》(路易斯·盧米埃爾,1895),亦或是《水澆園丁》(路易斯·盧米埃爾,1895),它們的形式不過是簡單的片段記錄,很難說創(chuàng)作者存在什么主觀的藝術(shù)性構(gòu)思,因其不符合一般評價體系中對“藝術(shù)性”的界定,所以一般來說并不歸于藝術(shù)電影一類。但從杜夫海納的理論來看,正是科技賦予它的創(chuàng)造性和吸引力構(gòu)成了它“藝術(shù)品”的特性。首先,就具備了“審美對象”之可能。將杜夫海納的理論引入電影框架,藝術(shù)電影的重要性就被凸顯出來。按照杜夫海納的理論,在電影工業(yè)的固定框架中按固定程式制作出來的類型化商業(yè)電影,絕大部分也就只是“審美客體”,不能成為“藝術(shù)品”,更不能成為“審美對象”。無論是從形式、劇本、鏡頭語言,還是在主旨上,這些作品都陷入套路化的藩籬,無法超越觀眾的認(rèn)知范疇,也就無法主導(dǎo)審美過程。這一點,類型電影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比如幾年前興起的青春片熱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中國臺灣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陳正道,2011)為開端,國產(chǎn)青春片成為新的市場熱點,愛情、懷舊、青春、遺憾等元素,被納入到一部青春電影的文本里。數(shù)年內(nèi),《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趙薇,2013)、《同桌的你》(郭帆,2014)、《匆匆那年》(張一白,2014)、《左耳》(蘇有朋,2015)等帶著“青春疼痛”印記的青春片涌入市場,但其創(chuàng)作千篇一律,極少出現(xiàn)具有吸引力的樣本,使觀眾無法真正得到審美體驗。從觀眾審美層面分析,類型片之“類型”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建立群體電影的共同藝術(shù)性,也會在趨同中,迅速消解群體電影的獨特性;既能打造觀眾的“期待視野”,也能在套路中消磨期待的可能。
二、審美對象的必然性與藝術(shù)電影發(fā)展
杜夫海納又從必要性方向闡述了藝術(shù)作品與審美對象之間的區(qū)別。他認(rèn)為,兩者的區(qū)別在于非感性對象和感性對象之間的區(qū)別。未進入審美經(jīng)驗中的藝術(shù)作品是非感性的存在,進入審美經(jīng)驗中的藝術(shù)作品是感性的存在:審美對象就是“一種感性要素的聚結(jié)”“感性的頂峰”“燦爛的感性”[3]。換言之,一件藝術(shù)作品需要放在審美的范疇中,完成從“非感性”到“感性”的轉(zhuǎn)化,才能成為審美對象,“審美過程”才能隨之實現(xiàn)。在這個過程中觀眾的立場觀點要比作者的立場觀點更為重要[4]。可以想象,在1985年的咖啡館中,看到這些電影的觀眾們所受到的沖擊力——新奇、激動,人們的心緒被前所未見的畫面牽引。對于觀影者來說,它沒有先例,沒有比較級,由此它不屈從于任何當(dāng)時的評價體系。也正是在“被觀看”這一過程中,它自身的魅力得以顯現(xiàn),并喚起觀眾的情感體驗,至此才真正成為“審美對象”。在“觀影”這一審美行為中,電影的放映和觀眾觀看是共生的、同時的。在這個過程中,電影和觀眾兩者間的關(guān)系,是一種互動的、共同的“情感氛圍”的營造和傳遞。杜夫海納揚棄了主客間的二元對立,視情感先驗為關(guān)聯(lián)創(chuàng)作者、欣賞者與審美對象的先在條件。這種先驗的情感特質(zhì)處于對象世界的根源之處[5]。從這個意義上考量,電影始終是處于被觀看的狀態(tài),它生來被觀看,也必須被觀看,無論是商業(yè)電影還是藝術(shù)電影,它們的不同界定,歸根究底是處于不同的受眾群的觀看中,觀眾對不同作品作出反應(yīng),從而凝結(jié)成共通的情感共鳴和群體意識,以此反向提煉出電影的屬性。盡管電影天生被觀看,但卻不是都具有能和觀眾達(dá)成審美橋梁的感性內(nèi)核。
值得注意的是,杜夫海納雖然強調(diào)審美對象與藝術(shù)作品的根本區(qū)別,但他并不是傳統(tǒng)審美觀的擁護者,不認(rèn)為觀眾對于審美客體的審美行為是一種基于自身經(jīng)驗的再創(chuàng)造,而是認(rèn)為審美對象,只是藝術(shù)作品在審美感知中會必然性地呈現(xiàn)出的一種感性狀態(tài)。也就是說,審美對象并不需要欣賞者主觀地創(chuàng)造抑或補充,而需要的是審美感知的一種感應(yīng)與見證。審美對象已然是以一種超脫于欣賞者的知覺的物的形態(tài)而存在,其所要求的不是一種可能或“應(yīng)在”,而是已經(jīng)存在之物的顯現(xiàn),亦即一種“呈現(xiàn)的存在”。[6]由此可見,杜夫海納強調(diào)審美對象的獨立和完整,強調(diào)審美對象所具有的不服從欣賞者的改變的必然性,這點也被研究學(xué)者看作是審美對象最深刻的特性。筆者認(rèn)為,這種觀點,正是藝術(shù)電影存在的理論支撐。誠然,電影是伴隨著商業(yè)行為誕生的,在之后的發(fā)展歷程中,電影的商業(yè)性也在不斷被強化。從鎳幣影院到今天的院線系統(tǒng)性經(jīng)營,大眾認(rèn)知中的電影,似乎始終要放在市場的視域中被審視。但事實上,在既定的電影框架之外,永遠(yuǎn)有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反叛性的藝術(shù)電影存在,它們其中的一大部分,并不能進入市場,或者說并不能用市場表現(xiàn)來證明自身的價值。從中國電影來看,婁燁、畢贛等導(dǎo)演,都是在藝術(shù)電影界卓有成就,但其作品在主流商業(yè)市場的表現(xiàn)卻不盡如人意,比如2014年,婁燁電影《推拿》(2014)上映,最終票房僅定格在1285.7萬元,而當(dāng)年的票房冠軍《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馬克·沃爾伯格,2014)最終以19.6億元收官。藝術(shù)電影像是在體系外探索,又像是在夾縫中生存。它們的受眾不是,或者說還不是習(xí)慣了商業(yè)電影節(jié)奏的電影市場主流消費者,但藝術(shù)之所以能成為藝術(shù),正是因為其藝術(shù)獨立性,受觀眾審視,但不被觀眾馴服。這點時刻提醒著電影創(chuàng)作者們,與其追逐市場熱點,不如挖掘自身的獨特性魅力,保持藝術(shù)特性。令人欣喜的是,現(xiàn)今國內(nèi)外電影市場已經(jīng)逐漸建立起了“商業(yè)院線-藝術(shù)院線”雙軌平行的院線體系,藝術(shù)和商業(yè)將在電影中進一步共通共融。
三、電影創(chuàng)作中對象性審美的探索與實現(xiàn)
審美客體之所以成為審美主體的現(xiàn)實客體,既在于審美客體的自身藝術(shù)與美的屬性,更在于審美過程中,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適應(yīng)性。如果說觀影的審美過程是一個產(chǎn)生于“審美主體-觀眾”和“審美對象-電影”之間,是二者感性世界的融合和互動。作為電影來說,如何傳遞自己的情感內(nèi)核給觀眾,對于觀眾來說,通過何種方式感受到電影的情感,這就是電影實踐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就引入了一個“審美中介”的問題。如果沒有審美中介,沒有審美中介與審美客體的互動,審美客體自身美的屬性仍然是處于“自在”的狀態(tài)[7],如此一來,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相互作用的審美關(guān)系難以建立。在審美中介領(lǐng)域,審美中介的實現(xiàn)往往透過一定的審美感官、審美觀念、審美的思維方式、審美的物態(tài)工具、審美的實踐活動等。電影是怎樣實踐這一點的呢?相比其他藝術(shù)形式而言,電影有一個優(yōu)勢性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這個結(jié)構(gòu)就是“電影故事”。這種動態(tài)的、流動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以現(xiàn)實世界為基礎(chǔ),與現(xiàn)實世界互聯(lián)。在電影故事之中,角色就是其中的人類。二者相乘,包容了一切“感官”“觀念”“思維方式”“物態(tài)工具”和“實踐活動”,也就自然建構(gòu)起了審美的橋梁。
深究起來,觀眾在觀影中的感性體驗大概經(jīng)過這樣一個過程:“與故事中的角色產(chǎn)生共情—體會到由角色傳遞的情感被—電影的故事打動”[8],這也成為了電影實現(xiàn)情感傳遞的邏輯鏈條。觀眾作為審美主體,是一個作為人的個體,電影創(chuàng)作者們試圖以此為突破口,建立兩個世界“一對一”的情感鏈接,主觀敘事成為最常見的方法:通過第一視角或第二視角的人物敘事引領(lǐng),首先了打破了傳統(tǒng)敘事的視角,消解了對觀眾而言,由此帶來的敘事壓迫感,更重要的是,精準(zhǔn)地促進了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的“角色代入”。2021年春節(jié)檔期表現(xiàn)優(yōu)異的《你好,李煥英》,就是成功案例的代表。電影始終以女兒“賈曉玲”的視角展開,開篇一段濃縮式的“母子關(guān)系”回顧選擇了第一人稱自白,把這一人物放在了情感世界的入口處,帶領(lǐng)觀眾進入電影的感情世界。誠然,這部電影的故事來源于創(chuàng)作者真實的人生體驗,這樣的敘事方式和角色設(shè)置有其必然性,但從這部電影的目標(biāo)受眾來看,“子女—父母”這一社會倫理框架下涵蓋的受眾群,幾乎已經(jīng)達(dá)到了最廣面,在這一前提下,創(chuàng)作者選取“女兒”這一視角,無疑可以實現(xiàn)更精準(zhǔn)的“目標(biāo)”,可以說是直接將角色的視角轉(zhuǎn)動到與觀眾的情感視角重合的某一角度上進行輸出。
當(dāng)然,電影作為藝術(shù)作品,是處于群體觀影的范疇去考量的,觀影這一其審美過程也是群體性的。單一角色的中介牽引作用有限,在單個故事里的情感選擇也較為純粹,在“一對多”的傳播路徑里很難最大限度地輻射到目標(biāo)受眾面,于是多角度敘事就成了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新選擇。其實多角度敘事所尋求的角色帶入性,是上文中提到“一對一”主觀敘事的變形,電影特殊的非線性剪輯技術(shù),賦予了多角色多視角平行敘事的可能性。在此類實踐中,觀眾不是從角色的單一視角來進入電影的感性層面。審美對象的全貌,是由不同角色的故事共同構(gòu)成的。以具體作品來看,2014年的故事片《親愛的》(陳可辛,2014)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個關(guān)于“拐賣兒童”的故事里,影片不僅從丟孩子的父母一方去敘述故事,也從“養(yǎng)孩子”的一方去敘述故事。兩個方向相互補充,打破了二元對立的情感結(jié)構(gòu),建構(gòu)了完整的情感體系,也給予觀眾更為多元的感性體驗。《找到你》(呂樂,2018)中,同樣可見這樣的雙面角色設(shè)置,放在現(xiàn)實世界中,這樣的設(shè)置無疑更為合理,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無法判斷觀眾是將自己代入孩子被拐走的精英律師,還是將自己代入歷經(jīng)生活苦痛,選擇極端方式作為情感出口的農(nóng)村保姆,她們代表了不同階層的人生體驗,但從根本上卻維系著作為母親的情感共鳴。對于觀眾而言,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別性,在審美群體中發(fā)掘出作為個體的審美經(jīng)驗,加以強化。
結(jié)語
如今,電影已是一種兼具審美性與大眾性的藝術(shù)形態(tài),已成為人們娛樂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受眾群不僅逐年擴大,也在不斷分化。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為應(yīng)對不同的形勢和場景,電影的觀影形式也愈發(fā)趨于多元化。我們要清晰地認(rèn)識到:電影的藝術(shù)地位一方不斷被藝術(shù)作品所鞏固,被大眾所確認(rèn),一方面,又不斷被沖擊和審視。然而,總有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具有感性吸引力的電影藝術(shù)作品,作為審美客體,在以觀眾為指向的放映中引發(fā)觀眾的審美體驗,并在這個過程中彰顯自己的美學(xué)特質(zhì)。故事是他們的空間,角色是他們思緒下的活物,將獨立的藝術(shù)和情感傳遞給觀眾。
參考文獻:
[1][法]M.賽松.杜夫海納的美學(xué)思想[ J ].王珂平,譯.世界哲學(xué),2003(02):71.
[2][4][6][法]米蓋爾·杜夫海納.美學(xué)與哲學(xué)[M].孫非,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5:44,52,65.
[3][法]米蓋爾·杜夫海納.審美經(jīng)驗現(xiàn)象學(xué)[M].韓樹站,譯.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6:45.
[5]崔欣欣.“形式需要通過知覺來釋讀”——杜夫海納的審美對象形式理論探析[ J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學(xué)報,2018(01):83.
[7]Mikel Dufrenne.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M].Trans.Edward s.Casey et al.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223.
[8]尹航.重返本源和諧之途[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1:55.
【作者簡介】? 劉 爽,女,黑龍江鶴崗人,山西師范大學(xué)戲劇與影視學(xué)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戲劇美學(xué)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創(chuàng)新基金項目“基于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美學(xué)精神的電視文藝創(chuàng)作嬗變研
究”(編號:2020BY085)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