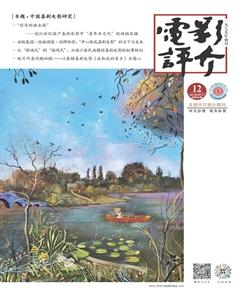宮崎駿動畫電影在中國的傳播與啟示
日本著名的動畫電影大師,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風靡世界。他的作品充滿了豐富的情感與人性的光輝,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共鳴。宮崎駿作品中飽含了日本的傳統文化,而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文化上具有較多的相似性,這便使其作品中表達的文化與思想能夠很順利地在中國傳播與接受。電影作為宮崎駿動畫作品的載體,其十分形象地承載與呈現了宮崎駿動畫作品中所表達的文化與思想內涵,使之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傳播,提升了日本文化與日本電影的知名度與影響力。
一、《千與千尋》進入中國電影市場
《千與千尋》是宮崎駿的代表作之一,于2001年在日本上映并在當年創造了票房神話,翌年更是獲得了第25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優秀作品獎、第5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和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長片等獎項。2019年,我國正式將該片引入內地,即便在中國市場已有無數人看過這部電影,2019年上映時也收獲了將近5億的票房以及貓眼評分9.3的高分①。究其原因,從中國制片方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由于宮崎駿電影本身的吸引力與影響力使得許多忠實粉絲走進影院重溫這部電影;其次,國內在引進時配制了中文配音、且配音演員以明星為主,如千尋的配音是周冬雨、白龍的配音是井柏然。兩位演員在年輕觀眾中間很有人氣,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電影對新粉絲的吸引力,也擴大了電影本身的宣傳廣度;最后,在宣傳海報上,負責海報繪畫的是中國電影界頂級藝術家黃海。為了能讓宮崎駿動畫電影的世界觀完整地傳達給國內觀眾,海報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了精心設計。在主人公形象方面,海報塑造了主人公自立自強的形象,能夠給青少年樹立正面的榜樣。這打動了許多家長,他們帶著孩子走進影院觀看這部電影。然而并不是所有采用相同引進方法的日本動畫電影在中國都能取得成功,也有水土不服的例子。如《櫻桃小丸子:來自意大利的少年》《精靈寶可夢:波爾凱尼恩與機巧的瑪機雅娜》《黑子的籃球:終極一戰》等也都是來自日本的動畫電影,且本身是有漫畫粉絲基礎的,但最終在中國只收獲了百萬票房,并未大火,影響力也遠不及《千與千尋》。宮崎駿動畫電影能夠在中國廣泛傳播并取得成功有其電影本身的深層原因,本文試著探究其在中國傳播與成功的深層因素。
二、《千與千尋》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原因分析
《千與千尋》講述了少女千尋在神靈世界中經過磨難不斷成長、幫助朋友和找尋自我并解救雙親的故事。這部電影在中國廣泛傳播了近20年卻經久不衰,其主要的深層原因在于電影巧用色彩塑造了與觀眾間的精神共鳴、善用敘事增加了受眾群體、活用文化增加了觀眾的認同感以及妙用生態共生美學契合觀眾的價值情愫。
(一)巧用色彩塑造精神共鳴
一部優秀的動畫電影的審美意境可以使人產生無限的想象、感受導演用畫面傳達的精神世界,使觀眾能夠快速對電影有深刻具體的第一印象。宮崎駿在電影中利用色彩傳達信息,服務于故事情節,加深了觀眾對電影的印象與理解。
《千與千尋》影片一開始即是以綠色為主的溫暖色調,讓觀眾以舒緩放松的心情慢慢浸入故事里。但進入神靈世界以后,故事的主要發生地“油屋”是一座以紅色為主要顏色、頗具唐風的古老建筑。大面積的紅色凸顯了這個建筑的華麗與貴重。同時,紅色的墻面上又有與之反差的綠色在其中,增添了莊重感,與頂端閣樓的亮黃色組成了油屋的整體印象。視覺從油屋擴大到天空,藍天白云的清新色調通透干凈,中和了油屋的沉重歷史感,透出一種動態的視覺擴張。油屋旁邊灰色的煙囪、深綠色盤旋蜿蜒的古松以及掛在大門上深藍色的門簾,這些低飽和度的顏色中和了大片紅與綠的顏色對比,給人以高雅柔和與古樸莊重相糅合后的美感。
在日本的民俗中素有“黑不凈”的觀念,白色則代表著潔白與真善美。在日本傳統婚禮上,新娘著一身全白的“白無垢”和服,象征著純潔無暇的婚姻。由此可見白色和黑色在日本文化中的寓意。影片中,小白龍的本體是一條白色的龍,白色則代表它是善良的。河神的形象是一團黑色的污泥,在千尋幫助他清理干凈后河神的身影卻變成了白色飛向天空。前后黑白對比十分明顯,寓意著被污染的河神回歸到潔凈之中。無臉男戴著白色面具、身穿一襲黑袍。一方面他生活在邊緣地帶,內心充滿了孤獨,還曾因為欲望而誘使并吞噬無辜的人;另一方面他在千尋的成長道路上給予了很多幫助。邪惡與美好并存的無臉男,正如他的形象一樣,是黑白交織而成的。黑白兩色的對比運用,使得影片中重要人物的性格與形象生動而簡潔地印在了觀眾的視覺中。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主人公千尋的形象。在神靈世界中,千尋一直身著一襲紅袍。紅色代表著熱情與活潑,也代表著斗志與勇氣。千尋在神靈世界中一直無私幫助著身邊的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沒有放棄過,最終也成功解救了父母,回到了現實世界中。宮崎駿利用紅色完美地體現了主人公千尋的性格與形象,使得少女千尋的身影深深地刻在觀眾的心中。在影片中,宮崎駿利用畫面表現的不是普遍意義上的色彩,而是區別于現實物象之外的心理主觀意象。整部影片不管是建筑的配色還是人物形象的用色,其色彩的運用都有其自身的寓意。色彩對比帶來的沖擊感與深層寓意以及明確深刻的主題都絲毫不亞于實拍的電影,這使得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具備很高的觀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能夠廣泛傳播的深層原因。
(二)善用敘事增加受眾群體
動畫電影面對的觀眾不僅有未成年人,還有成年人。《千與千尋》邏輯流暢、故事線明朗的敘事使得不同年齡段的觀眾都能看懂這部電影。同時,整個故事也不是簡單的動畫片,而是有其敘事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其敘事結構與人物角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坊寶寶、河神和無臉男最初是千尋在神靈世界所經歷的磨難和考驗,但最終也是給予千尋幫助并促進她成長的催化劑。小白龍在幫助千尋的過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記憶,有其自身的成長軌跡。對于成年觀眾來說,這是一部值得深入思考與反復品味的電影,只不過宮崎駿是以動畫的形式呈現出來,而動畫的表現形式無疑又對未成年觀眾產生了吸引。再加上故事本身簡單與復雜相互交織的敘事結構,使得電影的受眾面無形中擴大了很多。
在敘事方面,影片采用“迷失-尋找-回歸”的主線來敘述主人公的成長歷程。首先是千尋一家在搬家途中闖入神靈世界,隨后父母變成豬、主人公千尋被收走,名字改名為“千”在油屋打工自保。這屬于故事主線中開端的“迷失”部分。接下來為了解救父母和幫助過自己的小白龍,千尋決定踏上尋找錢婆婆的旅程。期間遇到了重重困難,在千尋經歷并克服磨難以后,她成功找到了錢婆婆。這屬于故事的“尋找”部分。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千尋得到了錢婆婆的原諒,小白龍的魔法也被解除。千尋返回油屋通過了湯婆婆的考驗,解救了父母并和父母一起回到了真實的世界。這是最后“回歸”的高潮部分。整體清晰緊湊的敘事結構便于各年齡層的觀眾觀賞電影。
在電影的制作方面,宮崎駿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社會意識與人文關懷。人類文明的毀滅和再生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主題都曾出現在他的作品中,給他的動畫電影注入了區別于其他娛樂性動畫片的思想深度和人文思考。其動畫電影的特點在于充分發揮動畫的形式創造出奇幻而豐富的想象世界,同時在作品中賦予深刻的思想主題。這不僅使得其作品有很高的觀賞性,也展現了宮崎駿對各種現實問題的思考。在《千與千尋》中,宮崎駿塑造了白龍與河神兩個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就是啟發人們要保護生態環境、思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問題。宮崎駿在動畫電影中注入深刻主題與人文思考也改變了人們對于動畫電影的狹隘認識以及以未成年人為主要觀眾的定位,使得其動畫作品跨越了觀眾的層次與年齡,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三)活用文化增加觀眾認同
一部電影想要獲得成功,離不開觀眾的支持與認同。《千與千尋》就獲得了日本與中國觀眾的極大支持與認同。宮崎駿是日本動畫界的大師,其作品獲得日本觀眾的認同——很好理解。其作品在傳入中國后依然獲得了中國觀眾的支持與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該電影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展現。在2000多年的中日交流中,漢字給日本帶去的不止是書寫表達的符號,而是以此為象征的發達的大陸文化。在歷史上,日本官方曾多次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來到中國學習語言、文化、制度等。即使是在沒有官方交流記載的時期,中日之間的民間交流也從未中斷過。[1]在近代,中國也從日本吸收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可以說中日兩國在2000多年的交流中,互相學習對方先進的地方來完善自己,在文化上亦有較多的相似性。《千與千尋》從日本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文化養分同樣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跡可循。
電影名“千與千尋”是其中文譯名,日文原名則是“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從日文原名中就直觀體現了電影所包含的日本傳統文化——神道文化的內涵。“千と千尋”(千與千尋)代表了千尋的兩個名字。在現實世界中,她本名叫“千尋”;進入神靈世界以后則叫作“千”。這兩個名字暗示了千尋處在一實一虛兩個空間中,只有找回自己的本名才能回到真實的世界。日本自古以來就有“言霊信仰”(譯為言靈信仰)。在上古時期口語交流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里,語言本身具有遠超現代人想象的神奇力量。即使是我們現代人,也會因為房間號是“四”而想到“死”覺得不吉利;父母在給孩子取名時也會取一個擁有美好寓意的名字。這都是相信、認同“言靈信仰”的體現。對于被詛咒或犯罪的人也是強行更改其姓名為惡名,以體現詛咒和懲罰的含義。在日本史書《續日本紀》中有這樣一則記載:因為權力斗爭失敗,“‘黃文王被改名為‘多夫禮(意為瘋癲之人),‘道祖王被改名為‘麻度比(意為執迷不悟之人),‘賀茂角足被改姓為‘乃呂志(意為愚蠢無能)。”[2]
因為名字擁有能使它所表示的意義成真的魔力,所以一旦改為惡名,當事人就會陷入惡名所昭示的境地。影片中湯婆婆收走了千尋的本名,代表著抹去了她的真實身份,令千尋只能停留在虛幻的神靈世界中。神道文化認為世間萬物皆有靈,即便是語言也有靈在其中。“言靈信仰”體現了這種萬物有靈的思想,是神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
在日文中“神隠し”(譯為神隱)的意思是“神靈讓你消失”,指受到神靈的招待,或遭誘拐、強擄而從人類社會消失。日本歷史上與“神隱”有關的物語有很多,最耳熟能詳的大概是“浦島太郎”的故事。年輕漁夫因救了龍宮中的神龜被帶到龍宮,得到了龍王女兒的款待。龍宮雖好,呆久了難免想家,臨別時龍女贈送漁夫一個玉盒,告誡他不可打開。可等浦島太郎回家后卻發現物是人非,疑惑中打開盒子,不料噴出的一陣白煙將他變成了老翁。原來龍宮一游幾日,回首已是百年。
少女千尋的故事同樣如此。一家三口在搬家途中誤闖神界,闖入后父母還未意識到不妥,看見街邊美味的食物就吃了起來,千尋則發現父母變成了豬,不認識她了。這不符合邏輯的一幕代表著千尋一家的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也就是傳說中的“神隱”。“神隱”在神道文化中體現的是一種“神向”,是對神的一種憧憬和幻想。同樣,“神隱”在中國的詩詞“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也有體現。樵夫進山砍柴,見兩神仙對弈竟看得忘了時間,中途棋局還未結束時手中的斧子已經爛掉。等看完棋回家,發覺已過經年,家鄉也已物是人非。這就是耳熟能詳的“爛柯山”的故事。
另外,宮崎駿在影片中安排了千尋這樣一位主人公——在父母身邊時她膽小害怕,在最初進入神靈世界與解救父母的途中也曾害怕哭泣,但最終用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從膽小到勇敢,用真誠和毅力感染了身邊的人,完成了自身的成長。在這期間,千尋感染了小白龍,讓他從順從湯婆婆作惡到變得清醒,找回自我;千尋也改變了坊寶寶,讓他從一開始的任性刁蠻變得明辨是非。最后坊寶寶回歸油屋時已不再是影片開始時那個得不到就哭泣的孩子,還幫助千尋向湯婆婆求情。這也間接影響了湯婆婆,使她首次遵守了自己的諾言,放回了千尋的父母;千尋也改變了無臉男,在無臉男迷失在用金子誘使他人對自己關心、欲望越來越大時,是千尋幫助他恢復了本來善良溫和的一面。千尋用自己的善良和堅韌改變了這一奇幻旅程中遇到的人們,使得他們都回歸了善良的本性。
“性善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早在戰國時期孟子的學說中即提出“人性本善”的觀點。孟子認為人為之善,是他本性的表現;人為之不善,是違背其本性的。宮崎駿在影片中所體現的“性善論”的價值觀無疑十分符合中國觀眾的傳統價值觀,無形中提高了中國觀眾對影片的認同感。正因為宮崎駿影片中所展現的日本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相似性,中國觀眾才能與影片中所表達的內容產生共鳴感與認同感。從而易于理解與接受這部影片的價值觀,不會產生文化不理解的現象。這恐怕是《千與千尋》在中國不像其他日本動畫電影一樣水土不服,而是被視為經典之作得到廣泛傳播的最重要的原因。
(四)妙用生態共生美學契合價值情愫
宮崎駿在《千與千尋》中還展現了他一以貫之的生態共生美學思想。這在河神出場時體現得淋漓盡致。河神來到油屋洗浴時滿身污泥惡臭熏天,千尋在幫他洗澡的過程中無意間摸到一塊硬鐵狀的東西,拉出來后河神身體里涌出了很多垃圾,竟都是人類的廢棄物,有自行車、電視機、冰箱和廢舊浴缸等。宮崎駿用隱喻的方式影射了人類對自然的污染,表達了他自身對于保護生態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呼吁。
在故事尾聲部分,宮崎駿也利用小白龍恢復記憶想起自己名叫賑早見琥珀主、曾是被人類毀掉的琥珀川的河神,來表達自身對于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定義。即人類不應該毀壞自然,而是保護自然。再者,小白龍在千尋初入神靈世界時數次幫助她,到最后千尋為了拯救受傷的小白龍而冒險踏上尋找錢婆婆的路程,都體現了宮崎駿理想中的人與自然互幫互助的和諧關系,以及想要傳達給觀眾的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生的生態美學思想。隨著《千與千尋》風靡中國,影片中所傳達的日本傳統文化與宮崎駿的生態共生美學思想也隨之得到了廣泛傳播。
此外,宮崎駿在影片中所體現的生態共生美學思想也時刻展示著他對社會和環境的人文關懷。宮崎駿刻畫了上述這些充滿寓意的細節,為觀眾樹立了正面的榜樣,增加了中國觀眾的情感獲得,契合現代觀眾對于保護環境的價值情愫,啟迪和教育了年輕一代。這也是宮崎駿動畫電影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
三、《千與千尋》對中國動畫電影的啟示
《千與千尋》在人物塑造、電影主題、文化運用等方面都是非常值得中國動畫電影借鑒的。近年來,《大魚海棠》《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動畫電影在國內上映時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三部電影在色彩的運用上也非常有中國特色,但卻收獲了不同的口碑。透過對《千與千尋》的分析與借鑒,中國動畫電影可從以下三點得到有益的啟示。
(一)神話故事應符合人物塑造
人民網是這樣評價《大魚海棠》的:“《大魚海棠》的故事設置、蘊含的世界觀都充滿中國氣象。而片子的故事邏輯和三觀還是讓人感覺有些混亂。看起來格局挺高,但故事濃縮起來就是個三角戀,偏還生硬地填進了古代神話,以及犧牲、選擇和生死這樣高大的話題。影片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物,除了名字外毫無特點,所有角色的刻畫浮于表面,缺乏基本的敘事動機。”[4]
不難看出,《大魚海棠》口碑不佳的原因主要是人物塑造膚淺,且過度注重刻畫神話背景,忽視了背景只是服務于劇情這一要素。引用的眾多神話人物也只是淪為了文化符號,并沒有推動或豐富整個故事的發展。不同的是,《千與千尋》在影片中同樣借鑒了日本傳統神話人物的形象。劇中給予千尋幫助與指引的鍋爐爺爺,其形象來自于日本古畫中的“土蜘蛛”。鍋爐爺爺對千尋的指引推動了劇情的發展,并不是一個純粹無用的角色。河神的臉部形象借鑒了日本傳統藝術“能劇”的面具,同時河神也是千尋成長路上所經歷的考驗之一,且具有影射人類污染自然的寓意。影片中的另一重要角色無臉男,其臉部形象設計成白色面具,這借鑒了日本神明“春日神”的形象。無臉男在影片中的作用無需再贅述。甚至影片開頭從船上下來的一眾神明之中,直接就出現了春日神祭祀時的形象。宮崎駿運用的這一日本傳統神話人物的形象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而是從側面點出了主人公正身處于“神隱”的虛幻世界里。影片中對日本傳統神話人物的借鑒并沒有浮于表面,而是契合了劇情發展和人物塑造,是為豐富整個敘事結構與深度刻畫人物而服務的。
(二)文化運用應契合故事發展
《大魚海棠》在創作時融合了許多來自古書《山海經》《搜神記》與“女媧補天”等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但正如《光明日報》的評價一樣:“……整部電影引經據典……但人物與劇情卻沒有呈現出更深刻豐富的世界。這導致片中眾多文化符號都變成了浮光掠影,甚至被批評為華而不實。”[5]電影從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汲取養分是有效的思路與方法,但不能空洞地堆砌傳統文化元素而忽視了利用其來服務于整個故事發展的這一核心。在《千與千尋》中,宮崎駿利用“神隱”這一日本傳統文化作為整個故事的出發點,少女千尋的奇幻故事正是建立在“神隱”的基礎上而展開的。宮崎駿在借鑒與運用傳統文化元素時做到了服務于故事發展這一核心,沒有讓傳統文化淪為華而不實的文化符號,從而為影片增加了文化內涵,錦上添花。
(三)電影主題應彰顯人文關懷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蘊含的人文關懷與深刻主題是目前中國動畫電影所缺失的。《大魚海棠》試圖探討“生死、選擇、犧牲”這樣宏大的主題,但顯然沒有成功,其表達的價值觀與主題都稍顯凌亂,試圖“深刻”但最終不倫不類。《西游記之大圣歸來》所表達的英雄主題與《哪吒之魔童降世》所表達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激發觀眾的奮斗意志,但最終只是對于個人的鼓勵,沒有升華到整個社會層面,也沒有對社會問題作出有力的呼吁。
宮崎駿把日本傳統文化與自己的生態共生美學思想嵌入電影主題之中,不僅在世界范圍內傳播了日本傳統文化,提升了日本傳統文化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同時也宣揚了自己的生態共生美學思想,把自身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呼吁體現在作品之中,增加了電影主題的深度、彰顯了自身對于人類和社會的人文關懷。這一思想不僅在《千與千尋》中有所體現,在其他作品如《風之谷》《幽靈公主》《懸崖上的金魚姬》等影片中都能看到。這是宮崎駿一以貫之的生態思想,是基于現代社會環境發出對于保護生態的懇切呼吁。保護生態環境是人類的共識,宮崎駿在其作品中不斷呼吁這一點,也令他的作品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認可。中國動畫電影在創作過程中不僅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還應關注社會問題、關注人類社會共同的議題,以便加強作品在國際上傳播的廣泛性與接受度。
結語
本文選取宮崎駿代表作《千與千尋》為例,分析了其在中國的傳播現狀與廣泛傳播的原因以及對中國動畫電影的啟示。宮崎駿動畫電影巧用色彩塑造了與觀眾間的精神共鳴、善用敘事增加了受眾群體、活用文化增加了觀眾的認同感、妙用生態共生美學契合了觀眾的價值情愫,使其在中國廣泛傳播。
中國相較日本來說,動畫人才較少,沒有形成像日本一樣完整成熟的動畫產業鏈;對于動畫原創人才的培養也不足,沒有形成像宮崎駿動畫電影一樣的文化IP或動畫系列。中國的動畫電影要繼續發展,應豐富動畫題材,培養更多的原創人才并拓展廣泛的目標受眾。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動畫電影也應向宮崎駿動畫電影學習,活用傳統文化,增加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并且關注電影主題的深度問題。
①數據來源于貓眼專業版實時票房http://piaofang.maoyan.com/,上網時間2019年8月29日。
參考文獻:
[1][日]藤家禮之助.中日交流兩千年[M].章林,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
[2][日]山口仲美.寫給大家的日語史[M].潘鈞,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10.
[3]韓立紅.日本文化概論第三版[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147-148.
[4]任義.《大魚海棠》:華麗但空洞的“幼稚病”[EB/OL].人民網,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9248052/bc1fJmmO5_hvNCgNfthOY-BjiZfkurFvbBRS7KgyIchhSTc98d9wAtr7wlm2d562UMEcy2R8wS-rZ2N3R16_DEWgyD2j93WRkG4ZEx0nEtTJ8kZi_p1-.
[5]陳雪.《大魚海棠》為何與優秀失之交臂[N].光明日報,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6-07/18/nw.D110000gmrb_20160718_4-02.htm.
【作者簡介】? 令狐菁菁,女,貴州遵義人,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中日詞匯交
流史、文化交流史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9年度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青年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貴州在中國-東盟
分歧管控中的機遇與挑戰研究”(編號:19GZQN2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