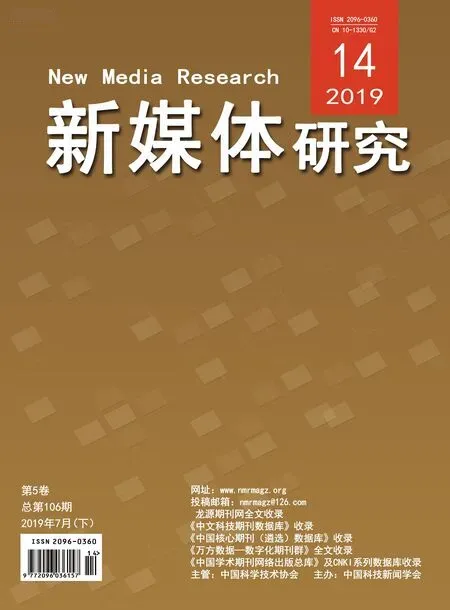伯克“同一理論”下觀察類綜藝的敘事策略分析
黃雯歆 聞娛
關鍵詞 “同一理論”;觀察類綜藝;敘事策略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4-0093-04
近年來,觀察類綜藝逐步走入大眾視野。在節目遍地“按臺本走”的國內綜藝市場里,觀察類綜藝抓住了“真實”這一稀缺的符號,最大限度地弱化了臺本的直接干預,優化受眾的沉浸式觀看體驗。而這類綜藝往往聚焦于某個特定的社會話題情境,諸如職場、戀愛關系等。
肯尼斯·伯克的“同一理論”認為,修辭話語采取三種方式達到交際雙方的互相認同,即“同情認同”“對立認同”與“誤同”[ 1 ]。以2020年末熱播的《令人心動的offer2》為例,節目圍繞“職場”,將中國的“紅圈所”(中國最頂級的律所)——君合律師事務所劃定為特定情境,并在其中置入八位各有特色的實習生。鮮明的個性、學歷背景標簽使得節目中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符號化了,實習生個體以及他們的情緒表達、參與性行為、所處環境等實際上都成為了意義構建的符號。這些符號通過一定方式進行組合后,使得“話語”不再單純地以傳統的語言體系特征呈現,而成為了超越文本狀態的符號結構體,整體性地構成對受眾的意義表達,以求與受眾達成“同一”,即通過觀看節目,反省思考,實現對自我、對與他人關系、對社會的某種關照。
1 同情認同:“95后新職場人”的敘事主題
“同情認同”旨在通過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共通性,縮短與受眾之間的距離,以贏得認同。類似于許多觀察類綜藝,《令人心動的offer2》所聚焦的敘事主題也是社會話題熱議的情境——“職場”。作為網生一代,“90后”和“00后”對社會熱點話題擁有更高的敏感度,是節目最主要的目標受眾群體。
當下正值“95后”剛剛大學畢業,邁入“職場”的人生拐點。職場中的表現除了會受到學歷、英語水平等硬性條件的影響,也會受到個人的整體性格、與團隊適配性等方面的影響。問題的復雜性和解決問題的剛性需要,使得目標受眾觀看節目的需求大大上升。
而不同于其他觀察類綜藝大批量地啟用明星,《令人心動的offer2》被觀察的對象皆為素人。素人對于受眾來說更為陌生,但是他們的個性和經歷卻更容易引起普通人的共鳴,相比之下,在“職場”這個情境中的輻射目標受眾群相較明星也更為廣泛。
此外,雖然8位實習生同為“95后”,個人和個人之間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卻十分明顯。節目組通過第一期實習生面試的自我介紹和后期課題合作中展現的個人特點,將當下各類的職場新人形象的進一步區格。學歷、自述和他述(如導師、觀察團評價)標簽的逐步完善,組合拼貼成了每個人符號化后對標的現實中不同的職場人群(如表1)。除了有“海歸精英”“完美男神”這樣職場中榜樣化的形象外,也有職場“小透明”“菜鳥”等更貼近普通觀眾的角色。他們分別代表著各類職場人,幫助不同類型的受眾通過觀察同性格的實習生表現,審視自己。比如第二季實習生丁輝,在實習工作結束后,回到家發現自己忙到忘記生日的這一段經歷,引發了受眾關于“丁輝是打工人的真實寫照”這一共鳴,相關熱搜的閱讀量高達5.2億。
2 對立認同:“精英”與“平民”的敘事沖突
受眾與綜藝之間的情感通道通過“同情認同”被打開,高壓的環境下素人的真實反饋觸及了受眾過往的生活經驗,幫助受眾完成了從單純的移情到共情的整個情緒接收過程,也為后期群體共同意義空間的建立進行了鋪墊。但單純依靠“同情認同”也無法長期維系群體之間的情感連接,當群體受到來自對立面的壓力時,反而能加強群體間的聯系,使節目內涵更加豐富。
“對立認同”認為對立兩方會基于共同的敵人,將對立面作為“一種凝聚的力量”[ 2 ]來看待,以達成必要的“同一”。“精英”代表的小部分和“平民”代表的大多數之間的矛盾沖突是古而有之的。拉斯韋爾認為,“精英是用于分類的、描述的概念。它指的是某一社會中占據高級職位的人”[ 3 ]。然而,隨著現代高等教育的普及,精英主義受到了來自大多數人的挑戰。他們主張應該限制精英權力,擴大平等。但是《令人心動的offer2》的敘事策略偏偏反其道而行,放大“精英”與“平民”的這對敘事沖突,制造矛盾和焦點,主動設置議題。一方面,在節目錄制的第一期,節目組就向觀眾介紹了君合律師事務所“紅圈所”的行業地位和被錄取實習生兩萬實習底薪的實習待遇。在節目面試環節,導師們也犀利地向實習生們拋出“你這樣的簡歷,如果是通過正常的社招面試,在人事環節就會被直接篩出”這樣的觀點,將精英的社會地位和資源優勢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通過實習生“平民”水平和律所“精英化”要求的差距,構造敘事沖突,達到吸引受眾持續觀察實習生逐步成長蛻變的目的。
另一方面,節目組在實習生前臺人設建構的環節,就植入了“海歸”“學霸”標準精英化的教育培養道路和“二本跨考”“口語不佳”這樣的平民路線作為對立概念,并利用每次課題排名和淘汰機制對選手的標簽屬性不斷標出和強調,深化矛盾,加強綜藝的戲劇效果。在節目的持續推進過程中,又主動將初始構建在學歷標簽基礎上的“精英”和“平民”概念推翻,更多強調“能力”這一標簽上的“精英化”,最終成功彌合了對立雙方的差距,轉移了敘事的矛盾焦點。
而伴隨著節目的播出,受眾也不斷根據節目內容,與節目主動設置的“平民”“精英”符號建立身份、情感上的“同一”,甚至在社交媒體上,主動地進行觀點表達和交換。本是教育背景各異的受眾,通過集體意志的集合,既共同呼吁職場新人不要囿于“出身”,職場上實力才是硬道理;又呼吁行業在用工上,拋棄刻板印象,樹立公平、公正的擇人標準,以此達到“對立認同”。在受眾被“教育”的過程中,節目敘事的社會價值也得到了進一步實現。
3 誤同:“影像流”和“多敘體”的敘事技巧
“誤同”是指錯誤地將某種形象、行為或效果認同為自己的,其根源是沒有真正認清自己認同的對象[ 4 ]。觀察類綜藝的相關研究中,很多學者都提到了“鏡像自我”的觀點,即“從(真人秀)的鏡子中我們能夠發現自己并建構自我”[ 5 ]。但是事實上,被觀察者鏡頭中的展示“全貌”其實是被選擇、加工后的“事實”,而不是事實本身。觀察類綜藝更多地只是利用了“影像流”和“多敘體”的敘事技巧,模糊了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的間離性,使主體更多地沉浸于類似鏡像的凝視中。
3.1 “影像流”的觀察體驗
在探討電視呈現背后的權力關系時,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影像流”的概念。
他認為,電視播出的是“有計劃的流程”,無論是電視劇、綜藝或是中插的廣告,其最終呈現給受眾的卻是連續的“流程”[ 6 ]。其背后有媒介對受眾的控制,即受眾只能看到媒介選擇性呈現的、符合模式或流程的內容。
觀察類綜藝作為一種“慢綜藝”形式,拍攝的是被觀察者的全天全時狀態和表現,但是往往最后成片只有1.5~2小時。這是因為綜藝會通過剪輯、拼貼,在一個時間段內更突出地展示緊貼當期主題的內容,弱化其他邊緣敘事線。《令人心動的offer2》中,實習生們的生活不僅只有工作,但在節目中,他們的下班生活、私人空間雖然也會有所提及,但都被弱化了,僅呈現能補充實習生個性的必要畫面,以保證主線的敘事連貫性。剪輯后的每期節目大部分篇幅都圍繞課題的準備、呈現展開,而這樣“影像流”影像觀看體驗,一方面保證了受眾的情感連續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受眾陷入“誤同”,更多地加入到節目預先架構好的節目敘事焦點話題的討論中。
3.2 “多敘體”的觀點互補
綜藝通過場景內所有在場的敘事主體間的互動來推動節目敘事進程,而觀察類綜藝相對于普通的綜藝,還另外增加了演播室的“第二現場”敘事空間。因此,受眾最后接受到的信息和觀點,其實不僅僅是被觀察者單方面的自敘信息,而實際上是節目運用“多敘體”的技巧,經預設性臺本支撐和演播廳意見領袖觀點集合共同架構起的“綜合意見”。
3.2.1 節目臺本:全知視角的預設性
觀察類綜藝中,節目組預設的敘事態度和意義選擇會大大影響觀眾對節目整體敘事的認知和解讀[ 7 ]。節目組不僅可以通過花字,配樂等輔助形式,突出制作組判斷的重點內容,甚至在其“無劇本”“真實觀察”等宣傳標簽的背后,實際上仍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必要性的臺本支撐。這些通過剪輯、渲染后出的內容事實上都包含了節目組在全知視角下的主觀態度,并不是一種完全客觀的內容呈現,其內容目的就是引導受眾產生共情。
3.2.2 被觀察者:“局內人”表達的戲劇化
沃爾特·費舍爾提出“人類本質上是講故事的動物”[ 8 ]。而人類的敘事行為動機也不僅僅依靠邏輯推理,還與個體對理由、價值的判斷和理解有關。因此,在綜藝限定的情境中,即使是被觀察者本人,所呈現的敘事行為也是復雜多樣的。被觀察者表現時的攝像機存在,讓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后臺反而成為了被包裝的前臺,被觀察者在一個不同以往完全生活化的“舞臺上”進行表演,會不自覺地增加不同于真實的戲劇性因素。
另一角度來看,被觀察者作為鏡頭內的“局內人”,對自己所敘述的內容最終到達的效果是無法把握的。這種效果的模糊性會使得“自敘者”的表達欲望下降,表達個性化減弱,而更加趨向公眾期待,“自敘”的價值也由此降低。
3.2.3 第二現場:多元身份代表的觀點互動
“第二現場”的敘事目標圍繞觀點互動展開,而雖然嘉賓的身份都是“觀察團”,團內的敘述主體具體代表的職場身份卻更為復雜。以《令人心動的offer2》為例,“第二現場”既要有何炅、撒貝寧這樣的“主持人”——節奏帶動者、楊天真這樣的職場“上位者”、周深和范丞丞這樣的同齡“打工人”代表,也有徐律這樣的專業職場榜樣。觀察團多元的“職場”身份提供了更多角度的討論觀點,共同承擔起“第二現場”的敘述任務。
而“第二現場”的觀察團事實上也是鏡頭里的人。公開的觀點分享使得他們成為事實層面中的隱形意見領袖。表面上的個人觀點,最后卻成為了第一現場被觀察者行為的“解釋性補充”。不可避免的,這種解釋性補充由于主體間性,本身就是一種誤讀,同時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觀眾的態度和意見,以達成節目意圖實現的最終敘事效果。
4 反思
肯尼斯·伯克的“同一理論”是其修辭學思想的中心內容,將其引入當下熱點的觀察類綜藝節目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尋求互動雙方的“認同”已經成為不論話語修辭還是觀察類綜藝敘事策略的共同目標。
觀察類綜藝的代入感和沉浸式觀看體驗,讓此類型的綜藝在同質化的綜藝市場中脫穎而出。關照受眾的敘述主題,幫助受眾更快的與節目設置的人設標簽站成“同一”;主動設置的敘事沖突,將基于對立認同觀念的深刻認知,轉化為受眾支持節目主旨的群體意識;新形式的敘事技巧,提高內容情感敘事上的連貫性和通達性,使得節目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但是,雖然節目因“同一”而成功,但其所呈現出的“真實”,實際上仍舊是一種滿足受眾凝視、窺探需求的商品,觀眾實際觀察的是節目精心打造的“擬態環境”,鏡頭內的“真實”和鏡頭外的現實之間的差距是終究無法彌合的。節目熱度散去,如何引導受眾回到現實,回歸理性,而不是單單囿于綜藝為了敘事效果放大的沖突或者構建的某個人設,從而摒棄無意義的娛樂消費,提升節目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是觀察類綜藝未來發展中更亟待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肯尼斯·伯克,等.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M].常昌富,顧寶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李鑫華.博克新修辭學對立認同說與對照辭格認知意義探析[J].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24-28.
[3]哈羅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M].楊昌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
[4]陳莉紅.從肯尼斯·伯克的認同說解讀公益廣告的和諧功能[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2(3):303-305.
[5]孔玉婷.職場觀察類綜藝節目的“鏡像自我”:以《令人心動的offer》為例[J].視聽,2020(2):40-41.
[6]易前良,金昌慶.雷蒙·威廉斯的電視本體論:“電視研究”的理論奠基[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09(4):158-164.
[7]高亞林.凝視體驗與通達意義:情感觀察類綜藝節目的敘事研究[J].當代電視,2020(1):66-71.
[8]Walter R.Fisher.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J].Communication Monographs,1984,51(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