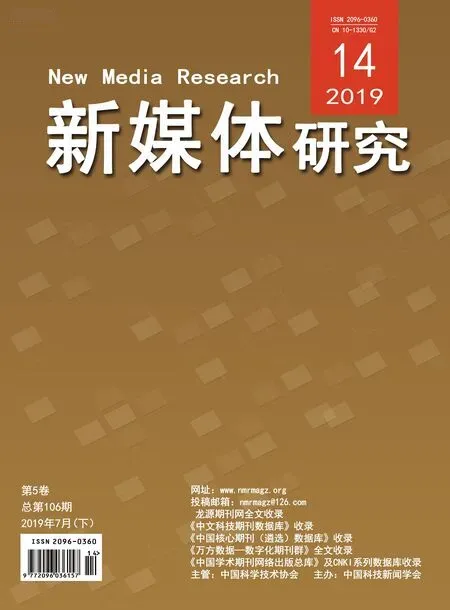融媒體視角下虛擬偶像人設符號的構建和維系
李雅欣
關鍵詞 虛擬偶像;人設;粉絲文化;擬劇理論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4-0101-03
1 虛擬偶像人設:科技與粉絲雙重構建
1.1 技術賦能:智能虛擬偶像的人設搭建
虛擬偶像是指其本身并不以真實形態與我們共處同一空間,卻可以借助互聯網等虛擬場景或在現實場景中實現偶像活動的一類新興偶像。他可以是虛擬歌姬、動漫角色,甚至可以不是人類形象。現如今,隨著動態捕捉、實時渲染、人臉識別和人物建模等多重新技術的應用愈發成熟,虛擬偶像的受眾也不再停留在“圈地自萌”的二次元圈內,走向了跨次元壁的嘗試。
新技術的應用賦予了虛擬偶像“血肉之軀”,隨著科技的發展,三維計算機圖形技術愈發成熟,網絡虛擬偶像、游戲虛擬偶像、虛擬歌姬等紛紛涌現。虛擬偶像生態已步入繁榮期,虛擬偶像在具備聲音、動作等多重表演模態的同時實現與人類同時空互動的效果。2020年愛奇藝推出的虛擬偶像才藝競演節目《跨次元新星》中,來自各大公司的虛擬偶像齊上陣,畫面上優質的虛擬偶像動作連貫、形象可人,可以完成與人類同時空的即時互動,甚至實現了與三次元人類的跨次元擁抱。
從技術的角度看,虛擬偶像是數字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計算機圖形技術的應用使得虛擬偶像的形象更加生動立體,也為塑造“完美偶像”奠定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全息投影讓他們從熒屏走向線下空間成為可能,給予受眾真實的空間陪伴感,強化了其作為“人”的存在。在人工智能語境下,把技術賦能解讀為“賦予智能”更有現實意義,基于“人工智能感官系統”,讓虛擬偶像成為具備情感和創作能力、可與人類實現無障礙互動交流的人工智能虛擬偶像[ 1 ]。而被賦予智能思維的虛擬偶像在動作、表情等方面做出實時反饋,能夠以更豐富的“人格魅力”與粉絲互動,實現了跨次元的“人格化傳播”。
此外,虛擬偶像的人設元素,如形象特點、服飾特色以及由此反映的性格特征,都受計算機技術控制塑造形成。以綜藝節目《跨次元新星》中的寐魚為例,他本是一只《山海經》中的神獸,被路過的師傅救下帶到山中修煉而化成人形。這樣的人設背景下,寐魚的衣著服飾總是帶有國風色彩;而初舞臺選擇了由李白的詩改編而成的《短歌行》驚艷四座;在擬人交互時,他的武術才藝表演也與其上山修煉的經歷有關。虛擬偶像的初始人設由程序設定,而人物建模的技術將其外在形象和服化道設置貼合人設要求。在虛擬偶像擬人際交互的過程中,通過表情、動作及其才藝表演實現了其人設符號的表達。由此,技術完成了對虛擬偶像人設的建構。
1.2 粉絲建構:在反饋和互動中臻于完善的虛擬偶像
虛擬偶像文化是典型的“參與式文化”,在亨利·詹金斯的理論中,粉絲被看作是積極的消費者,而處在新媒體傳播語境下的粉絲群體對偶像文本進行解碼和再編碼的行為更具能動性[ 2 ]。在傳統的偶像與粉絲的關系互動中,粉絲只作為其人設符號的消費者,而隨著虛擬偶像的誕生,粉絲的權利進一步擴大,他們高度參與偶像的角色編碼過程中,其意見成為官方修正偶像人設的重要考量。
虛擬偶像作為可被解碼和再編碼的素材,在不同粉絲筆下留下多元化的解釋空間。皮爾斯在《鮑德溫心理學與哲學詞典》中有關符號這一詞條中說到:“符號是任何一種事物,它可以使別的東西(它的解釋項)去指稱一個對象,并且這個符號自身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指涉它的對象;解釋項不停地變成新的符號,如此延綿以至無窮”[ 3 ]。在虛擬偶像人設符號的消費過程中,粉絲對其解釋應是開放動態的過程。粉絲群體對于偶像文本的再塑造也會影響新的粉絲對于偶像原文本的解讀。也就是說,虛擬偶像的人設并不只由基礎程序設定,同時包含有粉絲通過同人創作等手段為其賦予的新的人設符號。這些不同的特征不斷豐富完善虛擬偶像的人設,也為粉絲找到了獨屬于自己創作的偶像空間。以中國首位虛擬偶像東方梔子為例,她初次亮相在2011年的中國文化藝術獎首屆動畫獎頒獎典禮上,但是她的演出視頻卻惡評如潮:雙馬尾的外形設定疑似抄襲初音未來,“火龍果”的服裝設計也飽受詬病,再加上其嗓音難聽、動作僵硬,一時之間大家紛紛聲討制作方[ 4 ]。迫于輿論的巨大壓力,其制作人在一個月后宣布與東方梔子脫離關系。在2012年梔子同人社成立并開始在嗶哩嗶哩網站上發布MMD①同人作品,在精心制作的視頻里梔子形象得到改善,附加了之前被拋棄的萌屬性,動作也流暢自如。
由官方構建的梔子的形象在經由粉絲感知后,在其審美經驗的加工下被解讀為一種符號存在,而粉絲在此基礎上重構了梔子的形象,實際上是對梔子這一符號的闡釋。這一新的符號被其他粉絲感知并在下一輪傳播過程中再度變為可解讀的符號文本。粉絲之間具備交流和傳播梔子這一符號的能力,由此關聯了一個可以共享梔子符號解釋項的意義社群[ 3 ],粉絲在獲得集體認同感的同時,積極地對偶像文本行使解讀與探索的權力。意義社群提供了可討論和探究虛擬偶像形象符號的空間,在針對其形象發展探索的社群話語中,既有的虛擬偶像形象被改寫并逐漸趨近于粉絲期待的理想值,并在不斷歷經這一循環上升的過程中實現形象符號的無限衍生。
在參與到虛擬偶像內容生產的過程中,粉絲依據自己對虛擬偶像的理解進行文本的改編或補充等,極大地拓展了虛擬偶像人設的邊界,而正是對人設符號不斷地賦予和解讀,使得虛擬偶像的生命力得以維持或煥發新生。
2 人設維系:技術與運營的雙重考驗
2.1 “不會崩塌”的完美偶像
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 5 ]中把人們在他人面前刻意控制自我形象的場合定義為前臺,而相較于前臺,后臺是人們退出角色扮演的私下場合。于偶像而言,出現在公眾視野并需要保持表演性形象的即為前臺,而后臺則是他們的私生活領域。在傳統真人偶像的人設塑造中,總會因前后臺形象出現偏差而被粉絲詬病甚至出現人設崩塌的情況。但虛擬偶像人設崩塌的風險幾乎不存在。首先,虛擬偶像在事實層面不具備后臺這一部分。本質上他們是3D建模和全息影像等技術產物的結合,自誕生之日起,其身體元素和行為模式就已被制作人和粉絲書寫完成,客觀上不具備能夠獨立行動的意識。其次,虛擬偶像的后臺對粉絲來說是透明的,他們的“虛擬情感”和成長背景故事向粉絲完全敞開,甚至粉絲也可以參與到其人設構建的某些環節。這些因素使粉絲能夠從中獲得更加安全穩定的追星體驗。
不同于現實偶像的形象隨時間而流變,虛擬偶像不受時間流逝的影響,除非在一定的時間段里程序被制作人修改,其聲音和外在形象會始終如設定一般。也正是由于與三次元有著明晰的界限,處在二次元時空下的虛擬偶像的人設符號并不因現實流轉而改變。“次元壁”保護了虛擬偶像的青春形象和爛漫的性格不受現實條件影響,維持了在粉絲心中純粹的偶像形象。即便是當年備受爭議的東方梔子,大家紛紛不滿的也只是制作方技術上粗制濫造的問題,并沒有上升到針對梔子在人格維度上的價值判斷。在粉絲眼中,他們主動性的缺失恰恰是他們無辜的表現,次元壁成為保護他們完美形象的隔離帶。技術的進步只會讓虛擬偶像更像“人”,他們將會有無限潛力且永遠保持在最佳狀態,這是三次元偶像難以達成的完美狀態。
2.2 靈活的印象管理實現多平臺“人格化傳播”
所謂印象管理,是指人們依據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應,從而給他者帶來良好的印象。在戈夫曼的理論中,印象管理被分為獲得性印象管理和保護性印象管理,這兩部分在維系偶像人設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獲得性印象管理是指通過努力使別人積極看待自己的形象,而保護性印象管理是指弱化自己的缺點不讓別人消極地看待自己的保護性措施。在偶像人設維系的過程中,獲得性印象管理體現在偶像在各個平臺通過文字、照片或視頻等方式進行自我展示來鞏固自己人設的行為。保護性印象管理則表現為當出現偶像失格的情況時,公關公司努力為其減少負面評價以挽回形象的各種舉動。虛擬偶像的運營團隊同樣可以通過靈活的手段實現偶像人設符號在各媒介平臺下的建構,無論是在綜藝節目現身,還是通過微博、抖音等各種新媒體途徑,實質上都是通過不斷豐富自身人設的各種互動場景,進而實現與粉絲的情感交互。以愛奇藝自創的首支虛擬樂團廠牌——Richboom為例,個性鮮明的六位成員借助愛奇藝自身的節目資源在各大節目中紛紛亮相。成員Rainbow在《青春有你》舞臺上是唱跳俱佳的師姐,而成員ProduceC以虛擬主持人的身份加入《唱作人》的舞臺[ 6 ]。擁有獨立舞臺的Richboom成員通過才藝展示和與節目中其他成員的積極互動塑造其“個人魅力”。
在新媒體語境下,網絡虛擬空間給予了“人設”更多可架構的空間,由此虛擬偶像在微博等各種社交媒體平臺上也可以通過照片、視頻等方式分享自己的生活,營造更細節化的真實感,實現跨越虛擬與現實屏障的真實陪伴。正是網絡的不在場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官方回應的感覺,使粉絲有種被偶像回應的“錯覺”。而正是通過這種情感聯系的手段愈發強化了其在虛擬空間的陪伴感。加之動作捕捉和實時渲染技術的成熟,虛擬偶像直播互動也已普遍運用。利用直播的形式將粉絲與偶像置于同一場域下,粉絲可以借助彈幕進行實時反饋,雙方均“足以感知彼此正在做什么,足以感知到旁觀者,足以感知到自己正在被感知”[ 7 ]。
2.3 技術運營仍存在一定的不可控風險
雖然虛擬偶像的存在是由技術構建的,并不以實體形象存在于我們的同一時空,但在背后的運營過程中仍需要真人的配合才能實現。樂華公司推出的由真人練習生唐九洲配音的虛擬人物顧城在《跨次元新星》的舞臺上大放異彩。這暗示著虛擬偶像和其背后“扮演者”緊密的作用關系,也提醒制作人維系虛擬偶像人設需要關注“中之人”的管理風險。中之人是指虛擬偶像幕后的配音演員。一方面,真人演員的暴露對于虛擬偶像的形象存在一定挑戰,可能會破壞粉絲對偶像的想象。另一方面,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需要更換配音演員的情況可能會引發粉絲的抵觸情緒。“中之人”管理風險是虛擬偶像運營一直存在的問題,需要公司建立統一的藝人培訓和管理機制,避免由此引發粉絲情感脫軌的危機。此外,技術問題的短板也會給虛擬偶像的表演帶來致命的傷害。在綜藝節目《跨次元新星》中,選手寐魚在首次表演時三維模型運動出現問題,在向觀眾展示“五禽戲”時人物圖像卡頓,影響角色正常表演。諸如此類失誤會使觀眾在觀看虛擬偶像表演時“跳戲”,導致情感維系的過程出現脫離感。
虛擬偶像靠著與粉絲搭建情感聯系獲得喜愛,而互動所依賴的技術、真人配音等都潛藏著發生缺陷的可能[ 8 ]。對于運營者而言,應遵循虛擬偶像文化的情感運營邏輯,強化技術保障,增加與粉絲情感連接的互動,向粉絲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
虛擬偶像的生產和消費是全體網友共同參與的媒介革新,偶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他們的形象文本乃至性格命運都要接受粉絲的審視和改編。粉絲在擬人化的交際中傾注依戀感情的同時,虛擬偶像的情感反饋也在影響粉絲的生活,并被內化為獨特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意義。當然,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虛擬偶像技術不能脫離道德監管的范疇,倫理檢查需要貫穿虛擬文化生產傳播的全過程。運營者在講好商業故事的同時也要回歸“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以滿足粉絲對純真、美好的二次元世界的向往,而非忙碌于偶像經濟里的資本博弈。
注釋
①MikuMikuDance,通常縮寫為MMD,是一個免費的動畫程序,讓用戶動畫和制作3D動畫電影,最初是為Vocaloid角色Hatsune Miku制作的。MikuMikuDance程序本身由Garnek(HiguchiM)編程,用來制作初音未來等角色3D模組的免費軟件。
參考文獻
[1]喻國明,耿曉夢.試論人工智能時代虛擬偶像的技術賦能與擬象解構[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8(1):23-30.
[2]李毓婷.二次元角色偶像化:粉絲高度參與的符號構建[J].絲綢之路,2020(3):94-100.
[3]趙星植.論皮爾斯符號學中的傳播學思想[J].國際新聞界,2017,39(6):87-104.
[4]曹秋曄.國產虛擬偶像案例:東方梔子的推出與失敗[J].中國電視(動畫),2013(4):28-29.
[5]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9-200.
[6]愛奇藝全國創意策劃中心:《愛奇藝:2019虛擬偶像觀察報告》[EB/OL].[2021-05-10].http://www.199it. com/archives/1004591.html.
[7]歐文·戈夫曼.公共場所的行為:聚會的社會組織[M].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9.
[8]騰訊研究院.誰說虛擬偶像永不翻車[EB/OL].[2021-05-10].https://www.huxiu.com/article/4075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