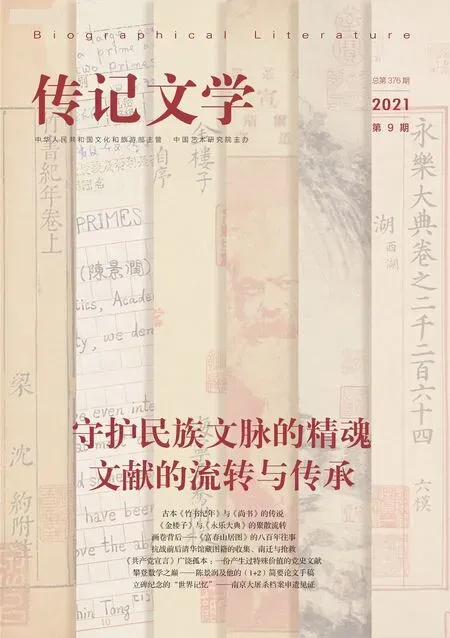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研究綜述
童志斌 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王佳藝 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本研究相關的文獻趨勢分析
關于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研究,針對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2001年到2020年年度立項課題名單,以“傳記”為搜索詞進行檢索,僅能搜索到2016年由嶺南師范學院鄭劍虹負責的一項題為《心理傳記學視角下杰出科學人才的成長特點與影響因素研究》的國家一般課題。在國家圖書館數據庫中以“高中傳記”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從2001年到2020年,獲得專著共154 本,多為高中傳記文學選修教材與選讀讀本。
這20年來,有關高中傳記文學的專著在總體上碩果累累,但是研究起步較晚,自2012年開始出現研究高潮,在2013年達到小高峰39本和2014年的36 本后,高中傳記文學作品專著的研究熱度明顯下降。同樣,與“傳記”相關內容的研究在2001年至2020年年度立項課題名單中僅有一項國家一般課題,不符合傳記文學作品應有的重要地位。

圖1 相關專著文獻趨勢圖
從學位及學術論文的發展趨勢來看,本研究以2001年至2020年為主要搜索階段,主要通過中國學術期刊網,選取“傳記教學”為篇名進行檢索,共獲得相關學位論文41 篇,均為碩士學位論文;相關核心期刊及以上學術論文30篇,其中核心期刊為4 篇,CSSCI 為1 篇;共有3 篇國內會議論文與1 篇國際會議論文;還有120 篇特色期刊文獻,共計195 篇文獻。相關趨勢如圖2所示:

圖2 相關學術及學位論文期刊文獻趨勢圖
2001年至2020年之間研究“傳記文學教學”的文獻并不少,且刊發的期刊論文數量分布總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說明傳記教學日益引發了學者們的注意。但研究的起步較晚,自2015年才有穩步上升趨勢,直至2018年達到小高峰,表明近五年學術界才開始重點關注傳記文學的教學。盡管近兩年來研究文獻數量又呈現下降趨勢,但傳記文學教學依舊值得學者們進行研究與探索。
研究內容分析
一、傳記文學作品的內涵研究
傳記文學作為一種自成格局且具有特殊性的文體,在20世紀便吸引了許多學者對其進行較為系統性的研究。值得關注的是在“傳記文學”的概念界定上,歷史真實性與文學藝術性成為界定傳記文學概念的兩大支架。李祥年將傳記文學定義為“一種融歷史學與文學為一體的藝術創作形式”。趙白生關注到傳記具有歷史屬性,但大量傳記又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虛構,他認為比較公允、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傳記是一種綜合,一種基于史實而臻于文的敘述,并在史與文之中達成一種由此及彼、彼此互構的關系。”此后,他針對傳記文學中文與史的關系作出進一步的闡釋,認為“文與史可以達到水乳交融、珠聯璧合的境界”。陳蘭村認為傳記文學是“藝術地再現真實人物生平及個性的一種文學樣式”,“真實”強調的是歷史的真實性,“藝術再現”與“文學樣式”則是對傳記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提出的要求。楊正潤更為直接地將“歷史性與文學性取得平衡的傳記”視作“主流傳記”,對傳記文學作品中的歷史性與文學性提出了更為明確的要求——即追求兩者的平衡。無獨有偶,全展認為“真實是傳記文學的生命”,“傳記文學要具備文學性的內涵,既包括描繪傳主形象時所用到的文學與藝術手段,還能對所寫歷史事件進行選擇與處理,最終使傳記的情節結構具備審美化特點”。筆者認為以上幾位學者的說法都敏銳地察覺到傳記文學作品一方面具備歷史真實性,描述的內容基于史實;另一方面具備文學性,其語言能夠體現鮮明的藝術特征,情節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基于史實的夸張和想象,富有文學價值。
傳記文學作品是契合傳記文學概念、兼有史學性與文學性的作品,對其發展脈絡的研究,學界大體達成了一致。傳記文學因子自《詩經》中萌芽,在諸子散文、屈原的《離騷》中生發出他傳與自傳這兩種文體。先秦傳記文學的雛形在《左傳》《國語》《戰國策》《晏子春秋》中可見一斑。司馬遷創作出《史記》則標志了傳記文體作為一種文學新體式的誕生,史傳文學由此走向了輝煌發展的時期。
此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傳文學由凝注創作者思想情感的記敘轉變為關注客觀史實的記載,其文學價值雖有所下降,但《列女傳》《裴氏家傳》等作品的問世豐富了傳記文學作品的類型,雜傳因此興起。唐朝經濟政治的空前繁榮、統治者修訂史書的需要以及古文運動的興起均提供了傳記文學發展的土壤,碑志傳記在這一時期蔚然成風。宋元時期的傳記文學更側重于說理與議論國家政治形勢,在文章內涵與藝術形勢上有所創新發展。明代市民傳記文學興起,傳主階級地位下移,審美取向逐漸向世俗化、趣味化發展,語言描寫更為通俗易懂。清代傳記文學作品大多充斥著激昂的民族情緒,在自傳體得以創新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傳記文學總體發展相較之于以往有所停滯的問題。
近代傳記文學的發展受到1840年外來侵略的影響,傳記創作者多不自覺地抒發感時憂憤的情感,開始由古代傳記文學向現代傳記文學過渡。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中國的現代傳記文學邁入了新時期,西方傳記文學作品帶來的啟迪和白話文的興盛使得傳記文學徹底擺脫了傳統模式,寫作的文體由文言文向白話文轉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當代文壇中,傳記文學作品依舊是一顆璀璨的明珠,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的“傳記熱”使傳記文學由初步復蘇走向繁榮興盛。
二、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的地位研究
有學者指出傳記文學閱讀教學已經被推上了高中新課改浪潮的浪尖,素質教育的實現必須要踐行傳記文學的教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的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方面,從入選語文教材的傳記文學篇目數量來看,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級中學語文》全6 冊中共有文言文課文48 篇,其中傳記文學作品13 篇,占據四分之一,且類型豐富:有選自《史記》的《廉頗藺相如列傳》《鴻門宴》這類史傳,也有《譚嗣同傳》《柳敬亭傳》這類專傳,還有《五人墓碑記》此類雜傳。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教新版教材中的傳記文學精讀篇目從舊版教材中的2 篇增加至5 篇,可見教材編者將傳記文學作品視作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伴隨新課程改革的形勢,為傳記文學作品專門開設了選修課程,編制了大量的選修教材,如人教版有《中外傳記作品選讀》,蘇教版有《傳記選讀》和《〈史記〉選讀》,語文版有《名人傳記選讀》《中外優秀傳記選讀》,粵教版有《傳記選讀》,魯人版有《〈史記〉選讀》。無論是必修教材中入選傳記文學作品的數量逐漸增加,還是為傳記文學教學專門編制選修教材,均可證明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三、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的功能研究
傳記作為我國古代歷史的一種呈現方式,同時是我國文學最早的表現形式,眾多學者均關注到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的過程中完善學生人格、啟迪學生思考的重大價值。
有學者認為學生初讀傳記文學作品能從中感受到魅力,激發閱讀興趣,還能培養人文情懷,提升情感品質,達成教學中“育人”的目標。劉俊柱和穆慧強調了傳記文學作品的閱讀教學對青少年人格養成所產生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傳記文學作品本身的內容能夠啟發學生思考如何與自我與自然、與社會相處,是青少年人格養成、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增強直面挫折時的勇氣與信心、培養樂觀主義精神并完善心理素質的最佳教材;另一方面,在傳記文學閱讀教學過程中能夠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個人教育,自然地引導學生學習傳主的高尚人格,并培養學生對傳記文學作品的興趣,將課堂延伸至課外。此外,傳記文學作品能發揮啟迪學生智慧的積極作用,結合教師有策略地講授傳記文學的相關知識,學生的文化底蘊得以充實,并能通過分析歷朝歷代的成敗興衰之理增強憂患意識與生命意識。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的功能基本可概括為:(1)歷史記憶功能,能夠幫助學生了解真實歷史情境;(2)激勵奮進功能,能增長學生志氣,引導學生以優秀的傳主為榜樣,學習其品行;(3)文學欣賞功能,傳記文學作品尤其是文言文傳記作品,往往在寥寥數語中刻畫出鮮明的人物形象,其以小見大的春秋筆法、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極具審美價值,能夠陶冶學生的文學素養。
四、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現狀研究
1.取得的成效
近幾年學術界對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頗為關注,尤其是在教材中傳記文學作品數目逐漸增多后,以及諸如肖培東等語文名師率先關注到傳記文學作品其獨特的文體對培養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塑造學生的健全人格等顯著作用后,針對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的研究正朝著多角度、多層次的方向發展。
在浙江省特級語文教師肖培東教學《美麗的顏色》和《偉大的悲劇》這兩篇傳記文體的初中部編本課文后,許多學者深受啟發,并進一步思考如何進行傳記文學作品的閱讀教學。這兩篇課文雖為初中課文,但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依舊能從其中覓得可供借鑒之處。肖培東在把握了《偉大的悲劇》的傳記文體并充分研究了茨威格的傳記風格后,肯定了本篇傳記兼有文學性和歷史性的雙重特點,將對傳主的細節描寫和作者豐富想象力的體味作為教學的重點內容。肖培東利用生成的課堂情境,針對某一位學生認為“作者是在胡編亂造”這一錯誤觀點,引導學生感受到茨威格的傳記文學是依托歷史事實,輔之以合理的想象而進行創作的。
林忠港、郭躍輝、李漫飛等學者的主張均肯定了傳記文學作品的體式在教學中應有所呈現。林忠港主張“傳記教學應該走自己的路”,他將教材中的課文分為“虛構作品”與“非虛構作品”,因傳記文學作品具備基于史實出發、以文學性貫通敘述的特點,故構成了“非虛構作品”在教材中的“主力軍”。此種“虛構與非虛構”的歸類方式與趙白生的觀點不謀而合,他提出事實是界定傳記文學的一個關鍵詞,并根據不同文體對事實的敘述策略將小說、戲劇和詩歌劃分為虛構性作品,將傳記、歷史和報道歸為非虛構性作品。李漫飛將教學內容選定的首要標準定為傳記體式,強調教師要依據傳記的文體特征選擇教學內容,不能將傳記文學體式與小說簡單地等同起來。他從肖培東教學《美麗的顏色》課例深受啟發,據此總結了傳記文學教學內容選擇的共性,需要著重體現傳記的“四性”即敘事性、真實性、歷史性與文學性,并力求在閱讀傳記文學作品的過程中使學生獲得精神上的啟迪與激勵。郭躍輝進一步肯定了傳記作者的價值選擇在一定程度上能對學生的思想、價值觀造成影響,創作時刻意為之的文學視角能在行文符合科學嚴謹的邏輯與史實的同時增添文學價值,并且關注到傳記文學作者與敘述者的身份常常重合。
除了對名師教學傳記文學作品實錄進行研究,有學者采用問卷調查法針對高中學生發放問卷,同時從教師角度編制了問卷。通過對調查結果分析發現,所有教師對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的重要地位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并肯定了傳記文學作品對學生語文修養的提升和人格的塑造均能起到積極作用;絕大部分學生能夠感知到傳記文學作品與其他體裁的作品有區別,能夠體會到傳記文學作品的獨特性。
此外,有研究者實地進行了以傳記文學作品為單元的選修教學模式改革。北京五中教師王屏萍和北京原地安門中學教師邊曄自2008年寒假起進行籌備,在3 至4月開創性地根據學生自身的興趣與需要開設了“史傳文學”專題教學活動。該課程目標明確指出在閱讀與鑒賞的過程中,引導學生領會鑒賞傳記文學的基本方法,提升學生的文言文閱讀能力,發展文學審美與探究能力。該課程培養了學生對史傳文學的閱讀興趣,豐富了閱讀體驗,對陶冶學生的性情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2.尚存的問題
盡管傳記文學作品在語文閱讀教學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并且學界已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實際教學中尚且存在一定的問題亟待解決。如針對《廉頗藺相如列傳》這篇出自《史記》的經典傳記文學作品,學者安孝采用小說視角審視這篇經典選文,不再單純地將其視作文言文進行教學。他雖已將本文定性為人物傳記,但在教學內容的選取上他僅選擇《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塑造人物的方法作為學習本文的教學支架,并引導學生從中掌握現代小說的相關知識,這顯然有失偏頗。
筆者認為以小說視角進行教學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學生應具備的傳記文體意識,同時違背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初衷。陳蘭村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將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成一家之言”作為他創作《史記》的最大目的,司馬遷借由一篇篇身份各異的人物傳記表達自身的思想主張,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言:“述往事,思來者。”因此,僅從小說視角學習《廉頗藺相如列傳》是片面的。無獨有偶,梁啟超在《名人傳記》中的《管子傳·自傳》篇直言:“夫導國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學其先民,則史家之職也。”梁啟超在進行傳記文學創作時有意識地將“教導”“教化”國民為己任。傳記文學作品雖多具備優秀小說的因素,但其教育目的與作用依舊不容忽視,故不可將傳記文學簡單地套進小說模式進行教學。
即便教師在閱讀教學中能夠準確把握傳記的文體,教學傳記文學作品時還會產生語文的“工具性”與“人文性”失衡的問題,在古典傳記作品教學時,教師“重言輕文”的情況時有發生。具體表現為教師在傳記文學閱讀教學的過程中過于重視文言文這一文體,力求厘清句意,忽視了傳記文學作品文學性的特征,造成學生對傳主的人生歷程、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一無所知,更無法激發學生向優秀傳主學習的主動性。有研究者提出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重言輕文”問題根源于高考試題編制的影響,教師通過研究高考中傳記文學作品的命題重點,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側重實詞、虛詞、斷句、翻譯等重要考點,忽視了傳主的優秀品質。該看法切中了部分傳記文學閱讀教學喪失人文性的原因。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同“教學大綱”與“課標”在文言文課程目標上所長期堅持的“實用取向”有必然關系。
五、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策略研究
基于高中語文傳記文學閱讀教學的現狀,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相應的教學策略,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依據語文課堂教學的不同階段采取六種教學策略,即聯系解讀法、誦讀體味法、品讀賞析法、比較探究法、對話教學法、活動教學法。有學者指出在導入階段,教師可采用聯系法對傳記文學作品進行較為全面的解讀,聯系創作的時代背景、傳主的寫作背景及生平經歷,豐富學生的知識儲備,幫助學生走近傳主。在初讀階段,對傳記文學作品尤其是文言文傳記作品進行吟誦,讓學生通過誦讀感受樂感美和文字美。在精讀階段,以對話的形式進行教學,一面對傳記文學作品進行細讀,抓住典型事件,分析作者采用的側面烘托手法;一面進行比較與探究活動,比較同一傳主的不同作者傳記作品、相同題材的不同文體的作品、影視片段與傳記文本。與此同時,教師還應在教學活動時組織多種活動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如觀賞視頻、開設講座、開展辯論賽、舉辦演講比賽、表演課本劇、舉辦成果展示欄。
第二類,依據傳記教學所設置的教學目的采取契合目的的閱讀教學策略,教學目的即讓學生了解該文體的特征、尋找人生的榜樣、培養語文素養、形成自身的感悟并能夠發表自己的看法。胡俊主張采用拓展比較閱讀法,比較不同傳記的優劣或特色、傳記素材選擇和作者的關系、他人和史料的評價,并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既要全面認識課文,理解“藝術真實”的內涵,引導學生公正地看待傳主;又要樹立大語文教學觀,夯實學生的文史知識積累。
第三類,從《普通高中課程實驗標準》的要求出發,有研究者認為教學策略應在激發學生興趣的基礎上抓住典型細節對傳主形象進行賞析,教師要有意識地選擇獨特的傳記文學作品進行拓展教學補充,并教給學生采用“互文”的策略建構對傳主新的理解。
第四類,從教學設計思路出發,陳麗主張在教學目標設定時關注對傳記文學作品的鑒賞與積累,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側重于“讀”的教學,尤其指出在教學環節中針對單篇課文要進行時間前后、人物行為乃至性格變化的串聯、多篇課文要進行比較和整合分析。
由此可見,針對高中語文傳記文學閱讀教學,學界普遍認為以下三種策略較為有效:一、聯系拓展法,往往在課堂導入階段使用,教師通過補充課外資料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并促進學生了解傳主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二、比較閱讀法,既包含多篇傳記文學作品中對同一傳主的不同作者的傳記作品,也包含在單篇傳記文學作品中傳主在時間發展中的前后變化。三、個性解讀法,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在閱讀傳記文學的過程中生成自己獨特的見解并勇于表達,在溝通與探討中完善人格塑造。
綜上所述,通觀中國傳記文學作品研究近20年的發展和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的閱讀教學策略,兩者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從現實角度來看,高中語文傳記文學作品閱讀教學雖存在著許多學者尚未討論過的問題,但傳記文學閱讀教學的實踐經驗積累和傳記文學作品本身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對傳記文學作品定義的詮釋和發展歷程的溯源共同構成了廣闊的學術沃土,值得廣大語文教師借鑒、參考、學習。
注釋:
[1]陳蘭村:《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 頁。
[2]李祥年:《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 頁。
[3]趙白生:《傳記里的故事——試論傳記的虛構性》,《國外文學》1997年第2 期。
[4]趙白生:《一沙一世界——論傳記主人公的選擇與整體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第5 期。
[5]陳蘭村:《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語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 頁。
[6]楊正潤:《論傳記的要素》,《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6 期。
[7]全展:《傳記文學:思考與觀察》,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36 頁。
[8]韓兆琦:《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略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4 期。
[9]唐龍:《淺談高中語文傳記文學的教學》,《中學時代》2014年第20 期。
[10]徐四英:《高中傳記教學初探》,《學理論》2010年第35 期。
[11]劉俊柱、穆慧:《傳記文學教學與青少年人格養成》,《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4 期。
[12]肖培東:《依體教讀,水到渠成——〈偉大的悲劇〉教學思考》,《語文建設》2019年第23 期。
[13]林忠港:《傳記教學內容的確定與呈現——以〈美麗的顏色〉為例》,《語文建設》2019年第23 期。
[14]趙白生:《“心靈的證據”——傳記事實的本質》,《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3 期。
[15]李漫飛:《從文體看傳記的閱讀教學——肖培東〈美麗的顏色〉課例研究》, 《北方文學》2019年第20 期。
[16]郭躍輝:《從作者視角解讀〈偉大的悲劇〉》,《語文建設》2018年第25 期。
[17]安孝:《廉頗藺相如列傳的教讀》,《語文教學與研究》1993年第11 期。
[18]陳蘭村:《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語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3 頁。
[19]梁啟超:《名人傳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 頁。
[20]胡俊:《高中語文傳記文學的教學策略》,《語文教學之友》2013年第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