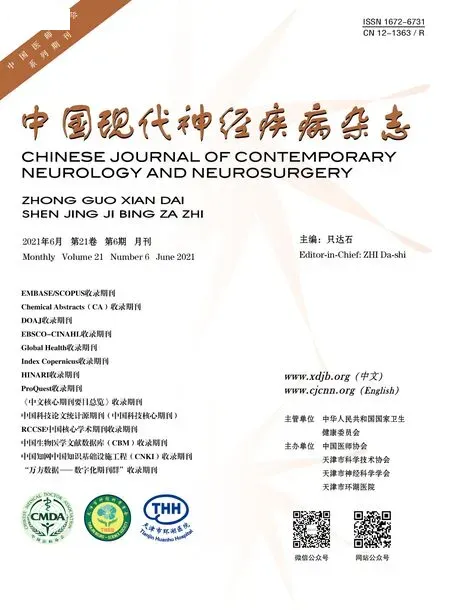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6型一家系
楊云鵬 劉佳 王魯寧
先證者 女性,41歲。主因頭暈、行走不穩、言語不清4年并進行性加重2年,于2016年5月21日入院。患者4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頭暈、步態不穩、步基增寬等癥狀,但尚能獨立行走,同時伴有言語不清,語調、語速改變,近2年來不僅新增飲水嗆咳,而且上述癥狀呈進行性加重,多次于外院就診,均以腦供血不足而予血塞通、天麻素等藥物治療,但病情仍不斷進展,為求進一步診斷與治療,遂至我院就診,門診以頭暈原因待查收入神經內科。自患病以來,精神稍差,睡眠可,飲食正常,大小便正常,體重無明顯變化。
既往史、個人史及家族史 既往身體健康,否認特殊慢性疾病病史,父母非近親婚配。其父現年73歲,身體健康,其母71歲,于33歲出現行走不穩癥狀;另有兄弟姊妹5人,除三兄30歲時死于車禍,長兄目前尚未發病,其余3人中二姐現年51歲、四兄43歲、六弟39歲,均于36歲時出現與先證者相類似的癥狀;先證者母親及二姐因下肢運動障礙失去行走能力。
診斷及治療經過 入院后體格檢查:神志清楚,對答切題,呈爆破性語言,雙眼各向活動正常,可見粗大的水平眼震。行走時步基增寬,四肢肌力正常,肌張力減低;雙側肱二頭肌反射、肱三頭肌反射、橈骨膜反射、跟-膝-腱反射存在。雙側指鼻試驗欠穩準,雙側快復輪替試驗笨拙,跟-膝-脛試驗欠穩準,直線行走不能,Romberg征陽性,肌回縮實驗(反擊征)陽性。雙上肢意向性震顫。雙側掌頜反射陽性,右側Babinsik征陽性,左側Babinsik征、雙側Chaddock征陰性。深淺感覺正常,腦膜刺激征陰性。洼田飲水試驗2級。神經功能量表檢查:經征得先證者及其母、二姐、四兄、六弟知情同意,均于我院接受國際協作共濟失調評價量表(ICARS)檢查,檢查結果顯示:總評分分別為44、84、64、26和25,其中姿勢和步態障礙靜態評分為18、32、26、9和8,動態肢體協調評分為21、44、30、13和13,語言障礙評分為3、4、4、2和2,眼球運動障礙評分為2、4、4、2和2(表1)。先證者實驗室各項檢查指標均無明顯異常。心臟、頸部血管及腹部彩超檢查無異常發現。影像學檢查:先證者T2WI平掃顯示小腦萎縮,以小腦蚓部明顯,腦干輕度萎縮(圖1a)。根據家族史分別對先證者之母、二姐、四兄、六弟進行MRI檢查,其四兄及六弟既往保存有完整的MRI檢查資料,亦呈小腦萎縮表現(圖1b,1c)。結合先證者家族史、臨床特征、影像學檢查結果,考慮遺傳性共濟失調疾病,且符合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疾病遺傳特點。在征得先證者及其子女,家族中其父母、長兄及其子、二姐及其女、三兄之子女、四兄及其子、六弟及其子女共16人知情同意,采集靜脈血5 ml,采用聚合酶鏈反應(PCR)聯合毛細管電泳(CE)法對臨床常見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SCA)1、2、3、6、7、12、17型,以及齒狀核紅核蒼白球路易體萎縮(DRPLA)等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共濟失調(ADCA)亞型進行基因檢測(北京金準基因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結果顯示:先證者(Ⅱ9)CACNA1A基因的1個等位基因CAG拷貝數超出正常范圍,為23次;家族中先證者之母(Ⅰ2)、二姐(Ⅱ3)、四兄(Ⅱ7)、先證者之女(Ⅲ9)、六弟(Ⅱ11)及其子(Ⅲ)11共6人存在CACNA1A基因CAG重復擴增,擴增次數均超出正常范圍,為23次,符合SCA6型致病特點,該家系明確為SCA6型家系(圖2)。治療原則以營養神經、促進神經細胞代謝為主,予以胞二磷膽堿0.50 g/d靜脈滴注、輔酶Q10口服10 mg/次(3次/d)、丁苯肽口服200 mg/次(3次/d)。患者共住院10天,出院時頭暈、行走不穩、構音障礙等癥狀無明顯改善,出院后繼續口服胞二磷膽堿200 mg/次(3次/d)和銀杏葉提取物40 mg/次(3次/d)。3個月復診時,癥狀與體征仍如前。

圖1 頭部橫斷面T2WI顯示小腦萎縮,以小腦蚓部明顯;腦干輕度萎縮(箭頭所示) 1a 先證者 1b 先證者四兄 1c先證者六弟Figure 1 Brain imaging showed cerebellar atrophy on axial T2WI,especially in vermis and mild atrophy in brainstem(arrows indicate) The proband(Panel 1a).The fourth brother of the proband(Panel 1b).The sixth brother of the proband(Panel 1c).

圖2 SCA6型家系圖Figur e 2 The SCA6 pedigre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patient's family.

表1 SCA6型家系ICARS量表檢查結果Table 1.Results of ICARSscale of SCA6 pedigree
討 論
遺傳性共濟失調是一大類具有高度臨床和遺傳異質性、病死率和病殘率均較高的遺傳性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占神經系統遺傳性疾病的10%~15%[1]。遺傳性共濟失調多于成年期(>30歲)發病,以小腦性共濟失調為主要特征,表現為平衡障礙、進行性肢體協調運動障礙、步態不穩、構音障礙、眼球運動障礙等,同時可伴有舞蹈癥、帕金森樣癥狀、肌張力障礙等錐體外系癥狀[2],以及錐體系、視覺、聽覺、脊髓、周圍神經損害,亦可伴大腦皮質功能損害如認知功能障礙和(或)精神行為異常等。本文家系三代共16人接受基因檢測,其中先證者母親、二姐、四兄、六弟及其子、先證者及其女共7例存在CACNA1A基因變異,其中先證者及其母、二姐、四兄、六弟共5例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小腦性共濟失調癥狀,發病年齡為33~37歲,該家系第三代2例CACNA1A基因變異攜帶者年齡<18歲(分別為9歲和12歲),目前尚無臨床癥狀,符合成年期發病之特點。與其他SCA類型相比,SCA6型發病較晚。本文家系中5例患者均接受ICARS量表檢查,該量表是半定量化的神經功能評價量表,可以描述和定量評價典型的小腦性共濟失調癥狀,包括姿勢和步態障礙評分、動態功能評分、語言障礙、眼球運動障礙評分,總分為100,評分越高,提示協調功能障礙越嚴重,本文家系中以先證者母親ICARS量表評分最高,其次為其二姐、先證者、四兄、六弟,5例患者的評分均與其病程相關。該家系患者語言障礙和眼球運動障礙相對步態障礙、肢體協調癥狀要輕,且均以步態異常為首發癥狀并進行性加重,其中年齡較大的先證者之母及其二姐目前已不能獨立行走,提示SCA6型病例大多以步態共濟失調發病且可導致嚴重殘疾。研究表明,SCA6型患者在臨床癥狀出現之前即已存在選擇性步態障礙,其步態障礙對疾病進展具有較高的敏感性[3],且平衡障礙與其疾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是SCA6型臨床綜合征進展的特征性表現[4]。本文先證者洼田飲水試驗為2級,家系中所有患者均無明顯吞咽困難、飲水嗆咳主訴。來自日本的一項研究表明,SCA6型患者所表現的吞咽困難通常比SCA3型輕,該研究經對14例SCA6型患者進行反復的熒光透視檢查(videofluoroscopic examinations)發現,其吞咽困難總體進展十分緩慢[5]。國內文獻曾報道SCA6型兩家系臨床表現特點:(1)遺傳早現現象。(2)于中年期發病,病程進展緩慢,癥狀相對較輕。(3)軀干和(或)肢體共濟失調。(4)慢眼活動。(5)假性延髓麻痹。(6)眼震。(7)意向性震顫。(8)腱反射減弱或活躍。(9)病理征陰性。(10)頭部MRI顯示小腦萎縮,而腦干基本正常[6]。本文家系臨床特點與上述基本相似,但也存在一些差異,本文家系未見明顯的遺傳早現現象,頭部MRI可見小腦萎縮,以小腦蚓部明顯,腦干輕度萎縮;且病理征呈陽性。國外也有文獻報道,SCA6型患者小腦蚓部萎縮較半球更為嚴重,且可累及腦干,類似于橄欖腦橋小腦萎縮(OPCA)改變[7]。本文首次報告我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SCA6型家系且病例數較多,共16人行SCA1、2、3、6、7、12、17,以及DRPLA亞型相關基因檢測,其中7例CACNA1A基因存在異常擴增,為大理地區遺傳性共濟失調流行病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SCA6型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藥物,臨床上仍以對癥和支持治療為主,主要目的是減輕癥狀、延緩病情進展,改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主要治療藥物包括神經保護劑輔酶Q10、艾地苯醌、利魯唑等,雖然這些藥物的神經保護效果尚有待證實,但有研究顯示,利魯唑具有改善遺傳性共濟失調患者運動障礙癥狀的作用[8-9]。對癥治療藥物包括丁螺環酮、坦度螺酮,可改善患者共濟失調癥狀;左旋多巴及其復合制劑、苯海索、金剛烷胺等則用于改善錐體外系癥狀。非藥物治療主要包括神經康復、經顱磁刺激、心理治療等。此外,基因治療和干細胞移植亦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尚待進一步研發。
利益沖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