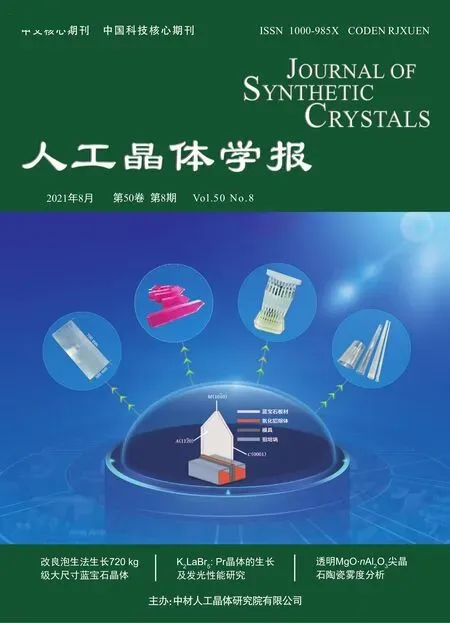Demko-Sharpless 合成稀土四唑化合物的結構及性質
應婷婷,韓定沖,譚育慧,李玉孔,黃 珺,唐云志,杜鵬康,莊加昌
(江西理工大學材料冶金化學學部,贛州 341000)
0 引 言
Sharpless等[1]開創了一種簡單安全又環保的合成四氮唑化合物的方法后, 利用原位反應合成四唑有機配體成為研究熱點。四氮唑環上具有四個可配位的氮原子,因此具有豐富的配位模式,既可以以橋聯的方式與金屬離子配位,也可以以螯合的方式與金屬離子配位。此外,在進行配位反應時四氮唑環上唯一的N-H基團的氫原子通常情況下會離去,使整個配體顯負電性,同時四個N原子的電荷密度分布均勻,這導致所有氮原子的配位能力大致相同。即四氮唑配體具有多種配位模式與金屬離子進行配位(見圖1)。

圖1 四唑配體的部分配位方式Fig.1 Possible coordination modes of tetrazole

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本課題組利用氰基吡啶(4-氰基吡啶和3-氰基吡啶)與稀土鹽作用,已經合成了四個稀土四唑離子型化合物,它們分別為([Ln(H2O)8·3(p-TPD)·2(p-HTPD)·7H2O], (Ln=Nd, Eu, Yb,p-TPD=4-tetrazoylpyridine), [Ln(H2O)8·3(m-TPD)·6H2O], (m-TPD=3-tetrazoylpyridine, Ln=Yb)[5]。為了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所以本文以Ln3+為Lewis酸催化劑, 利用4-氰基吡啶(3-氰基吡啶)為配體, 選擇Ln3+代替過渡金屬鹽作為Lewis酸, 進行[2+3]環加成反應, 然后程序降溫冷卻至室溫, 成功合成了四個目標產物(見圖2)。值得一提的是, 目標產物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四唑配合物, 所有的稀土配合物(1~4)均為離子型, 中心金屬陽離子[Ln(H2O)8]3+在內層, p-TPD和p-HTPD陰離子在外層, 內外兩層由氫鍵相互連接。同時,利用單晶X射線衍射分析、紅外光譜分析、熱重分析、介電性能分析、X射線粉末衍射分析等對目標產物進行了表征[18-21]。
1 實 驗
1.1 晶體生長
化合物1的合成如圖2所示。化合物1是在水熱反應下制備的, 將4-氰基吡啶(0.020 8 g, 0.2 mmo1)、NaN3(0.039 g, 0.6 mmo1)、La(NO3)3·6H2O(0.065 g, 0.2 mmol)和去離子水(2.5 mL)的混合物加入到一根硬質Pyrex管中,抽真空后密封,再放入150 ℃的干燥箱中烘干72 h, 靜置緩慢冷卻到室溫,得到粉色塊狀晶體。計算出產品產率:30.1%(以4-氰基吡啶計算);元素分析C30H52N25O15La (1 141.88):實驗值(%) C, 31.56; H, 4.55; N, 30.67; 理論值(%) C, 31.39;H, 4.61; N, 30.82。化合物2~4的合成步驟與化合物1的相同,把La(NO3)3分別換成Gd(NO3)3、Er(NO3)3和Er(NO3)3。

圖2 (a)化合物1~3的合成路線, Ln=La(1), Gd(2), Er(3);(b)化合物4的合成路線,Ln=Er(4)Fig.2 (a) Synthesis route of 1~3, Ln=La(1), Gd(2), Er(3); (b) synthesis route of 4, Ln=Er(4)
1.2 性能測試
將化合物1(0.560 mm×0.400 mm×0.300 mm)、化合物2(0.800 mm×0.600 mm×0.500 mm)、化合物3(0.600 mm×0.400 mm×0.200 mm)、化合物4(0.660 mm×0.500 mm×0.460 mm)的單晶置于BrukNer P4單晶衍射儀上, 采用經石墨單色器單色化后的Mo Kα射線(λ=0.071 073 nm)進行X射線測量, 各衍射數據在293(2) K測試溫度下, 以θ-2θ掃描方式收集不同衍射范圍內的衍射數據。使用SADABS[22]程序, 全部強度數據經Lp因子和經驗吸收校正。晶體結構用直接法獲得,經過幾輪精修后, 所有氫原子坐標由差值Fourier合成法得到。所有非氫原子坐標采用各向異性熱參數法,并通過全矩陣最小二乘法進行優化。所有計算均通過SHELXL-97晶體結構分析程序包來完成。晶體學信息文件可以從劍橋晶體學數據庫獲得,CCDC:911647,1;911646,2;941826,3;941828,4。熱重分析(TGA)在TA儀STD2960系統上進行測定,其溫度以10 K/min的速率從室溫增加到1 300 K。PXRD衍射測試是在室溫,發生器電壓(40 kV)和管電流(40 mA)下,使用5.0°~50.0°的連續掃描類型,用銅輻射(Kα1=0.154 060 nm,Kα2=0.154 443 nm)測量。
2 結果與討論
2.1 合成討論
化合物1~4均是在水熱反應下制備, 實驗表明稀土鹽的類型、化學反應物的起始濃度、體系的pH值以及反應溫度等因素對產物晶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以不同的稀土金屬鹽做前驅體, 利用Demko-Sharpless反應,選擇可以提供易與金屬配位的氮原子的4-氰基吡啶(3-氰基吡啶)為配體, 進行[2+3]環加成反應, 得到一系列稀土化合物。如圖2所示, 將4-氰基吡啶(或3-氰基吡啶)、NaN3及Ln(NO3)3原位合成,得到四個化合物:[Ln(H2O)8·3(p-TPD)·2(p-HTPD)·7H2O ](Ln=La(1)Gd(2), Er(3))和Ln(H2O)8·3(m-TPD)·6H2O(Ln =Er(4))。
2.2 化合物1~4的結構

化合物1~4均為離子型,稀土金屬離子與配體分別處于不同的兩層,即中心金屬陽離子[Ln(H2O)8]3+在內層,p-TPD和p-HTPD陰離子為外層(見圖3(c)和3(d))。另外,在金屬陽離子[Ln(H2O)8]3+之間仍然存在p-TPD陰離子,這使得金屬陽離子為線性結構。如圖3(d)所示,化合物1~4中存在豐富的氫鍵和π-π堆積相互作用。從b軸上看,稀土金屬離子[Ln(H2O)8]3+與一個4-四唑吡啶配體形成氫鍵(O(2)-H(2A)…N(20)#3(0.282 9(7) nm);游離結晶水和吡啶環上的氫形成氫鍵O(6 W)-H(6 WB)…N(16)#10(0.293 9(9) nm);同時配位水和游離結晶水分子間氫鍵O(5)-H(5B)…O(1 W)#5(0.262 9(6) nm)形成了一條稀土金屬陽離子鏈。另外,4-四唑吡啶配體在氫鍵(N(6)-H(6)…N(21)#1(0.266 5(7) nm);N(1)-H(1)…N(11)#2(0.270 5(7) nm)連接成一條配體陰離子鏈。兩條鏈狀結構交替排列,再通過游離水分子間的氫鍵(O(1W)-H(1WB)…N(3)#8(0.279 7(6) nm);O(2W)-H(2WA)…N(22)#10(0.275 5(7) nm)作用而沿b軸無限擴展成二維網狀結構。值得注意的是,相鄰的四唑(0.367 2 nm)以及四唑和吡啶環之間(0.365 2 nm)存在著π-π堆積作用,化合物在氫鍵及π-π堆積的共同作用下堆積成一個三維網狀結構(見圖4)。

圖3 (a)化合物1中心金屬離子LnIII的結構圖;(b)化合物4中心金屬離子LnIII的結構圖; (c)化合物1的離子層結構; (d)化合物4的離子層結構Fig.3 (a)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metal ion LnIII of 1; (b)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metal ion LnIII of compound 4; (c) ionic layers structure of compound 1; (d) ionic layers structure of compound 4

圖4 由氫鍵連接的1的三維網絡結構(a)及π-π堆積圖(b)Fig.4 Three-dimensional network structure (a) and π-π stacking diagram (b) of 1 connected by hydrogen bonds
2.3 熱重測試和粉末衍射測試
從化合物1~4熱失重曲線(見圖5)可知,所有的化合物都具有相似的失重趨勢, 化合物1的第一個凈失重過程發生在70~120 ℃范圍內(失重約11.94%),這與所計算得到的化合物中所含的游離水的重量相當(11.03%,以一個結構單元計算),表明化合物1中的游離水分子被剝離。隨著溫度的持續升高,化合物1的第二個失重過程發生在180~230 ℃范圍內(失重約17.23%%),這表明化合物1中配位水分子(12.61%,以一個結構單元計算)已經從化合物中移除,整個化合物的結構遭受到破壞。化合物1~4具有相似的失重情況。化合物1~4粉末衍射譜圖(見圖6)表明:實驗測得的結果與通過單晶X射線衍射數據擬合的譜圖吻合較好, 只是在強度方面有略微差別, 說明化合物均為純相。

圖5 化合物1~4的熱重(TGA)分析曲線Fig.5 Thermo gravimetric analysis(TGA)of compound 1~4

圖6 化合物1~4的粉末衍射譜圖Fig.6 Powder XRD patterns of compound 1~4
2.4 介電常數測試
介電常數的溫度系數是指在一定范圍內,溫度每升高1 ℃時介電常數的相對平均變化率。介電性能是在電場作用下材料所表現出的對靜電能的儲蓄和損耗的性質[24]。其中的介電常數與溫度之間的關系主要由以下兩個公式所表明[25]:
(1)
(2)
式中:Σ為介電常數;f為頻率;N為分子數;S為熵;λ為導熱系數;q為電量;e為電子電荷;r為半徑;p為極化強度;α為極化率;β為正離子電離系數;k為玻爾茲曼常數。
從公式(1)和(2)可知,介電常數Σ與溫度主要有兩種關聯效應(λ3和λ4),λ3代表的是熱膨脹作用。在低介電常數的材料(通常Σ<20)中介電常數的數值主要由λ3控制,故當晶格膨脹即相互作用被削弱時,介電常數與溫度成正比。化合物1和2的測試結果與上述結論類似,化合物1和2的電容值分別在180 ℃和200 ℃下發生明顯的轉變。由圖7可知,在相變發生前,溫度從90 ℃升到200 ℃時,化合物2的介電常數逐漸增大,但在200 ℃下電容值卻發生明顯的轉變。對照熱重分析曲線(TGA)推斷,該轉變過程可能是由于在200 ℃時化合物2中的配位水分子從結構中移除, 整個配合物的結構發生破缺,即發生相變。相變的發生伴隨著化合物的電容值在該相變溫度下發生明顯的轉變,并導致介電常數在相變溫度下隨頻率的變化而出現顯著波動[26]。由此可以得出化合物2在200 ℃時電容值的變化是由相變導致的。

圖7 1,2不同溫度下的介電常數與頻率的關系曲線圖Fig.7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1, 2 measured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i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3 結 論
以稀土硝酸鹽(硝酸鑭、硝酸釓、硝酸鉺)為Lewis酸催化劑,4-氰基吡啶(3-氰基吡啶)為主配體與疊氮化鈉,在水熱條件下發生Demko-Sharpless原位反應成功合成了四個新穎的稀土四氮唑化合物,分子式為[Ln(H2O)8·3(p-TPD)·2(p-HTPD)·7H2O)],Ln(H2O)8·3(m-TPD)·6H2O(Ln=La(1), Gd(2),Er(3,4))。晶體結構分析表明,這四個稀土四唑化合物均為離子型,是由稀土陽離子與八個游離的水分子進行配位構成的雙帽三棱柱的八面體幾何構型,而且稀土金屬離子與配體分別處于不同的兩層,[Ln(H2O)8]3+結構單元與 p-TPD 以及水分子通過氫鍵作用形成陽離子層,同時 p-TPD 與 p-HTPD 通過π-π堆積與氫鍵作用形成陰離子層,陽離子層和陰離子層交替排列形成一個規則的網絡結構。由介電測試結果得出,化合物1,2的電容值分別在180 ℃、200 ℃溫度下發生了轉變,這種介電常數異常主要是由化合物發生相變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