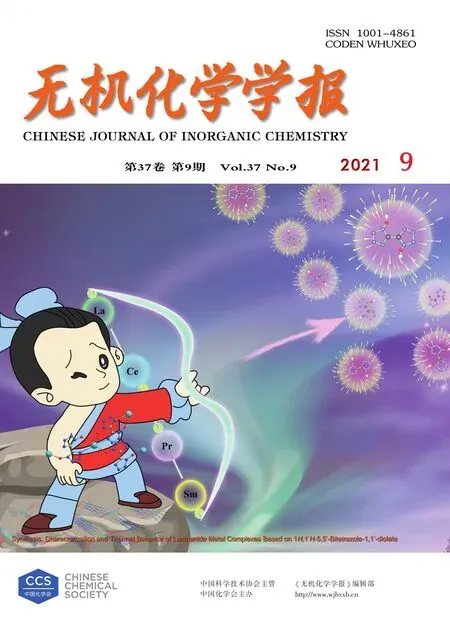Cu/MoS2的熔鹽電解法制備及其在堿性條件下析氫反應性能的提高
王子鳴 盧雅寧 唐 夢 張 爽 王英財 張志賓 劉云海 柳玉輝
(東華理工大學核資源與環境國家重點實驗室,南昌 330013)
0 引言
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對于能源的依賴性日益增加。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化石燃料能源在地球中的含量有限,并且屬于非再生能源,所以尋找一種儲備含量豐富的可再生新能源就成了重中之重[1]。與其他化石燃料相比,氫氣在燃燒過程中不會產生有毒氣體[2?3],而不同于傳統方法的電解水析氫反應(HER)成為了首選的制氫方法。但是由于其反應動力學過程緩慢,通常在HER過程中需要添加高活性的催化劑來提高催化效率并增加催化產物。目前而言,一些貴金屬(如Pt[4])由于吸附氫的吉布斯自由能小以及自身優越的選擇性和穩定性等原因,是目前性能較好的催化劑,但由于其價格昂貴、儲備量稀少,很難實現商業和工業化應用。
近幾十年來,非貴金屬二維材料由于其獨特的電學、光學以及廉價的特性,已經被廣泛應用于HER中,其中被研究較多的是過渡金屬硫族化合物(TMDs)。而二硫化鉬(MoS2)作為二維TMDs中的典型代表,已被科學家廣泛研究。Hinnemann等[5]通過密度泛函理論(DFT)計算發現,Mo原子吸附氫的吉布斯自由能與貴金屬Pt相接近,因此推測其可能具有優異的析氫催化活性;Raybaud等[6]使用ab initio算法發現MoS2的二維平面面內是惰性的,活性位點在其邊緣上;而 Bonde和 Jaramillo等[7?8]先計算MoS2中Mo和S原子邊緣吸附氫的吉布斯自由能并測試其電化學性能,再通過掃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MoS2納米粒子邊緣的長度,進一步證實MoS2的反應活性位點確實是邊緣。盡管如此,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驗結果也表明MoS2存在著一些問題[9?12]:首先,MoS2的基底面是催化惰性的;其次,MoS2的電子遷移率和導電性較差;最后,由于在合成MoS2材料過程中很容易發生聚集現象,這會覆蓋有用活性位點,而且想要同時得到具備較高的導電性和較多的活性位點是比較困難的。這些問題也進一步限制了MoS2作為HER催化劑的應用。
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們發現通過一些手段可以提高MoS2在HER過程中的催化性能:Wu等[13]通過球磨法合成了一種新的MoS2納米結構,經高溫處理后在電流密度4.56 mA·cm-2時過電位可達150 mV,Tafel斜率可達68 mV·dec-1,證明可以通過提高比表面積獲得更多的活性位點從而提高其催化活性;Li等[14]通過DFT理論計算表明MoS2在其惰性表面上的硫空位是新的活性位點,通過硫缺陷可以使其具有更高的HER催化活性;而Hai等[15]通過往2H構型MoS2中摻雜Co元素并形成晶體缺陷,使其惰性表面HER催化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以上方法本質上都是通過增加MoS2活性位點的數目和改變MoS2的電子結構從而改善MoS2的HER催化活性。而摻雜作為一種最普遍的使用方法,對提高MoS2的HER催化活性具有研究和指導性意義。因此,我們選用過渡金屬Cu摻雜2H構型MoS2制備Cu/MoS2復合材料,以提高其催化活性。
MoS2可分為1T、2H、3R三種晶體構型。結合圖1可知,在單層結構下,1T構型為八面體配位,而2H構型和3R構型為三棱柱配位。但是,2H構型和3R構型中同一個Mo原子連接6個S原子,S原子組成的三角形上下互為鏡像,這有別于1T構型。而多層MoS2是由八面體或三棱柱配位單層所組成,每一層都可以具有這2種狀態中的任意一種。最常見的2H構型MoS2有著類似卻又不同于石墨烯的二維層狀結構,其單層MoS2是一種獨特的三明治夾層結構,即S—Mo—S,層內原子之間通過共價鍵/離子鍵[16?17]連接;而多層MoS2的層與層之間通過微弱的范德華作用力連接,層間距約為0.65 nm[18]。范德華作用力的影響會造成層與層之間的堆積,從而進一步限制MoS2在HER中的電子遷移過程[19]。

圖1 MoS2不同晶體構型的金屬配位方式、俯視視角和堆垛排序圖Fig.1 Metal coordination,top view and stacking sequence diagrams of different crystal types of MoS2
傳統MoS2制備方法主要可分為物理法和化學法,其中化學法中最常見的主要是水熱法[20]、氣相沉積法[21]、電化學沉積法[22]等。水熱法的優勢在于其操縱手段的可控性強,獲得的產物更接近于理想特性,比如結晶度高、雜質少,但對反應所用的高壓反應釜要求過高;而氣相沉積法所合成的產物質量高、尺寸大,但其工藝流程比較復雜;電化學法是利用含硫源和鉬源的電解質溶液中的離子發生氧化還原反應,將目標產物沉積到電極上的一種方法。該法工藝流程簡便且可控性強,可以使用不同的電沉積手段(如恒電流、恒電位等)并改變不同的參數(時間、溫度等)從而得到不同形貌的產物。我們使用熔鹽電解法來制備2H型MoS2,并在此基礎上摻雜過渡金屬Cu以改善MoS2的HER催化活性。
1 實驗部分
主要試劑LiCl、KCl、Na2MoO4、KSCN、CuCl2等均為分析純,購自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玻碳電極直徑為5 mm,鉬絲直徑為1 mm,純度99.99%。
1.1 Cu/MoS2的制備
首先使用電子分析天平(CPA225D,北京賽多利斯儀器系統有限公司)分別稱取LiCl(42.0 g)、KCl(51.3 g)、KSCN(6.0 g)、Na2MoO4(4.0 g)、CuCl2(1.5 g),混合均勻后放入坩堝中,將坩堝置于真空干燥箱(573 K,6 h)中烘干,之后將坩堝放入馬弗爐中加熱至1 073 K使其熔化。以鉬絲為陰極,玻碳電極為陽極,電解2 h后得到黑色沉淀物。之后將黑色沉淀物洗滌、抽濾、干燥,得到最終產物Cu/MoS2。在低溫(550℃)、低電流(0.5 A)電解下制備的材料命名為Cu/MoS2?nanoflowers,在高溫(750 ℃)、高電流(2.0 A)電解下制備的材料下命名為Cu/MoS2?nanosheets。
1.2 表征與測試
分別稱取上述樣品0.1 g、蒸餾水5 mL、無水乙醇5 mL、質量濃度5% Nafion溶液0.32 mL混合放入離心管中并將其在超聲清洗機里放置1 h使其均勻分散開,然后將混合溶液均勻滴在面積為1 cm2的碳布上并烘干(電熱鼓風干燥箱,WGL?65B,天津市泰斯特儀器有限公司)。之后在三電極工作體系下(直流電源EPS?1530MD,深圳市兆信電子儀器設備有限公司;電化學工作站Interface 5000E,廣州市剛瑞普凡科學儀器有限公司),以Ag/AgCl為參比電極,玻碳電極為對電極,夾雜在鈦框里的碳布為工作電極,電解質為1 mol·L-1的KOH溶液。使用X射線衍射(XRD,Bruker D8?A25,德國Bruker公司進行物相分析,Cu靶Kα輻射,波長0.154 06 nm,管電壓40 kV,管電流40 mA,掃描范圍0°~140°);使用掃描電子顯微鏡(SEM,Nova Nano 450,荷蘭有限公司,工作電壓15 kV)和能量色散X射線光譜儀(EDS)觀察樣品微觀形貌和微觀化學結構;使用X射線光電子能譜(XPS,Axis Nova,英國自雷尼紹公司)分析元素成分和價態;使用高分辨率透射電子顯微鏡(HRTEM,LS?780,北京賽多利科學儀器有限公司)和電子選區衍射(SAED)分析微觀晶體結構。通過線性掃描伏安法(LSV)測量HER過電勢范圍,之后通過LSV曲線得出Tafel曲線;使用循環伏安法(CV)通過改變掃速測得雙電層電容(Cdl)大小;通過加速耐久性實驗(ADT)和計時電位分析(CP)法來測試電化學耐久性能;通過交流阻抗法測量特定電勢下的電化學阻抗。
2 結果與討論
2.1 XRD分析
Cu/MoS2?nanoflowers 和 Cu/MoS2?nanosheets 的XRD圖如圖2所示。由圖2可知,在14.378°、29.026°、32.676°、33.508°、44.151°、58.334°、60.144°處均出現衍射峰,對應于六方晶系MoS2(PDF No.37?1492)的(002)、(004)、(100)、(101)、(006)、(110)、(008)晶面,可以證明摻雜后MoS2的晶型未改變;二者的衍射峰強度不同且(002)晶面峰強均較高,說明其暴露出更多的邊緣結構。Cu/MoS2?nanosheets明顯在43.297°、50.433°、74.130°處出現了新的衍射峰(藍色菱形處),分別與 Cu(PDF No.04?0836)的(111)、(200)、(220)晶面相對應,說明Cu成功摻雜進MoS2中。

圖2 Cu/MoS2?nanoflowers和Cu/MoS2?nanosheets的XRD圖Fig.2 XRD patterns of Cu/MoS2?nanoflowers and Cu/MoS2?nanosheets
2.2 SEM?EDS分析
Cu/MoS2?nanoflowers 和 Cu/MoS2?nanosheets 的SEM和EDS分析如圖3所示。由圖3a可知,納米花狀樣品的微觀形貌表明其層與層之間的堆垛現象較為密集,平均直徑約1 μm且有明顯的花瓣狀結構;而由圖3c可知,納米片狀樣品平均直徑約為2 μm且有明顯的片狀結構。對比可知,納米片狀和納米花狀樣品都是由小且薄的納米片組成,而前者相較于后者尺寸更大、更厚一些;兩者的微觀形貌都較為良好。而由EDS分析可知,樣品中含有S、Cu、Mo三種元素,其中Cu的質量分數分別為1.519%和0.598%,證明Cu已摻雜成功,與XRD結果相符。

圖3 (a)Cu/MoS2?nanoflowers和(b)Cu/MoS2?nanosheets的SEM圖及EDS譜圖Fig.3 SEM images and EDS spectra of(a)Cu/MoS2?nanoflowers and(b)Cu/MoS2?nanosheets
2.3 HRTEM與SAED分析
Cu/MoS2?nanoflowers和 Cu/MoS2?nanosheets的HRTEM和SAED分析如圖4所示。通過標定可知Cu/MoS2?nanoflowers的晶格間距為0.273和0.268 nm(圖 4a、4d),分別對應 MoS2的(100)和(101)晶面。而Cu/MoS2?nanosheets的晶格間距為0.274和0.228 nm(圖 4d、4f),分別對應 MoS2的(100)和(103)晶面。經傅里葉變換(FT)處理后(圖 4b、4e)可以看到 Cu/MoS2?nanoflowers和Cu/MoS2?nanosheets具有2種類型不同且規則的網格狀條紋排布,同時在Cu/MoS2?nanosheets的部分地方清晰地觀察到了晶格缺陷(圖4e中圓圈)。而晶格缺陷可以提高樣品的電催化活性,這正是Cu摻雜所致。除此之外二者都沒有明顯地出現大面積的納米簇現象,說明晶型都較好。而圖4c、4f表明二者的SAED圖均為衍射斑點和衍射環共存,由此可以判斷二者均為多晶,圖中3個衍射環分別對應六方晶系MoS2的(100)、(102)、(106)晶面。

圖4 Cu/MoS2?nanoflowers的HRTEM圖、FFT變換圖和SAED圖;Cu/MoS2?nanosheets的(d)HRTEM圖、(e)FFT圖和(f)SAED圖Fig.4 (a)HRTEM image,(b)FFT image and(c)SAED pattern of Cu/MoS2?nanoflowers;(d)HRTEM image,(e)FFT image and(f)SAED pattern of Cu/MoS2?nanosheets
2.4 XPS分析
Cu/MoS2?nanoflowers和 Cu/MoS2?nanosheets的XPS分析如圖5所示。圖5a為使用外來污染碳C1s作為基準峰進行荷電校正的XPS全譜圖,該圖表明2種材料都含有Cu、Mo、S元素且Mo3d特征峰最為強烈,這進一步說明Cu元素摻雜成功。圖5b為Mo3d的XPS譜圖,二者在結合能229.9和233.2 eV處的2個特征峰分別對應Mo4+的Mo3d5/2和Mo3d3/2氧化態。然而,Mo3d中不僅出現了S2s的特征峰,還在236 eV附近檢測到了較弱的特征峰,對應于Mo6+氧化態。Mo6+特征峰的出現可能是由于在合成樣品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少量的MoO3。在摻雜Cu后 Cu/MoS2?nanosheets的 Mo6+含量也隨之增加,而且結合能向高場方向偏移,這說明摻雜的Cu與2種材料之間發生了電子轉移過程。由圖5c可知,S2p中結合能162.8和164.1 eV處分別對應S2-中的2p3/2和2p1/2軌道能級,表明其主要氧化態是S2-。Cu2p譜圖中結合能933.3和953.1 eV處分別對應Cu+的2p3/2和2p1/2軌道能級,證明其是以Cu2S的形式存在,而且無伴峰存在(圖 5d)。

圖5 Cu/MoS2?nanoflowers和Cu/MoS2?nanosheets的(a)XPS全譜圖、(b)Mo3d、(c)S2p和(d)Cu2p XPS譜圖Fig.5 (a)Survey,(b)Mo3d,(c)S2p,and(d)Cu2p XPS spectra of Cu/MoS2nanoflowers and Cu/MoS2nanosheets
2.5 電催化析氫性能
Cu/MoS2?nanoflowers和 Cu/MoS2?nanosheets的析氫性能分析如圖6所示。圖6a為相應的LSV曲線,由圖可知,當對應電流密度為10 mA·cm-2時,二者的過電位分別為259.6和199.6 mV。圖6b表明Cu/MoS2?nanoflowers的Tafel斜率為 62 mV·dec-1,而Cu/MoS2?nanosheets的 Tafel斜率僅為 59 mV·dec-1。以上結果說明Cu/MoS2?nanosheets的電催化性能最佳。同時根據在堿性條件下的HER機理可以推斷出二者的催化機理為Volmer?Heyrovsky機理,而Heyrovsky步為基元反應的決速步。而對比圖6c和7a可以發現,經過1 000圈循環之后,Cu/MoS2?nanoflowers和Cu/MoS2?nanosheets在電流密度為10 mA·cm-2時對應過電位分別為239.6和214.5 mV,相較于初始LSV曲線的過電位而言,變化不大,穩定性較好。圖7b和7c說明了二者在不同掃速下通過的非法拉第電流不同。掃速越大,通過電極的非法拉第電流越大,曲線圖更接近矩形,表現出Cdl的行為。由圖 8a可以看出,Cu/MoS2?nanoflowers的Cdl=15.6 mF·cm-2,而 Cu/MoS2?nanosheets的Cdl=26.1 mF·cm-2。以上結果證明 Cu/MoS2?nanosheets相較于Cu/MoS2?nanoflowers表現出更大的有效電化學活性表面積,暗示其存在更多的催化活性位點,電催化性能也更優異。圖8b為樣品的Nyquist圖及等效電路圖,其中包括歐姆阻抗(Rs)、電荷傳遞阻抗(Rct)和Cdl。Cu/MoS2?nanosheets擁有較小的Rct(12.4 Ω),這意味著納米片狀樣品中電子可以更容易、更快地參與電荷轉移過程,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證明摻雜Cu可以促進電子轉移動力學過程,這可能是因為Cu/MoS2?nanosheets獨特的晶體結構導致電子可以更好地與基底面接觸。圖8c為二者的ADT和CP圖,可用于評估其耐久性和穩定性。分別在-20和-100 mA·cm-2恒定電流密度下每10 h進行一次穩定性測試,電位范圍為0~-0.6 V,循環1 000圈。由圖可知,在經歷長時間的催化過程后2種材料仍能保持較好的催化活性。

圖6 Cu/MoS2?nanoflowers和Cu/MoS2?nanosheets的(a)LSV曲線和(b)Tafel斜率;(c)Cu/MoS2?nanoflowers的初始和1 000圈循環后的LSV曲線Fig.6 (a)LSV curves and(b)Tafel slopes of Cu/MoS2?nanoflowers and Cu/MoS2?nanosheets;(c)LSV curves of Cu/MoS2?nanoflowers for the initial and 1 000th cycles

圖7 (a)Cu/MoS2?nanosheets初始和1 000圈循環后的LSV曲線;(b)Cu/MoS2?nanoflowers和(c)Cu/MoS2?nanosheets的非法拉第電容曲線Fig.7 (a)LSV curves of Cu/MoS2nanosheets for the initial and 1 000th cycles;Non?Faraday capacitor curves of(b)Cu/MoS2?nanoflowers and(c)Cu/MoS2?nanoflowers

圖8 Cu/MoS2?nanosheets和Cu/MoS2?nanoflowers(a)在不同電流密度與掃描速率下的雙電層電容、(b)交流阻抗圖和(c)在-20和-100 mA·cm-2下每10 h對應的恒電位曲線Fig.8 (a)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curves,(b)double?layer capacitance at different current densities and scan rates,and(c)chronopotentiostatic curves at-20 and-100 mA·cm-2for every 10 h of Cu/MoS2?nanosheets and Cu/MoS2?nanoflowers
2.6 電化學性能
目前HER催化劑主要的類型可以分為非貴金屬催化劑和以Pt為代表的貴金屬催化劑。考慮到實際運用,有必要將貴金屬催化劑和目前性能比較好的非貴金屬催化劑的電化學性能進行比較,為工業和商業運用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表1列舉了一些催化劑在不同電解質溶液下的電化學性能參數。由表1可知,大部分非貴金屬催化劑仍無法和Pt基催化劑的催化性能相比擬,但其價格低廉等優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表1 部分貴金屬和非貴金屬催化劑的電化學性能參數Table 1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some noble metal and non?noble metal catalysts
3 結論
2H構型MoS2的析氫性能受限于活性位點的數目和導電性能的制約,通過摻雜Cu可以使MoS2晶格結構發生畸變從而影響電子結構特性,減少吸附氫的吉布斯自由能,從而提高HER催化活性;另一方面在堿性條件下,由Volmer?Heyrovsky機理可知中間態吸附產物的產生速率與水解離有關,而水解離又受限于H在金屬表面的吸附能。過渡金屬有著更大的吸附能,因此摻雜Cu可以加快水的解離從而提高催化劑析氫活性。
綜上所述,通過使用熔鹽法制備MoS2并加入CuCl2成功制備出納米花和納米片狀Cu/MoS2樣品,納米片狀Cu/MoS2表現出更優越的電催化析氫性能,為非貴金屬在電催化析氫方面的有關應用提供了參考。
- 無機化學學報的其它文章
- Coexistence of Two Unique Cu(Ⅱ) Ions in Mononuclear Cu(Ⅱ)Complexes with Furanyl Substituted Triaryltriazoles
- Effect of Zn on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Block?Shaped Monoclinic WO3
- Synthesis,Structure,Luminescence,Photocatalytic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a Neodymium Complex Constructed from Biphenyl?3,4′,5?tricarboxylic Acid
- Preparation and Nonlinear 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SiO2@CdTe@Au Composite Nanoparticles
-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on Electronic Structures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g?C3N4Nanoribbons
- 二茂鐵基-雙酮鋅配合物的合成、電化學活性及多光子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