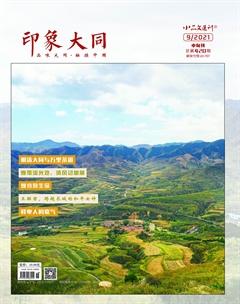鑼鼓的品格
林之說

相較于絲竹管弦,鑼鼓是有些粗鄙的。
他們,跳躍起來最快不過三十二分值,掙了命也只是簡單的“咚咚鏘”。鑼鼓最容易喚醒聽覺,也最可能制造煩躁,初聞人們心旌蕩漾,用不了三五分鐘,興致就減弱一半,繼而心煩意亂、塞耳避之。所以,就有了“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所以,大多時候鑼鼓只在幕后充當配角。即使是在打擊樂音樂會上,大多也會拉些管弦充內涵、壯聲勢。因其鏗鏘之勢而青睞者眾,但真正抵達內心深處的寥寥無幾。
鑼鼓之深奧,戲曲體現最為深刻。揚鞭躍馬、刀兵相接、攻城水斗、大鬧天宮,有幾番變樣就有幾番熱鬧,鑼鼓之酣暢貫通演員和觀眾,描摹出劇場沸騰的聲響。
鬧是鑼鼓的本性。但,鬧中取靜也妙趣橫生。
有一次,在省京劇院看《奇冤報》,演員在后臺一聲叫板,板鼓“噠、噠、噠”聲漸密,演員上場門亮相。
當時,我有一種特別強烈的反應:如果演員再矜持一點,晚一點、慢一些露面,“噠噠”聲再拉長一點,效果會是怎樣?人們會猜:“這是誰要上場了?”“怎么還不出來?”,等等。適度的緩沖,會給人物增加神秘感,讓情節轉換更為從容鎮定。
戲曲中,司鼓是一家之主,其指揮功能大于伴奏。大多數人很容易把“賣力”“手快”評價為優秀。其實,真正的高手,不在手下、而在心中,“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隨時做著繁與簡、緊與慢、長與短、輕與重的組合和取舍,特別是根據劇情需要,將音樂感情化、人物化。曾經,一個老師講:“司鼓最難的地方,不在唱腔,而是迎來送往,特別是對一個眼神、一個情緒的拿捏。”隨著閱歷增多,我才漸悟其神。鼓師與鼓師的差距在哪兒?最明顯的是手巧,但根本還是心靈,是駕馭、調節和服務。
藝術是要追求品質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好的演員,唱念做舞一招一式都收放自如,從容瀟灑,大氣穩重。唱得抑揚頓挫,詞合卯、字達意,眉宇配合展露形色;做的時候,一抬腿、一甩袖起勢明顯,落子無悔,瀟灑飄逸;打的時候,閃轉騰挪,張弛有度……
鑼鼓同樣,在演員需要的時候賦予適當的力道,隨著動作的幅度和感情的波動而迅即反饋、動靜開合。簡單中蘊藏豐富,運用中千變萬化。
經典經得起反復咀嚼。大多數傳統劇目故事情節都不復雜,甚至個別在邏輯上還不算嚴謹。但是,完全不影響觀眾欣賞的熱情。對于傳統劇目,人們關注的是韻味,流連百轉千回中的千錘百煉。電影、電視劇賣的是新,一經劇透就價值大損;戲曲貴在陳,并非一味“陳詞濫調”,而是不同流派、不同團隊對同一個作品的理解和演繹,這種觀感更注重細節,精細到顧盼生輝,更在意推陳出新,精致到唇齒之形。有時,一些評論總是盯住故事“隔靴搔癢”,其原因或是壓根就是《故事會》讀者,或是音樂已經面目全非,根本沒有討論價值。在講故事方面,戲曲使盡渾身解數,也趕不上電影、電視劇,因為原本就不是寫實的。用寫實的眼光去審視和批駁,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苛求。而鑼鼓是服務寫意的,寫實多了,鑼鼓也就沒有了市場,也就只好“弦歌滾滾、鑼鼓偃息”了。
不同劇種弦樂天壤差別,鑼鼓卻是相通的。戲曲鑼鼓依附于唱腔音樂,緊跟演員行止,其表現力就在于和舞臺的結合度。所以,打擊樂樂手最應該讀懂人物身份,最應該掌握劇情發展,這樣才能啟發操作靈感,形成獨特演奏技法。有幾次,在劇場看演出,鑼鼓似乎完全不顧劇情,賣命地刷存在感,幾個樂手“鐵匠”似的嗨到極點,我把座位從一樓前排挪到后排,不得已又爬至二層,都難以避其轟炸,鬧心到極點,當時對打擊樂恨得牙根疼。而,好的樂隊若明若暗、拿捏得當,似乎感覺不到打擊樂的存在,但某時某刻又助力變檔,環環相扣,步步為營,給演員的唱腔和表演打通經脈,將整個演出粘連得嚴絲合縫,令觀眾潤耳、養眼、寬心,演出結束都意猶未盡。
鑼鼓是戲曲的一道警戒線,演員懂得駕馭才能不慌不亂、不怒自威,觀眾識一點才不會被浮華的說辭迷眼,在樸素的精華和絢麗的糟粕中保持一份定力。
入耳聲聲,音噪而心平。每一下敲擊,都代表不同的心跳,隨性卻不隨意。
鑼鼓的品格,大概盡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