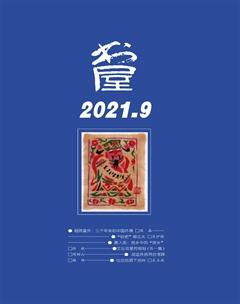魯迅與徐渭
那秋生
一
青藤書屋坐落在紹興市西區,如今是明代奇才徐渭的紀念館。書屋里有一副十分顯眼的對聯曰:“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這不由使人聯想到魯迅先生,他的一本雜文集題目就叫《南腔北調集》。正是:穿越三百年的歷史風云,魯迅與這位同鄉的先賢有了神遇。
徐渭以“南腔北調”自稱,便體現了他的叛逆個性,證明著這是一個不倫不類的人。就說其字號罷,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漁隱、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鷴山人、鵝鼻山農等,可謂五花八門。
其實,“南腔北調”是有來歷的,同戲曲相關。徐渭是個“大雜家”,詩、書、文、畫乃至戲曲都出人頭地。比如他的《四聲猿》,被人稱為“明曲第一”,其中的《雌木蘭》之北與《女狀元》之南,更是戲曲中的“奇中之奇”。當然不僅如此,徐渭的自稱還有著更深的意味,同他的豐富而坎坷的經歷是相應的。徐渭四歲識字,六歲誦讀唐詩,八歲學作時文,十二歲學琴曲,十六歲學劍術,二十歲成為秀才,可見他從小就不愿專在一門,而是博學廣識,任性有為。不幸的是,性格決定了命運。科舉試場的八股文讓他的恣肆才情無法施展,因為他寫的文章“不入調,不入流”,所以屢試不第,終于斷了功名之念。徐渭是一個既有深厚傳統文化素養,又具強烈叛逆思想個性的奇人。
魯迅何嘗不是如此?他在《南腔北調集·題記》中寫道:“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為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后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瞧吧,這就是一個獨具個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南腔北調”成為“離經叛道”的代名詞了。
二
袁宏道對徐渭最為賞識:“宏于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梅國楨稱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文,文奇于畫”。魯迅心目中的徐渭不僅僅是才氣而已,更在于他的傲骨。那些在民間流傳的《徐文長故事》,把他說成是一個插科打諢式的滑稽人物,掩蓋了其悲劇性的性格本色,魯迅是很不以為然的。
魯迅與林語堂發生過關于小品文的爭論,兩次提到已經被弄得面目全非的“徐文長”:“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圣嘆,‘殺頭,至痛也,而圣嘆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圣嘆并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并無什么瓜葛的。”“‘幽默一傾于諷刺,失了它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于‘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為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于國貨,終將成為洋式徐文長。當提倡國貨聲中,廣告上已有中國的‘自造舶來品,便是一個證據。”
魯迅的胞弟周作人似乎別有一種知音,他將自己的書房命名“苦雨齋”,就是從徐渭那里來的:“會稽滄海國,苦雨快茲晴。”這一個“苦”字,不正是徐渭一生心境的真實概括嗎,他如何能“幽默”得自樂呢?
敢于叛逆的徐渭把自己比作“梟獍”,他的《曹娥祠》詩曰:“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鱉浮尸出,八尺龜螭臥絹黃。總為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繞爺娘。”徐渭是在同“孝女”曹娥做著反比,說自己是“梟”(即不祥之意的貓頭鷹)與“獍”(一種會吃掉生母的不孝之獸),表示他與傳統現實是格格不入的。無獨有偶,魯迅的外號就是“貓頭鷹”,他把自己的言論稱為“梟聲”,致力于反傳統的革命宣傳。瞿秋白曾經熱情贊揚魯迅“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
徐渭是一個典型的紹興人,魯迅在《女吊》一文里寫道:“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這對于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魯迅稱此為“越中遺風”,它深遠地影響著徐渭以及后人的文風。俗曰:“沃土之民謔,瘠土之民忍。”紹興的民風鄉情孕育與陶冶了文人的風流倜儻,如陸游、徐渭、張岱、王思任、李慈銘、魯迅等,“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他們之獨特,在于其硬氣與謔性的完美融合。
三
戲劇與人生,在文人來說是一回事。徐渭善于寫戲,魯迅對戲也很熟悉。我們再來說說徐渭的《四聲猿》,這是明代雜劇中最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經過考證,徐渭認為“南曲”是“北曲”的正聲,可以融為一體。他在《南詞敘錄》中說:“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發灑淅,足以激人勇往之志……南曲則紆徐綿眇,流麗婉轉,使人飄飄然喪其所守而不自覺。”于是,他著意創作了一組不倫不類的“南腔北調”之戲。《四聲猿》之名取自《水經注》,“猿鳴三聲淚沾裳”,猿鳴四聲則更為斷腸了,這四出戲都是具有悲劇性的故事,徐渭的意圖是借古諷今。而魯迅的《故事新編》也有此意,其小說的結構可以視為戲劇的原型,如《藥》的結構就像是標準的四幕劇。
《狂鼓史》表現了禰衡在陰間擊鼓大罵曹操的情景。徐渭曾以禰衡自比,代表了那些敢于參劾嚴嵩的文士,并且借用他們陰間的“鬼話”,來說出自己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野心與狂氣,真是淋漓痛快至極。魯迅非常熟悉歷史,他說:“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后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他對文人論政和曹操功績都是肯定的。
《雌木蘭》和《女狀元》塑造了一武一文的兩位巾幗英雄,而且都是女扮男裝的曲折經歷,這是徐渭對于女性的贊歌。但其中也能看出他對于人才容易遭埋沒的惋惜和嘆息,一個是“苦戰”,一個是“苦熬”,故能心心相印。魯迅自然看得分明,他知道在封建的男權社會里,女子縱有才華也不能成大事,因此他的小說著重刻畫了一些女主人公的悲慘命運,如《明天》里的單四嫂子和《祝福》里的祥林嫂等。給木蘭冠以“花”姓也是徐渭的創作。
《玉禪師》取材于佛教中的輪回傳說,寫了玉通和尚與妓女紅蓮的私通,以及償還“紅蓮債”的故事,這真是驚世駭俗的奇聞。這使人聯想到了魯迅那篇趣文《我的第一個師父》,他在幼時“父親怕有出息,因此長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里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這個龍師父,其實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發的俗人”,他還有老婆——“一個年輕的寡婦”呢。顯然,魯迅的幽默敘述中含有反抗傳統世俗的意味,這同徐渭戲的主題不謀而合。一切皆如徐渭的戲臺聯所曰:“隨緣設法,自有大地眾生;作戲逢場,原屬人生本色。”
四
文人的靈犀可以穿越時空,尋求歷史的回響。魯迅自嘲:“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這也許是受到徐渭的影響,其詩《恭謁孝陵》曰:“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孝陵。”魯迅喜愛梅花,以為“只有梅花是知己”。這也是有文人遺傳的,徐渭最喜歡畫梅花,他的《畫梅》詩曰:“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著便成春。”魯迅的舊體詩中有不少思鄉之句,如:“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明眸越女罷晨裝,荇水荷風是舊鄉”。徐渭的鄉情盡在《鏡湖竹枝詞》中,如:“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十里荷花迷水鏡,一行游女惜顏酡。”他還有一副著名的對聯:“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煙火盡歸此處樓臺。”
徐渭是文學奇才,非一般人所能比。他的人生遭際更奇,也非一般人所能遇。他身懷奇才而遭逢不幸,坎坷一生,布衣終身,他的奇特身世、奇異性格在中國文學史上罕有其匹。清人的評說是:“文長之為文長者,乃其無所借傍,一任其天性之自由亢起、自由創制,加之其秉性卓邁,故所涉無不發揮至其天性之極也。”這樣的“天性”,唯“奇才”是有。魯迅也是“懷才”的,其詩曰:“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任何一個具有良知的文人,都知道手中這支筆的分量,更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
徐渭的藝術主張是“順情從心”,他是以情為本色寫雜劇,并在《選古今南北劇序》中如此宣稱:“人生墮地,便為情使。聚沙作戲,拈葉止啼,情昉此已。迨終身涉境觸事,夷拂悲愉,發為詩文騷賦,璀璨偉麗,令人讀之喜而頤解,憤而眥裂,哀而鼻酸,恍若與其人即席揮麈,嬉笑悼唁于數千百載之上者,無他,摹情彌真則動人彌易,傳世亦彌遠。”魯迅也一樣是“有情”的,其《答客誚》詩曰:“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他以情為本色寫文章,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五
徐渭把王陽明的“心學”稱之為“圣學”,并且把王陽明和孔子、周公相提并論。徐渭《水簾洞》詩:“石室陰陰洞壑虛,高崖夾路轉縈紆。紫芝何處懷仙術,白日真宜著道書。數尺寒潭孤鏡曉,半天花雨一簾疏。投荒猶自聞先哲,避跡來從此地居。”該詩注云:“陽明先生赴謫時投寓所也”,表達了對這位先哲的崇敬之情。徐渭在《畸譜》中回憶說:“及新建伯陽明先生以太樸卿守制還越,先生造門師事之,獲聞致良知之說。”“發明新建旨,提關啟鑰,中人心髓,而言論氣象,精深擺脫,士翕然宗之。”
王陽明主張“心即理”,告訴人們要相信自己,傾聽內心,樹立起強大的主體意識。他強調要內圣外王,將心性之學轉化為卓越的事功,最終達到“此心不動,隨機而動”的心理境界。魯迅契應“心學”的啟蒙,積極主張“內曜者,破黯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這個“內曜”與“心聲”是合為一體的,即心靈啟蒙與良知發現,這正是魯迅的人格理想。然而,要啟蒙,就必須批判,思想的自由是需要以掙脫鎖鏈為前提的。
徐渭受到中晚明激進王陽明心學的影響,他批判地繼承和發揚了王陽明心學中對于個性張揚的肯定,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新型狂狷人格。這就反映在他的書法繪畫中,表現為對傳統規范的突破和富于個性的新奇創造。盡管其中年始學畫,既無師承,又窮困潦倒,但心學所提供的顛覆勇氣和道德正當性,讓他相當自信地進入書畫,并創造新的繪畫樣式。
魯迅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通過改造人的思想即“人心”來實現社會的變革和歷史的進步,并且堅信人心是可以改變的。這一思想特征顯然與儒家心學思想在本質意義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此可見,魯迅同王陽明的思想十分契合。魯迅的“立人”之說,是“反求諸身”的生命探索,“唯此自性,即造物主”;“唯有自我,本屬自由”。
徐渭當過“紹興師爺”,他的才情是獨具一格的。在魯迅的身上,也有“紹興師爺”那種冷峻、精密、尖刻的風氣。我們似乎看見徐渭的影子,一一閃現在魯迅的小說中:徐渭的科舉失落、窮困潦倒,猶如“孔乙己”;徐渭的精神分裂、癲狂反常,恰似“狂人”……魯迅的書房里掛著一副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徐渭肯定是魯迅的“知己”和“同懷”,魯迅這樣聲稱:“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這也許就是魯迅說給徐渭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