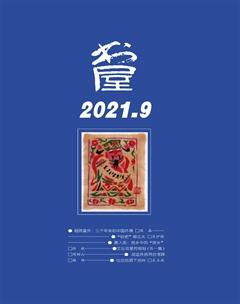日本的“盛世”與“窮民”
朱奇瑩
《飽食窮民》是日本著名的新聞記者齋藤茂男(1928—1999)寫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間的紀實文學作品。作品分為三章,所記內容的時間跨度將近五年半,當時面市是以通過作者供職的日本共同通訊社發送至各個加盟報紙進行連載的形式刊登出來的。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些文字是他當時企圖通過探索人們的內心世界,來描繪日本二十世紀末的社會圖景的一種嘗試。當然,這份嘗試并不僅止于《飽食窮民》,或者說,《飽食窮民》只是其記錄的一個側面和角度。實際上,齋藤茂男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直以普通人為采訪對象,通過報刊連載的方式記錄日本泡沫經濟時代下無數的“世相”點滴。這些不同題材的作品,于1993年至1994年由巖波書店正式出版為十二本紀實文學作品集“日本世相”系列,可謂齋藤茂男記者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同時也成為一幅生動印刻著日本社會從經濟高速增長走向泡沫破滅的多面向的時代畫卷。此次于2020年1月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僅是該系列中的頭兩冊作品——《飽食窮民》和《妻子們的思秋期》。雖說譯本距原作在日本出版有近二十五年的時間差,書中所述的不少事情已經過去三四十年甚至更久,但作品在中國仍引起了熱銷及熱議。
一、新窮人
《飽食窮民》一共收錄了三篇紀實文學。第一章的“飽食窮民”寫于1984年,主要聚焦的是日本社會當時的貸款和債務問題,記錄在經濟發展時代下特有的“繁榮中的貧困”。齋藤的采訪對象均是任職于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企業的人士,文字背后呈現出的是其被銷售指標和業績窮追不舍的生活狀態。齋藤認為,泡沫經濟時期,隨著日本微電子革命走向成熟,無論企業內部還是企業之間,均構建起了龐大的機械化、自動化、無人化網絡,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統無孔不入地覆蓋至每個角落。在如此不日不夜的工作競爭狀態下,企業活動轉向二十四小時制,該時期日本人工作的瘋狂程度也達到頂峰,甚至遠超因瘋狂工作而出名的戰后經濟高速增長期。當加班變成日常,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便所剩無幾,尤其對于一些男性職員來說,“家對于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吃‘洗‘睡的地方”,盡管“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都打出‘男女平等、共建社會的口號,但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下,男性幾乎沒有條件平等分擔日常收拾、育兒、照顧老人等家務勞動”。這樣一來,家庭內部也無法構成相互支撐的親密關系,而允諾預支消費、分期消費購物的信貸系統和如洪水般涌來的高標而精致的消費欲望生產,恰恰可以為所有上班族和他們的家人提供想象中虛假的繁榮,讓其依靠物質來填補心中的空虛,爭先恐后地預支未來的幸福,而不惜被卷入借錢消費的黑洞之中。
夜以繼日的工作方式和停不下來的買買買創造了日本石油危機之后低增長時代的夢幻奇跡。然而光鮮背后,是人類健康亮起的紅燈和思考能力的逐漸喪失,乃至職場的業績神話敗露,曾經的“精英”輕易地掉進債務的陷阱。當這些潮流追夢人的金色夢想化作沉重的債務和信用卡的殘骸,最終淹沒在東京林立的高樓之間時,齋藤認為這份幻化的悲哀其實是現代商務人士心底所流淌的共通感情。所以,他認真地尋訪信貸問題發生的時代背景,把每一個信貸問題勾連在眼下物質與欲望生產均極度泛濫的社會背景中去看待。在他看來,這么多人之所以不顧自己的償還能力也要從信貸公司借貸,或是用信用卡購物,“這絕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虛榮心在作怪,而是出于一種人們在苦悶中試圖證明自己的心理:證明自己能夠融入這個社會,沒有落后,不低人一等”。而“刺激企業追求利益的沖動、經濟的沖動”仍舊“不停地侵蝕著人們的生活,壓垮、吞噬并統治生活本身。”面對這樣的現實,齋藤在反思中發出善意的預警,“雖然經濟是支撐人們生活的重要基礎,但其本身不是我們活著的目的”,如果本末倒置,只能看到眼前的利害得失,那么經濟原理將徹底占領我們的生活,人很容易淪為欲望的奴隸,面臨“人性喪失”的危險。
二、“技術應激”之人
第二章命名為“快節奏的城市”,主要內容來自于作者1988年對計算機企業一線的軟件技術人員展開的采訪,主題在于揭示飛速發展的計算機化潮流給人們帶來的變化。作者在記錄當時的工程師和程序員們高強度、長時間、高密度的工作狀態的過程中,揭示出計算機領域的工作一方面富于創造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卻存在體力嚴重透支的危機和精神上無時無刻不需要面對被時代追趕的壓力,還有在人機過度親密之后產生的技術應激現象,即人容易走向自閉化、思考邏輯二元對立化乃至人際絕緣化的種種特征。例如,文中提到,計算機領域的技術革新已遠非用“日新月異”能夠形容,已經到了“分秒必爭”的地步。每當新型計算機接連登場,更高、更新的軟件技術就必須應運而出,所以每個工程師都要面對自身技術落后于時代的不安。以前積累下來的經驗很快就會被淘汰,甚至有人說工程師三十五歲就得退休。
那么,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計算機本身嗎?事實上,在對比軟件技術人員和普通辦公室職員的狀態后,作者發現,這種高壓自閉的勞動狀態和緊張僵化的生活面容其實并不限于計算機領域的工作人員,其他的職業與工種也同樣面臨被步步緊逼的逼仄境況,乃至一般的普通職員也時常會在精神方面出現技術應激行為,日常備受身心嚴重疲勞的煎熬,亦無法處理人際關系的緊張。因此,與其說人們遭到了魔性的計算機的洗腦,不如說是為了躲避現實中的種種焦慮與空洞化的人際關系,而選擇逃進了計算機的世界,寧愿變成“膠囊人類”。齋藤指出,這一診斷結果,是基于日本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即整個商業領域都被籠罩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之下,“每天的銷售目標這種細如漁網的工作量管理、時間管理隨處可見,而用于督促、監視這些管理條目的計算機也在飛速普及”。而且,這種公司化管理模式已經覆蓋至教育、行政等其他領域并成為普遍趨勢,在考察人機關系的時候,如果不對縈繞自身周圍的這種殘酷且反人類的工作環境和制度環境進行反思,不深入思考個人需要在怎樣的現實體驗中才能獲得人生的成長和人格的豐富,那就無法阻止通向自閉化社會的列車一路急行,最終人之為人的身份也會變得可疑。也正因如此,在記敘技術應激現象的過程中,齋藤不斷關注并強調人們在現實日常中體驗真實的喜怒哀樂與人情冷暖的重要性,他認為現實世界中種種感情的真實袒露、碰撞與交流,能使心靈的體驗更加充實,能使精神世界更加豐富,也有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
三、“嘔吐”的“女人”
第三章以“嘔吐的女人”為題,齋藤主要以“拒食”“過食嘔吐”這一女性特有的疾病作為素材切入點,試圖通過女人們的內心世界揭示出日本現代社會背后所隱藏的問題。他看到,“在一個到處充斥著金錢和物質的社會之中,不知是人們被卷入了飽食的漩渦,還是社會對于效率的追求近乎偏執,抑或是對于人情溫暖和愛情的饑渴已經到了讓人近乎窒息的程度,人們迷失在人生的選擇中”。于是,各種挫折、“病態”現象的出現,成為齋藤眼中“為了擺脫生存的不安而發出的求救信號”,因此他將目光對準了在病態時代中煎熬、挫折、掙扎著的年輕女性,關注那些有進食障礙和由此衍生出盜竊、出軌等其他心理疾病的患者群體(患者幾乎全都是女性)。作者在調查中發現,過食嘔吐癥這類疾病的增加和戰后日本的經濟增長曲線幾乎完全重合,疾病最早出現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后飛速增加,特別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患病人數開始幾何級數增長,至采訪時增長速度更是進一步加快。而且,除了數量劇增,該疾病還呈現出很強的特征性:即患者的發病年齡段已迅速擴大,從小學生至中老年均可見患病者,中年患者中很多甚至是所謂的“職場女強人”。
跟隨作者對挫折問題本源的不斷追蹤,既讓人看到從個人層面的愛恨情仇中折射出來的病態社會之縮影,也讓人不得不直面進食異常癥之所以在女性中產生并不斷蔓延的原因。由于生活方式上的迷茫、育兒過程的孤立、性生活中的閉塞、職場或者家庭關系的緊張等等,導致人們需要通過大量進食、嘔吐或者極端拒絕進食的行為來緩解心中不斷加劇的不安。齋藤在反復的調查與尋訪中提示,這些嘔吐行為本身反映的正是現代人心靈的“空虛”,這些空虛與心中缺乏足夠的信任感是造成此類病癥的元兇之一。與此同時,許多潛在的、被社會強迫和控制的傳統價值觀對女性的禁錮,讓她們感到無法正常地、有自尊地、自我肯定地生存下去,這也是造成其發病的一個重要原因。齋藤真誠地體恤這些遭遇困境的女性群體,描述她們“用誠實而又有些過激的方式,在直面心中苦楚的旅途之中顛沛流離”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他將這些“嘔吐的女人”視為“煤礦里的金絲雀”,從她們的內心苦楚與過激的應對方式中,讀懂了她們對缺氧環境做出的敏感反應和本能預警,意識到她們正是通過“疾病”這一脫離社會常軌的行為,揭示了日本現代社會的癥結所在,對這個“健康”的社會進行自己“病態的”反抗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