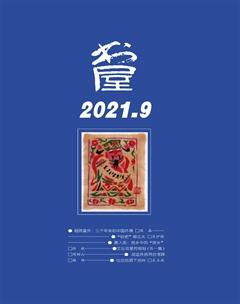沈從文:《一種建設人材》
李牧
1946年6月22日,《一種建設人材》刊登在云南《正義報·新論衡》增刊第八十八期上,署名沈從文。文中,沈從文設想了一個理想的美術館應當具備的“理想的工作人員”,茲略加整理,披露于此:
一種建設人材
一個理想的美術館,它的實現是從長時期準備而產生的。我們得先有幾個工作人員。近乎理想的工作人員,應當是——
他的年齡大約三十歲,曾畢業于國立大學的建筑系或歷史系,平時對于考古學和美術史研究就極有興趣。他還懂一點音樂,一點圖畫,一點民俗學或人類學。他是個美術鑒賞家,尤其是有關于東方的,代表西南地方性、民族性的工藝美術和造型藝術,具有深刻的愛好和高度的鑒別力。他能寫,能畫,縱缺乏特別創造天賦,可是到臨摹藝術品時,卻有本領把握得住對象,做到準確和逼真程度。他也可說是個好事者,對一切古典藝術所表現的華貴莊嚴情操能欣賞,能領會,對另外一種違反傳統藝術所表現的熱忱幻想也能欣賞,能領會。他的愛好有時看來可謂雜而不純,淵博而不精深,然而興趣的濃厚真率卻補足了那個缺點。因為興趣廣,認識多,凡各個民族在同一時代,或同一民族在不同環境下,熱情與巧思共同形成的種種藝術品,他都是一律給予應有的關心。他能于平凡中發現美,發現價值,因此許多歷來被疏忽、被湮抑了的藝術品,由于他的努力,在世界上重新得到應得的重視和注意。
他曾用故宮收藏美術品教育了自己多年,他曾在一個國家博物館服務。他曾參觀過河南、山東兩省博物館的精美收藏,并學習現代處理藝術品的各種方法。
他還抱有一種書呆子的頑固信念,即國家的重造,文化的復興,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復,實有待于各方面的努力。美術可能做的貢獻并不比政治經濟差多少,而且現代唯武力武器的政治觀、市儈主義的經濟觀已使得國家毫無辦法。言重造,人民情緒實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或發潑,或安定,美術可做的事還多。他即由于這種單純的信念,因此不斷地研究,充滿活潑生氣的學習,去發掘收集古代或現代藝術品絲織布匹上的刺繡扣花挑花,陶瓷器的奇異形制和美麗圖案,木石上的浮雕或圓雕,皮革制件的彩畫裝飾,代表種種習慣與愛好、性格鮮明的服裝,代表宗教情感,各不相同的建筑物和紀念物,解釋歷史的標志物和碑碣,代表一民族哀樂有藝術價值的種種象征,他都能用一種極端的謹慎來收集保存,并作精密的分類。
他的好動天性和對于工作的持久狂熱,不僅使他常常向邊遠縣份跑去,還常常向邊遠鄉村以及人煙稀少的某地跑去,凡是充實一個有地方性美術館的內容,而豐饒觀覽者知識情感的藝術品,他總會想方設法弄來集中陳列。
他一面如此勤于工作,一面卻明白清楚,所從事的是一種事業,溝通連接地方過去和將來文化教育的理想事業,不是普通職業。正因為是一種事業,而且工作的創始,談成就五年十年努力也只能做到規模初具,說不上空前絕后。他更應當知道社會習慣,若干人的成見和偏見,不可免要發生工作上的困難。或屬于一地方迷信,或屬于經濟,都妨礙到工作的進行。他終得用各種努力來克服這些困難。還有一種最大的障礙,即工作所需的經費。這工作雖并不比工業建設費錢,可是所費的錢卻不能如商業投資,到時本利收回。從經濟觀點言來,這簡直是一種本利兩忘的投資,花的錢近于古話說的“擲諸虛牝”。公家的金錢和個人精力的堆積,只能成一個堆滿破銅爛鐵、雜貨羅列的美術館,到這一點被出錢方面提出異議時,他還得努力來有所解釋,用口舌奮斗,爭取預算的通過,并擴大其數目。
末了是我們要問,這時節,這個地方,這種理想人材可容易找,容易造就培植?在這個時代中,大部分的青年幻想和熱忱,不傾注于“政治”上,即寄托于“出路”上,這種工作人員向什么地方去找尋,用什么方法來培植?這就有待于這個社會“負責者”或“好事者”對于“文化”二字能否重作解釋而決定了。負責者如果有一點認識,即時代今昔不同。武力能統制人民,并不能教育人民,工業無科學基礎,根本談不上進步,近三十年歷史已足以證明。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凡只知單純武力的,已不能成功。而市儈主義的經濟觀,更不能使人民真正得到什么福利。欲建設一個地方,自然更得從其他多方面著手。提高多數的知識,激發多數對于所寄托的一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才有個真正轉機!
因此讓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即新的領導者應當具有一種對文化對人生的新的見解。用這種新的見解作土壤,方能培養新社會各方面的有用人材,來啟發來領導一群有感情、有信心、活潑健康的人民,走上真正建設的大路!
(沈從文:《一種建設人材》,云南《正義報·新論衡》1946年6月22日增刊第八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