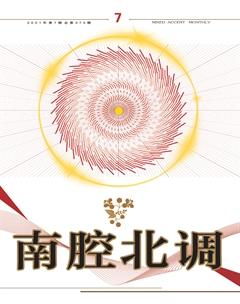《忠實》:重審小說的思想性
劉軍
文學界對小說思想性的重視,貫穿了當代中國文學史的進程,同時,源于具體歷史階段的文學現實與觀念生產的不同,相關思想性的闡述又存在著差異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文學的思想性以及思想標準的直接源頭,可上溯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勃夫、別林斯基這三大批評家創設的文藝觀念體系里,而更早的淵源則是來自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1]曾被恩格斯稱為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他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這一觀點,后來在給拉薩爾的信件中再次強化了這一觀點的普適性,同時也強調了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的統一性問題。那么何謂美學的觀點?即馬克思提及的“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這一命題,至于歷史的觀點,則對應了作品揭示出的客觀真實性、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要求這三個方面。后來,恩格斯又以“三融合說”進一步呈現了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融合的結果,三融合說具體表述為“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以及莎士比亞戲劇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融合”[2]。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在歷史實踐中逐步被轉換為思想性、藝術性這兩大文學批評的準則,俄國的三位批評家完善了思想性、藝術性兩大標準的具體內容,尤其是別林斯基,建樹甚豐,既有概念、命題的清晰闡發,也有優秀批評家的活力生機。
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論成為主導性的文學理論,十七年時期,在特殊國情和特殊文情的歷史條件下,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并重逐漸傾斜化,藝術性標準旁落,而思想性標準凸顯,并逐漸讓渡到政治化標準的確立,且由高度的政治化逼近政治美學化的境地。這一失衡的狀態在新時期開啟后方得以調整,一方面,藝術性標準得以回歸,另一方面,思想性標準被政治標準替代的局面也得到改觀。在回歸常識和回歸文學本位的語境中,文藝批評的思想性標準開花分枝,藝術真實、主體性、性格組合論、典型理論等具備批判性反思的理論命題開始涌現,并一直影響至今。
在新時期文學中,軍旅題材一直作為重要的題材類型與時代同行,軍旅小說與軍事題材電影、電視劇因個別作品的輻射力一度成為社會的聚焦點,20世紀80年代初期李存葆的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以及根據這一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21世紀初期的電影《集結號》(2007年),電視劇《亮劍》(2005),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媒介語境的轉換以及大眾文化的興起,一部小說產生轟動效應的機會已經微乎其微,軍旅小說同樣遭遇困境。以上面所舉的影視作品為例,《集結號》《亮劍》(小說原著分別為楊金遠的《官司》、都梁的《亮劍》)皆改編自小說原著,從結果來看,影視劇可謂風行天下,而小說原著至今依然默默無聞。因此,并不是因為當下的小說作家的專業素養注水或者被稀釋了,根本原因在于文學業已退出了社會大眾的話語場域。如果將新時期以來的四十年劃分為三個時間段,其基本圖式如下:文學的黃金時代——市場經濟興起文學邊緣化——21世紀大眾文化興起。軍旅題材小說也隨之發生轉換,一個總體的趨勢則是,有一個從主題強化到個性化塑造的轉變趨勢。然而,變化中又潛藏著不變的內容,軍旅題材作為特殊的題材領域,無論是在創作環節還是在批評環節,對思想性的重視都是一貫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主義(忠誠、責任、榮譽)與民族精神則是當代中國軍旅文學的靈魂,也是思想性追求的主體內容。對家國情懷的強調,與軍旅文學的意識形態特質及軍旅文學自身的品質密切相關,歷史感和崇高感構成了軍旅創作的“主題先行”的內容。從“十七年”到“新時期”,及至新世紀,無論是對“革命歷史”的史詩式建構,對當代戰爭的反思意味的書寫,還是對和平時期軍營現實問題的深刻剖析,軍旅文學始終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核心部分,建構起了崇高、壯麗的美學風格和張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精神傳統。
21世紀之后,軍旅小說的創作按照朱向前在《當代軍旅文學的精神傳統》一文中的說法進入“雙重回歸”期,即“一是回歸長篇小說敘事性文體本源,開始注重故事性和形式探索;二是回歸文學對象的生命倫理和生活本體,開始關照復雜人性和個人命運,重視日常生活經驗的表達。前者,注重個人化寫作、自由地虛構、強調敘事及敘事主體自身的意義等等,標示著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的敘事觀念覺醒和文體觀念的自覺;后者,開始關注軍人的個人命運和個體經驗,在歷史、戰爭和現實層面探尋更為廣闊的人性空間和精神存在。”[3]不管時代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于軍旅題材小說來說,仍然面臨如何寫軍人、如何寫人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兩個側面之間有矛盾也有統一。這個問題從本質上說,就是如何解決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矛盾問題。屠格涅夫指出:“如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一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4]軍旅小說中的人物很容易抽象化,但成功的軍旅小說中的具體個人無一不是血肉豐滿,而且不僅僅是主人公立體而真實,里面的人物群像皆個性分明。總的來說,作家不能因為題材的特殊性,就消弭掉小說的本體功能,每一種社會身份之下,皆藏匿著深刻的人性,只有以“人物”為中心,才能夠解決特殊性與一般性之間的矛盾。
河南是個農業大省,改革開放之前,對于數量龐大的鄉村青年而言,參軍恐怕是改變人生命運、見識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因此,在當代作家譜系之中,50后、60后這兩代作家群體中,河南籍的軍旅作家為數眾多,且成績斐然。周大新、閻連科、柳建偉、朱秀海等作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忠實》的作者趙俊杰與之相似,作為20世紀60年代生人,在云南邊防戎裝多年,后轉業回地方。軍中經歷,磨礪并塑造了其個人的意志品質,更重要的是在青年階段形成了典型的軍人式的價值觀,重集體、重家國而輕個人。雖然不能以“武死戰、文死諫”加以概括,但那種特別的理想主義自然會浸染入他筆下的文字之中。《忠實》作為他的一部中篇小說集,計收錄三個中篇,三篇作品時間跨度較大。《邊城疑案》以軍營刑事案件為切入點,觸及建國初期云南邊防某地敵我之間的暗戰;《兄弟》的時代背景則進入改革開放前后,主要處理軍營的管理和不同民族戰士之間的磨合問題;《鐘實》則以一位擁有轉業軍人身份的縣紀委書記的視角,道出了他的反貪腐的驚險歷程,這部小說指涉的生活內容,距離當下非常近,甚至可以說就是書寫當下。三篇作品中,最后一個中篇《鐘實》雖然脫離了具體的軍營背景,但因為主人公特殊的意志品質,依然可以將其視作軍旅題材的延伸。
比較而言,三篇作品中,因為前兩篇直接觸及軍營生活,因此,皆有著穩固的主題設定。對于《邊城疑案》而言,則是在白熱化的敵我斗爭中,凸顯我方指揮員的勇氣與謀略,對于讀者而言,牌底是明面化的,大家關注的是斗爭過程中的斗智斗勇,是對抗性力量的起伏沉落。關于《兄弟》這部中篇,其故事情節的最后走向,讀者也有相應的預判,只不過,過程已然由敵我之間的抗衡轉向人民內部的矛盾紛爭。源于沖突性質的不同,這部小說將更多的目光傾注在軍營的日常生活中,而作為加碼的戲劇性要素則是少數民族戰士語言和行動的特異性,作為外溢性力量,他們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軍營的紀律和意志品質上。雖然,上面兩部作品在追求宏大敘事上是一致的,但在大的處理方式上則花開兩枝。《邊城疑案》的基本處理類似諜戰劇本,不僅主題被設定,連人物也是角色化的,包括故事情節的走向,還有故事背景的場景置換,皆有著劇情化的特點。當然,舞臺化有利于改編,但對于小說而言,缺乏必要的張力。《兄弟》則與之不同,人物和故事,有著諸多偶發性的要素,每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皆會涌現一條幽徑,如此,作家的自由度就得以施展,為作品留下意在言外的空間。《鐘實》的主題則與上述兩部作品有所不同,這部作品直擊現實生活,主人公處于漩渦之中,他和各方力量形成博弈、制衡、對抗的多種關系,因此,很難以特定的主題加以預設。就像任長霞犧牲于公安局局長的崗位之上一樣,不是所有的反貪腐和掃黑行動皆必然走向勝利的。作為一部現實題材的中篇小說,這部作品處理的對象不是對立雙方的力量抗衡,而是多種力量在現實場域的博弈。除了主人公之外,這部作品中對縣委書記的刻畫還是很成功的,他的模糊與搖擺,他的堅定與大局觀,對立統一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呈現出作為一個人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汪曾祺先生曾經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家劉慶邦則認為,寫小說就是寫細節。他們的主張各有自己的出發點,但是從一個普遍性的角度出發,寫小說,基礎點位還是寫人物。撇開西方的現代和后現代小說不說,從明清的白話小說發展到今天,寫小說就是寫人物的脈絡始終未變,這也是漢語小說的獨特性所在。那么,怎么寫人物?簡單來說,就是貼著人物來寫,性別、年齡、家庭環境、族群、飲食、地方性、時代背景、文化教育、交往圈子等等,都是要考慮的要素,如此,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方面的刻畫才能趨近別林斯基言及的“熟悉的陌生人”。以此反觀趙俊杰的創作,在貼著人物來寫這方面,需要做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人物的心理活動要剔除作家自我的代入,比如,小說中其他人物的處理,也要做到“人皆有其聲口,人皆有其形狀”。總的來說,只要小說中的人物站立起來,如同托爾斯泰的夫子自道,他會自行奔跑,帶著作家的筆觸向前運動,這樣的人物,對于讀者而言,必然有著內在的爆發性力量。
參考文獻:
[1]恩格斯.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7.
[2]恩格斯.致斐·拉薩爾[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1.
[3]朱向前,傅逸塵.當代軍旅文學的精神傳統[J].當代文學研究資料信息,2009(05).
[4]譯文[J].19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