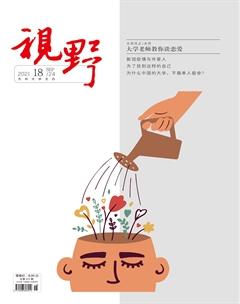大學老師教你談戀愛
王一博
“如果以下的男性品質換算成金錢,而你的手里只有五塊錢,你會怎么選?”武漢理工大學職業(yè)發(fā)展教研室教師張曉文在大屏幕上列出這道題,課堂上的學生們開始嘰嘰喳喳地討論起來。
“帥氣的外表三塊錢,忠誠三塊錢,富有三塊,浪漫一塊,身體健壯一塊,風趣幽默一塊,聰明機智一塊。”大二學生鄒濤把這道題發(fā)給在長沙上大學的女朋友,問她怎么選,女朋友夸了他一通,“你身上的品質遠遠不止五塊錢。”
大部分學生都優(yōu)先選擇了“忠誠”。一個高個子、聲音洪亮的女生站了起來,她是第一個選擇“富有”的女孩,她認為物質是維持一段親密關系的基礎。底下有學生鼓掌,張曉文鼓勵她說:“這是非常誠實的答案。”
另一位嬌小的女生站起來,給出一個新的思路:“找男朋友和找老公是不一樣的。”如果是男朋友,她會選擇帥氣的外表、身體健壯和幽默風趣;如果是結婚對象,她會選擇忠誠、浪漫、身體健壯。有個男生私下嘀咕:“講這么多有什么用,還不是要有錢。”碰到價值觀不同的學生,張曉文也想站出來理論一番。這是《愛情心理學》選修課上腦力激蕩的時刻,各種觀點在交鋒。
這些年,《愛情心理學》一直深受大學生的追捧,張曉文后來又在中國大學慕課平臺開課,其他高校也將這門課程作為選修課。今年“兩會”期間,有政協(xié)委員建議構建和完善高校婚戀教育體系,將婚戀教育設為高校學生必修課。還有媒體稱,近九成大學生支持開設婚戀課。這是張曉文不曾預料的,她十年前開設《愛情心理學》,“更多的時候是讓我們認識愛情,或者激發(fā)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不是把你培養(yǎng)成一個愛情高手”。
一堂課,十秒被搶光
鄒濤提前坐在電腦前,選課時間一到,他準備快速搶下張曉文的選修課《愛情心理學》。這一次,全校有1400人選了這門課,最后只有100多人選上了。
搶課成功后,鄒濤松了一口氣。他和女朋友高中時就在一起了,上大學后,異地戀中的鄒濤遇到不少煩心事,他想這個課程可能對自己有幫助。
“十八九歲的男孩女孩,正是對異性充滿好奇和渴望的年紀。但他們往往不懂得如何與異性交往,缺乏與異性相處的能力。”張曉文做過輔導員,當過心理健康老師,她很清楚這個年紀的學生在迷茫什么。她曾開過一門《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必修課,學生們總是催促她“先講愛情吧”。
在人際交往和親密關系上,大學生們往往不會表達,不敢表達。張曉文說,女孩基本不用教,她們可能會面臨很多選擇,這個時侯需要幫助她們認清現(xiàn)實,而男生更需要的是鼓起勇氣、樹立信心,他們是不一樣的。
但在中國的傳統(tǒng)教育里面,人們普遍認為愛情不值得學,不該學,年紀大了自然就會。“這其實是最可怕的觀念。”張曉文覺得,真心愿意學習的人,收獲幸福的可能性會更大。
2011年,張曉文決定開設《愛情心理學》。四年前,《愛情心理學》上了中國大學慕課平臺。張曉文記得,第一期開課時就有13萬多的選課量,討論區(qū)有20多萬的帖子。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高校也開設了戀愛課程,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情感心理學》、天津大學的《戀愛學理論與實踐》,等等。
與其他婚戀課不同,《愛情心理學》最大的差別在于張曉文很少強調自己的觀點,“它不是一門雞湯課,更沒有人生忠告”。她結合現(xiàn)實個案,讓學生們開展討論。
《愛情心理學》第一章是講人際吸引,“我們喜歡什么樣的人,這就是看臉的世界”。在課堂上,她一般先講一下友情,然后是關于愛的表達,之后會談一些愛情的理論。大部分學生其實很難獲得愛情,孤獨也是很重要的篇章。張曉文還會提及失戀的應對,關于大學的愛情與性等。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性別與教育研究博士崔樂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國內(nèi)一些高校的戀愛課往往有很強的實用性,“一些課程除了會介紹關于搭訕、撒嬌、溝通等相關的技能外,教師還會化身紅娘,把課堂變成相親現(xiàn)場”。上海大學《愛情心理密碼》的課堂上,老師收集了一份正在談戀愛的學生名單,并讓這些學生分享戀愛的經(jīng)驗。
崔樂建議,教師的視野不應僅僅局限于婚戀,應當引導學生批判性地反思主流的性與性別規(guī)范,提倡性與性別的多元平等,致力于建立一個公正的性別秩序。“比如說,我們是引導學生進入婚姻,視婚姻為人生幸福的唯一目標,還是鼓勵學生批判性地反思主流的婚戀觀念,尊重多元的親密關系實踐?”
年輕人都不戀愛了
張曉文曾受邀去計算機學院講課,她發(fā)現(xiàn)學生們都一臉懵懂。張曉文忍不住發(fā)問,底下有學生小聲回應:“老師,我們連戀愛都沒談過。”男生們普遍覺得生活壓力大,認為連自己都養(yǎng)不活,怎么戀愛?女生們有很多也更愿意追求事業(yè),覺得未來可以和閨蜜一起生活。
有一次線上上課,有個男生覺得現(xiàn)在沒必要談戀愛,他認為:“男人有錢了,女人就會撲上來。”張曉文立刻反駁他:“這種話表達出來,好女孩就會離你很遠。而且你有錢時想找的那些女孩,也未必是你真心想要的。”
張曉文希望自己的課程能夠激發(fā)學生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斷地維護親密關系。但現(xiàn)在大學校園里,最常見的愛情是,在一起很簡單,只要遇到一點困難,兩人就會立刻分開。有一次在課堂上,一位男生站起來分享,自己談戀愛三周就分手了,他的理由是:“我每天早上要給女朋友占座位,中午要陪她吃飯,每天要陪她八小時……我覺得好累,我沒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打游戲。”
聽到這些,張曉文為他惋惜,為什么現(xiàn)在愛情變得像速食,來得快、去得快?因為大家都不愿意忍讓。“大家都不愿意付出和忍耐,現(xiàn)在所有的奉獻犧牲這些詞全部變成了貶義詞,助人型人格、付出型人格現(xiàn)在都慢慢消失了。”張曉文說。
這種趨勢看下去也很可怕,大家又孤獨又難受又壓抑,其實并沒有幸福可言。這讓張曉文隱隱覺得,高校婚戀教育勢在必行,需要大力地去引導學生們。
脫單不是最終目的
有的學生線上、線下聽了三遍,張曉文問他怎么還來啊,學生回答,還沒有脫單啊。“他們想多了,就是一些自我表達、與他人交往這種基本的技巧。”張曉文說。有時,她在課堂上也會傳授一些技巧。大部分學生沒有戀愛經(jīng)驗,他們可能有喜歡的人,只是在觀望等待。為了鼓勵他們做出行動,張曉文布置的作業(yè)是讓學生們在本學期找到一個異性朋友,她還讓學生制定一份詳細的脫單計劃。有人在作業(yè)里寫道:“三天內(nèi),要勇敢地坐到喜歡的人身邊。”
盡管脫單的學生能直接獲得滿分,但張曉文表示,脫單不是這門課的最終目的,“對愛情要有敬畏之心,學會維持親密關系,這才是目的”。
鄒濤也是這樣想的,他認為,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可能會讓自己有一個更好的定位,對未來不會過于焦慮,內(nèi)心會有一個方向感。他和女朋友談戀愛三年了,每次課后,鄒濤總會將張曉文提出的問題和討論,在QQ上發(fā)給女朋友。上一節(jié)課中,張曉文提到女生耍小脾氣小性子,是為了看看男生有沒有擔當和責任心,鄒濤覺得在理,以后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張曉文每天仍在接收無數(shù)人的愛情故事。自從在慕課平臺上課,很多人給她寫信求助,多是在情感經(jīng)歷中遇到了困惑。張曉文一般會以鼓勵為主,若對方有特別嚴重的情緒問題,她會主張去看心理醫(yī)生。
授課的過程中,她也在感受這門課的意義。有一次,張曉文讓學生們畫一條生命線,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遇到的好事向上畫一個箭頭,壞事則向下畫。一個學生的生命線上,所有的箭頭都是朝下的。這個男孩個頭矮小,從不主動回答問題,被點名時總是結巴、臉紅。在他很小的時候,父母離婚了。后來,他父親出車禍去世,他被寄養(yǎng)在親戚家里。張曉文仔細看了他的生命線,發(fā)現(xiàn)有一個小小的箭頭是朝上的,旁邊寫著“遇見曉文老師”。
(摘自《Vista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