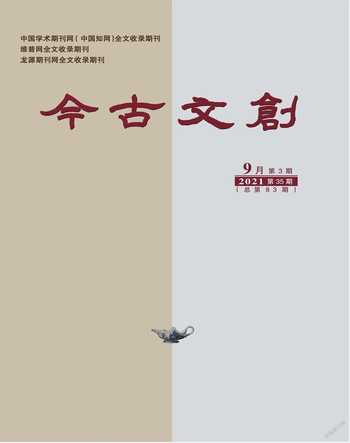芥川龍之介漢詩與中國文人關聯之研究
王心禹 金湘琳 汪心怡
【摘要】 芥川龍之介(以下簡稱“芥川”)除了是位享譽世界的小說家之外,還是一位漢學家。關于他的小說研究頗多,而對其漢詩的研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僅限于少數研究者。芥川生平創作的34首漢詩,因僅附在友人的信札中或受托題于畫作上,故而對其漢詩的研究少之又少。本課題將在現有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析出其漢詩的關鍵詞并構建芥川漢詩的表現手法體系,探討其漢詩中的中國要素,和與中國文人之間的關聯。
【關鍵詞】 芥川龍之介;漢詩;中國文人;桃源鄉;禪
【中圖分類號】I313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5-0026-02
芥川文學在中國、日本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雖然國內外關于他的小說研究有很多,但對他漢詩的研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僅限于少數研究者。而還未形成對芥川漢詩系統整體的研究,有個別的整體研究也只停留在注釋,言及的淺入淺出的階段,國外如村田秀明(1984)、村田秀明(1989)主要介紹了芥川漢詩的創作背景以及詩歌的意義,但并未從細節進行分析;國內如邱雅芬、沈雪俠(2006)、邱雅芬、劉文星(2005)從創作背景、詩歌內容方面加以概說,輔以對中國詩歌的聯想和分析,劉默(2014)對所有的漢詩進行了分類,如山水田園詩、旅愁詩等。但都缺乏對芥川漢詩的整體觀照,還有深入的余地。
隨著國際化的逐步發展,不同國家間文學方面的交融是必不可少的,芥川的漢詩是日本人用中國漢字寫出中文詩,這本就是文化交流的體現。而現在對于芥川漢詩的研究還處于初期,未來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研究的行列中,這樣才會使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化更加走向世界。因此,本文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以“桃源鄉”和“禪”的意象為視點,將芥川與中國文人的關聯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這對提升中國文化在日本文學中的價值也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如劉默(2014)也提到了芥川詩與陶淵明詩的關聯,并對芥川的詩風進行了分析,但只是從芥川漢詩的字里行間找出陶淵明的影子,且盡管能看出清幽之意,但卻并未系統從中析出意象加以分析。
一、芥川漢詩中“桃源鄉”與陶淵明之關聯
任常毅(2002)提出“芥川的漢詩,深受漱石和白居易的影響,而探其源可以說他承繼的是陶潛的詩風”,但只是籠統介紹了芥川詩與陶淵明詩風相似,并未對二者進行意象上的詳細對比分析。通過分析芥川34首漢詩,有16首漢詩中都含有包括山水竹石等“桃源鄉”的意象,并且在前期漢詩中出現得尤其頻繁。
基于熊沐清(2020)比較認知詩學的理論可以知道,“比較認知詩學的基本含義是:基于認知科學的文學對比分析和研究,即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比較文學(比較詩學)所關涉的問題,同時,也運用比較的視野和方法進行認知詩學研究包括研究認知詩學本身。”其中研究類型可以分為4種:一是不同范式流派之間的比較;二是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三是對比較的對象進行認知研究;四是對不同文明進行研究。因此,本文將運用“比較”研究類型中的第三、四種,即:“對比較研究的對象進行認知分析”(芥川與陶淵明漢詩中的意象)并將“不同文化/文明間文學進行認知比較”(日本作家芥川與中國古代文人陶淵明的漢詩),從中探求芥川漢詩與陶淵明之間的關聯。
從認知方面來看,“春寒未發早梅枝、幽竹蕭蕭匝小池。”(明治45年1月1日,山本喜譽司宛)中的“幽竹”“小池”;“放情憑欄望,處處柳條新。千里洞庭水,茫茫無限春。”(大正4年6月29日,井川恭宛)中的“柳條”“洞庭水”等都是“桃源鄉”意象的具體化的物。還有“閑情飲酒不知愁、世事拋來無所求。笑見東籬黃菊發、一生心事淡于秋。”(大正4年10月11日,井川恭宛)中的“東籬”“黃菊”更是“桃源鄉”意象的典范。
再從認知屬性和認知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比較”特性來看,陶淵明詩(《飲酒》):“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菊”“東籬”“南山”等意象即是陶淵明閑適淡薄的心境意境的經典詮釋方式。
芥川漢詩中,還有“靜讀陶詩落燭花”(大正元年12月30日 小野八重三郎宛)、“陶詩讀罷道心清”(大正2年12月9日,淺野三千三宛)兩首直接提到“讀陶詩”,無論是從“桃源鄉”意象還是從他在漢詩中對陶詩的提及程度,都能分析出芥川對陶淵明的詩風是崇拜與借鑒。芥川在《漢文漢詩的趣味》一文中也提到過“許多漢詩的意境與我們的性情完全合拍,漢詩漢文中所包含的使我們受益的東西多得超出我們的想象。”從中可以看出,陶淵明也是芥川漢詩漢學研究學習的重要對象。這一點通過芥川的34首漢詩中有18首包含著桃源鄉意象的詩歌里也能看出。芥川詩中強調的對不理世事,淡薄閑適生活的向往之情通過這些意象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通過此類山水田園詩表達的愁緒也與陶淵明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陶淵明的詩風深入芥川漢詩的靈魂。
二、芥川漢詩中“禪”與蘇軾之關聯
芥川的漢詩中,除了“桃源鄉”意象,還能找出很多與“月”“茶靄”等相關的意象,比如“簾外松花落,幾前茶靄輕。”(大正9年4月11日 松岡譲宛)“我鬼先生枯坐處,松風明月共蒼蒼。”(大正9年3月3日,小島政二郎宛)。通過這些詩句中的意象,可以輕易找到孟浩然、王維等中國古代文人的影子,但由于意象內容的散亂性,本文暫未進行體系化的研究。盡管如此,仍然能看出芥川的漢詩寫作對于中國文人的學習是“集大成”的,吸收模仿了眾多文人的詩作風格。
其中,杜文倩(2003)提到,“芥川對這首《偶成》(琴琴侵階月,幽人帶醉看。知風露何處,欄外竹三竿。)格外喜愛,曾與多位摯友共賞,詩中的意境給人一種禪境仙鄉的遐想。”通過對本詩意象進行分析,可以的析出關鍵詞“月”“風”“竹”等。李明華(2011)解釋可以理解為禪就是關于“修心”的學問。通過其中佛禪寺院在北宋時期功用的分析,可知佛禪寺院常為山水旅游勝地或精神皈依之所。那么茂林修竹、山水幽靜的意象詞當然也可以自然地歸入“禪意”意象關鍵詞,通過對這首詩的意境和意象的分析,不難推論其漢詩與中國古代文人蘇軾充滿禪意的詩歌有著極其相似之處。
從“認知”方面來看,用“禪”入手,可以發現芥川的34首漢詩中有25首中都含有煙雨茶譚等相關意象。從中能輕易讀出“禪意”,如上文提到的“幽竹”“風月”以及未提到的“龍團”“山水”等。比如詩句“放情憑欄望,處處柳條新。千里洞庭水,茫茫無限春。”(大正4年6月29日,井川恭宛)中的“柳條”“洞庭水”,明顯就是前文提到的山水幽靜之意象,禪意自現。而“叢桂花開落,畫欄煙雨寒。琴書幽事足,睡起煮龍團。”(大正4年12月3日,井川恭宛)中的“煙雨”“琴書”“龍團”“窮巷賣文偏寂莫、寒廚欠酒自清修。”(大正9年5月15日,與謝野晶子宛)中的“窮巷”“賣文”“寒廚”這類清幽空靈的意象詞中,也可以析出“禪”意,更可以看出芥川心中對于禪意仙鄉的向往與憧憬。
再從“比較”方面來看,上面的芥川詩與蘇軾的“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等詩中的意象極為相似,是芥川受到蘇軾詩及想法的影響的見證,也是芥川對心中禪道追求的證明,可以看出蘇軾對于芥川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在大正這樣一個對于芥川來說極為特殊的時期,通過漢詩中的禪意深刻中和了芥川失戀與初入文壇時的迷茫心境,并表達出芥川對于清靈禪境的熱愛。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桃源鄉”意象所表現出的對田園山水、恬靜生活的向往情境恰好是“禪”的意象所展現的一部分意境。綜觀芥川的34首漢詩,可以看出芥川詩中蘊含著內心的寂寞、孤獨、哀傷,而“桃源鄉”“禪”這種意象表達出來的或恬淡,或清幽的意境正是芥川所無限追求的。芥川通過大量使用“桃源鄉”“禪”的意象來營造出他心中的禪境和桃源鄉,為現實生活中的不如意尋找一方凈土,為煩亂的心情與思緒辟一隅安寧。
三、結語
本文通過結合認知比較詩學的理論與“桃源鄉”“禪”為視點,分析了芥川龍之介漢詩與中國古代文人陶淵明、蘇軾的關聯,為后續芥川漢詩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點。
從中可以看出芥川的漢詩承繼陶淵明的詩風,因此與陶淵明的詩風最為相似,“桃源鄉”意象也就出現得最為普遍,而隨著其對漢文學、漢詩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受到中國文人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多樣化,以蘇軾的禪道文化最為典型,這對芥川以后的文學觀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參考文獻:
[1]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M].日本:巖波書店,1997.
[2]村田秀明.芥川龍之介の漢詩研究[J].方位,1984,(3).
[3]村田秀明.中島敦と芥川龍之介の漢詩[A].田辺幸信.中島敦光と影[C].日本:親友堂,1989,(3):363-397.
[4]邱雅芬,沈雪俠.論芥川龍之介的早期漢詩[J].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01):30-32+47+63.
[5]邱雅芬,劉文星.論芥川龍之介的中晚期漢詩[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3):104-107.
[6]劉默.關于芥川龍之介的漢詩考察[D].吉林大學,2014.
[7]任常毅.芥川與漢文學——以漢詩為中心[A].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日文系.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研究論叢(第一輯)[C].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日文系: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2002:9.
[8]熊沐清.比較認知詩學的理論建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08-31(003).
[9]杜文倩.文化匯流中的抉擇與創造[D].湘潭大學,2003.
[10] 李明華.蘇軾詩歌與佛禪關系研究[D].吉林大學,2011.
[11] 王書瑋,莊鳳英.關于《芥川龍之介全集》中的漢詩研究——以大正4年(1915)為研究視角[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8(01):70-7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