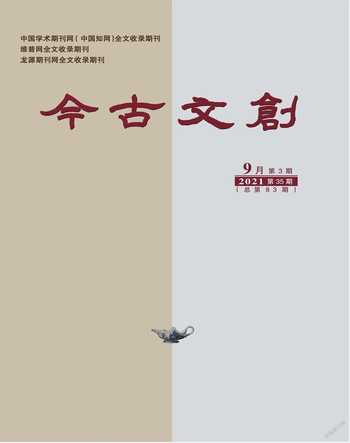百花深處,伊人何歸
【摘要】 第五代導演陳凱歌所執導的《百花深處》是影片《十分鐘年華老去》的最后一個單元。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影片,短短十分鐘,平實幽默,卻引人深思。導演充分運用精美的視聽語言、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加以角色與細節的精心設計,表現了在老北京快節奏的城市化進程中對于漸漸遺失的傳統文化的思考。
【關鍵詞】 《百花深處》;陳凱歌;文化;反思
【中圖分類號】J90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5-0087-02
城市化進程中,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論是經濟建設、社會建設還是生活方式都在不斷地進步。但是,在快節奏的現代文明建設的過程中,那些仍舊想要活在慢節奏的傳統文明中的人,他們的精神似乎無處安放,像一個個搜集者,不停地尋找他們過去生活的影子。同時,也不得不讓人們思考,該如何更好地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對于傳統文化是有著深厚感情的,他執著于人文主題,以理性主義精神反思在現代化過程中新舊文化交替,密切關注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在《十分鐘年華老去》中也不例外,單元影片《百花深處》是具有藝術性、反思性和觀賞性的,其延續了陳凱歌的人文主義風格,追尋著被人們遺忘的傳統文化。影片敘事脈絡清晰,講述了一位瘋癲的“老北京人”馮先生與搬家公司的故事。影片從一場喧鬧的搬家戲開始。一位居住在百花深處胡同的馮先生請搬家公司為他搬家,搬家公司到達后發現他的家已然成為一片廢墟,為了要回搬家費,不惜上演了這場看似滑稽實則意味深長的“搬家戲”。在對影片《百花深處》的分析中,本文將從視聽語言、意象表現、角色設計等方面分析,揭示該影片所隱喻的意義。
一、主題展現——新舊文化碰撞下對傳統文化的追尋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越過人世滄桑的斑斑銹跡,在經過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痕跡。在片中可以看到,去往搬家的路途中,現代的貨車上搭載著的是一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老北京人,他誤以為開錯了路,說明他對于這座城市已經漸漸陌生了,足以反映出部分老北京人對于快節奏的城市化進程的不適應。當到達胡同口時,搬家頭兒看到滿是“拆”字的破壁也露出了不解的表情,說明了現代北京人對于傳統胡同也是陌生的。而后帶有陳氏黑色幽默的虛擬“搬家戲”上演,引起觀眾一笑的同時也會引起深刻的思考。《百花深處》以胡同命名,快節奏的生活里,一個“拆”字便決定了其狹小不能滿足現代社會要被淘汰的命運。拆遷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重要的一步,導演用拆遷使得胡同消失表現了現代工業文明對于傳統文明的沖擊;以一位瘋癲的老北京人對于過去家園的念念不忘表現現代與傳統文化的碰撞;以高樓大廈與殘敗胡同反映社會變遷與文化傳承之間的矛盾;以最后鈴聲與槐樹的青蔥尋回了對傳統文化的寄托。棄舊建新,拆除殘敗的百年老宅,讓人們搬進富有現代化的新宅,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導演運用理性精神對于現代化拆遷中所面臨的對傳統文化繼承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
二、視聽語言——傳統被吞沒的不堪
(一)鏡頭的運用
全片103個鏡頭,多為中近景。
(二)拍攝角度的運用
影片一開始便是一個自下而上的仰拍鏡頭,展現了一棟現代化的高樓,此鏡頭不但交代了環境,更能夠給人心理上的沖擊,壓抑和束縛住人們的神經,讓人想要逃往一個輕松自在的環境。此鏡頭也隱喻了在順勢而來的現代文明面前,傳統文明顯得那么的無力。
貨車行駛在馬路上,馮先生的主觀鏡頭看到的是筆直的高樓大廈快速閃過,既展現了現代城市的真實,也反映了現代生活節奏之快。人物交往關系中,鏡頭的視點也在發生著變化。起初在高樓下,馮先生找搬家頭兒說話,鏡頭多俯拍馮先生,仰拍搬家頭,這表現了現代文明的“強勢”。隨劇情發展,馮先生站在百花深處的槐樹下,畫面呈現了對馮先生的仰拍以及對搬家公司人的俯拍。從拍攝角度的轉變足以看到導演迫切想要轉變的文化態度。
(三)構圖的運用
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封閉式構圖,展現的是汽車后視鏡中看到的站在槐樹下的馮先生對遠處的張望。后視鏡的框與框內的人組成了一個“囚”字,表現出了現代化的進程對于傳統老北京人思想的束縛。
(四)聲音的運用
1.對白的運用
耿樂口中的“就這老北京才在北京迷路呢”,一句話道出了北京現代化進程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給錢就搬”這句話體現出了當下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變得唯利是圖。隨劇情發展,“干嗎呢?悠著點”也看到了他態度的轉變,他與馮先生的距離正在一步步拉近。馮先生問搬家公司的人:“花瓶應該在哪兒?應該在堂屋,在堂屋的條案上”,短短的對白足以看到傳統與現代文化交織下,現代人對于傳統文化的缺失。馮先生在撿到鈴和鐺后都不停地念叨著:“這不在這兒呢”表現了馮先生已經找到了他對于過去文化和思想的寄托,以搬家公司為代表的現代人好像也看到了傳統文化的魅力。足以說明,影片中每一句對白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2.音樂與音響的運用
在電影中,“音樂是作為一種心理對稱介入的,目的是給觀眾提供一種元素幫助他們去理解影片段落中所具有的那種與人有關的音調。”(引自美國波布克的《電影的元素》第52頁)音樂使用的得當能夠強有力地加強某段時間或某場戲的戲劇作用和深度。
影片開始的鞭炮聲預示著喬遷之喜,直接展現了故事的背景。小孩子叫喊著“我的電腦呢”,表現出了現在的孩子比起傳統文化來說,會更加迷戀現代化的電子設備。
汽車行駛在公路上汽笛聲展現了工業文明的進程,百花深處胡同的拆遷的音響聲給人帶來懸念的同時,也不免帶給人一種荒涼感。
“影背”“后堂”等詞語剛說出來的時候甚至顯得特別滑稽,但等到影片主題切到深處的時候,就會感到非常震撼。
音響與音樂運用最出色的部分便是搬家。搬家工人開始搬,有節奏的鼓聲也配合著劇情的發展響起來了,富有獨特韻律和喜劇效果。導演對于空手搬道具時的音響獨具匠心的運用,讓人不得不拍案叫絕。如家具的“咯吱”聲、魚缸內的流水聲以及花瓶摔碎的聲音。花瓶打碎后,歡快的鼓聲變成了悲傷的笛音。正是這些聲音的運用使得虛擬空間變得真實起來。同時,也讓人們不禁反思,是不是應該為傳統文化做些什么了?
片尾由清脆的鈴鐺聲引出了水墨畫,古韻悠悠,伴隨著空靈的音樂使得人們尋找到了過去那份美好。
(五)色彩的運用
本部影片以黃、灰為主色調,無論是景物還是衣物都特別暗淡。馮先生戴著黃色帽子,穿著紅色的衣服,而外面卻罩上了一件灰色的外套。故宮紅和琉璃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而那件灰色外套正如鋼筋水泥一般束縛了傳統文化的生長。影片的最后呈現了虛幻的四合院彩色水墨畫,與馮先生的衣物色彩相似,只是那么美好的事物早已逝去,留下的是一片廢墟,引起人們萬分惋惜之情。
三、意象獨特的表現——尋根之旅
(一)槐樹
“若問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從明朝開始,這句民謠便不絕于耳。從古至今,人們便把大槐樹和老鴰(鸛) 窩視為民眾便于傳承歷史記憶的符號。大槐樹不僅是中華兒女魂牽夢繞的精神寄托,更承載著先人對故土家園的依戀和顧盼。在本部影片中,大槐樹是馮先生“家”的標志,也會給人生發出一種心安之感,讓人們不禁幻想到四合院此前的熱鬧景象。導演運用大槐樹隱喻為一種傳統文化的根,申訴著傳統文化的消逝。
(二)鈴鐺
馮先生提著鈴鐺說道:“遇到刮風下雨的時候,叮叮當當好聽著呢。”銹跡斑斑的鈴鐺正是馮先生對于以前百花深處慢生活的象征,如今再次撿起,只剩下這個“叮叮當當”的鈴鐺讓他追憶。那鈴鐺也似乎是打開傳統文化的一把鑰匙,他口中不停地念叨著“這不在這兒嘛”似乎是導演試圖表達傳統文化盡管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但其并未消亡,依舊值得人們去追尋。
四、人物設立——品京都遺韻
馮先生作為片中主角,其語調、神態、動作都可圈可點。從語調來看,操持著一股子京腔,自稱“先生”,加以蘭花指的動作和夸張的神情,不禁讓人想起了梨園戲子。人們都認為馮先生是個“瘋子”,可他對于自己家的路線、物件的位置記得那么清楚。他不是瘋了,只是慢生活的消失殆盡,讓他努力尋找自己精神的寄托,可始終都那么費力。
陳凱歌說過:“全球化的東西,就是用一種非常暴力的力量來橫掃你的文化,讓你的文化無立足之地。你的生活方式都變了……在大槐樹底下搖著芭蕉扇的中國人,變成了在冷氣房里的中國人。其實這是值得憂慮的事,就是我們真的喪失了那些無形中支持我們的東西,支撐著我們的這些東西。”當傳統文化這個物質家園被摧毀之后,人類的精神家園也將無枝可棲。正是這樣,才造成了現代人看到的馮先生的“瘋”。
綜上,《百花深處》作為一部尋根電影,是現實的精神鏡像。導演運用生動的視聽語言和獨特的意象設計,讓人們感受到生命轉瞬即逝,在時間面前人們總是顯得那樣渺小、無助、脆弱、甚至不堪一擊的感受,也告訴人們走得太快,不要忘記看看來時的路。
參考文獻:
[1]劉洋.消逝的“慢”歌——淺析陳凱歌《百花深處》[J].今傳媒,2013,21(07).
[2]張效利.北京的老去年華——評陳凱歌電影短片《百花深處》[J].電影評介,2015,(15).
作者簡介:
邊永紅,女,漢族,山西晉中人,山西師范大學,本科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