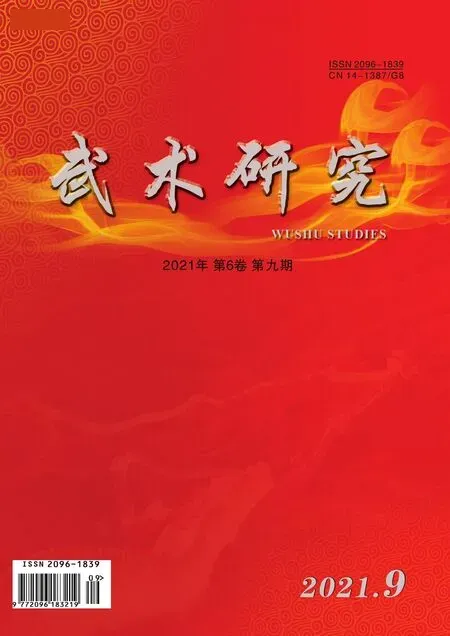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尋繹研究
王 帥 路國華 楊惠蘭
長江大學教育與體育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1 前言
一種文化從產生、發展、衰落、再創新到再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其中會受到特殊地域、特殊時期、特殊政治經濟背景等的影響,因此對于處于鄂西南這個特殊地域的土司體育文化的歷史探究也不能割裂諸多因素對其造成的影響。這樣才能在了解這種特殊文化的復雜內涵的基礎上推動現代社會對土司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2 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屬性
地域性,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總是會受到特定地域其他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民族文化自然也會受到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鄂西南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土司文化濃厚的地域特色,這在擺手舞、撒爾嗬、肉連響等土司體育舞蹈的展現形式中就可見一斑,在特殊的地域中形成的民族體育具有很明顯的識別度。民族性,鄂西南是土家族、苗族、侗族、漢族等民族的聚居地,
長期的雜居生活,使得鄂西南土司文化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單就體育文化來說,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豐富性,傳統文化的確在傳承的過程中展現的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內容,但是如果將精神文化的載體僅僅理解為各種典籍、體育動作形式等宏觀表面內容在一定層面上就局限了民族體育的內涵。李瑩、李雨衡在《土司體育文化理論建構研究》中將土司體育文化分為四種:體育物質文化,指展現體育文化的物質形態,如恩施土司城、擺手堂等;體育制度文化,即土司統治時期形成的成文法以及各種習慣法;體育精神文化,即為了維護土司統治以及安撫民心而表現出來各種意識形態以及體育行為文化,即通過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化形態。
3 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與地理環境
在《風俗通義》和《漢書》等著作中都曾提到過“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說明不同的地理環境,甚至是同一地理環境由于地域廣闊也會存在民風民俗的差異。一是武陵山區復雜的地形使得村落之間、村民之間相對分散的居住特點,造成文化地緣性的差異,地處鄂西南的地區,是絕大多數土家族和一部分苗族的世居地,侗族等其他民族則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遷進來的。鄂西南地區地形復雜,以山地居多,同時物廣人稀,因此很多活動都是以集體形式進行的,通常是一個村寨或者幾個村寨一起進行,而這些村寨通常會形成相對獨特的民族文化,板凳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板凳龍”由龍頭、龍身、龍爪三部分組成,利用三腳高凳和竹片一起進行,活動的很多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簡單便利,既起到了娛樂的作用同時又加深了民族感情,利于民眾團結。[1]二是鄂西南地區地理環境較為封閉,與外界的聯系較少,在地區內存在著民族融合的現象,以武術為例:土家族的拳術,多攻打近攻,動作迅疾,拳勢猛烈,剛勁有力;而苗族的拳術則氣勢剛烈,步伐穩健,招法多變。[2]可以看出,雖然苗拳和土家族的拳術存在著不同的特色,但是境內的民族并不是互相割裂存在的,互相之間在交流過程中存在著相互改進的方面,因而兩種拳術也呈現著相似之處,而這也是當地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共同造就的結果。三是在特殊地理環境基礎上形成的勇猛好斗的圖騰文化,在鄂西南地區內巴人是土家人的主要構成,因此土家文化和巴文化是一脈相承又互相衍生的,在鄂西南的眾多景點中都有跡可循,例如在清江附近的“巴公山”“巴公溪”等都可以看出來兩者的相互影響。同時在精神文化層面,巴文化的圖騰崇拜也漸漸的深入鄂西南各民族的心中,其中尤以白虎崇拜著稱,例如恩施市、利川市、宣恩市的很多地方都冠以“白虎堡”“白虎山”等地名。巴人的后裔土家人就曾經在其為逝者送喪時跳的撒爾嗬中體現出“猛虎下山”“抱虎頭”等通過擊掌、撞肘、撲躍動作等模仿白虎的動作形態。[3]四是土司治下的鄂西南地區在古代屬于邊疆蠻荒地帶,相對于武夷山地區、黃土高原地區的土司統治而言,內外壓力相對較大,因此出于統治需要形成的尚武文化,這也是古代土司為了保衛邊疆必須進行的一項措施,例如明朝崇禎統治時期兵部尚書張鳳翼就曾對恩施地區的士兵制度進行評價到“施州士兵,頗稱勇敢,登崖涉顛,如履平地,要剿依山之賊,非依彼不可”,其中更是涌現了許多民族英雄,巴蔓子將軍、羅榮光將軍、鶴峰的“范家五將”等,這體現了土家文化中含有的深厚的民族情懷以及頑強進取、積極上進的品質。
4 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與生產勞動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元明清時期的中國采用的經濟模式依然主要是小農經濟,因此生產力發展相對穩定和緩慢,而且在這一時期國家經濟相對強盛,民眾除了日常的生產活動之外有了一定的時間來創造和發展土司體育。因此在勞動之余,更是將勞動過程以體育舞蹈的形式展示生產勞動的過程、豐收后的喜悅甚至形成了一定的風俗習慣。
土家族的“舍巴日”,即漢譯的擺手舞,就是反映生產勞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古老的土家擺手舞是土家人們在生產勞作、獲得豐收之后用以祭祀祖先、敬謝天地的祭祀舞蹈,展現土家族人民的農事、狩獵、生活景象,例如其中的“犀牛看月”“趕猴子”等舞蹈形式與狩獵情景相似;而“紡棉花”“種包谷”“撒種”等又展現了土家人們從事生產活動時的情景。土家族土司也通過這種方式來緩解社會矛盾,維護土司統治,更命令修建擺手堂來為土司人民提供休閑娛樂的場所。
豐富的娛樂活動與經濟的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元明清時期土司經濟也呈現繁榮之勢,如:在《恩施縣志》中曾提到元朝時期的土家族人民“客民趕場作市,設有場頭、客總,土著只有十之二、三,余俱外省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小農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之后,土司們和土民們就自然會有休閑娛樂、相互聯絡感情的追求。民族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自然也增多了,中央實行的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地區的民族特色,但是在主流文化方面仍然堅持中原文化的正統地位和儒家文化,多民族之間互相融合,互相發展。土家族的儺戲文化就是中原地區的漢文化傳入土家族地區,并與土家族原始的巫文化結合而形成的。[4]
5 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與宗教祭祀
宗教是統治者維護統治和安定民心有力的精神武器,利用宗教的神秘性和普通民眾的愚昧來維護統治,甚至剝削人民,而同時很多民眾會自覺遵守土司的統治。土司們利用政教合一的統治賦予自身“神”的意志,以宗教為工具來收服人心。例如:土家族土司將代代相傳的擺手舞賦予“祭祀先人,求福娛神”的功能。[5]土司們通過舉辦一系列的宗教祭祀活動,提供祭祀的場所間接地也為民眾提供了一些體育活動的形式和場所,促進了民族體育的發展。帶有宗教色彩的土司體育文化對于凝聚民族,發展文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在民國時期的《永順府志》就記載了“司治二里許,有教場坪,土人常駐于此處演武”。宗教文化與體育文化的結合無疑使土司統治下的人民有了精神寄托。
很多宗教精神是通過節日的形式展現的,例如傳統土家族有擺手節、過趕年、牛王節等三十多種民族節日,以其中流傳比較廣的女兒會為例,女兒會發源于恩施市東北140多公里的恩施市紅土鄉石灰窯鎮,女兒會的產生不僅僅是土家族人民關于婚嫁的習俗,同時也是與中國的傳統節日中元節聯系而發展形成的。中元節俗稱“鬼節”,在恩施一直有“年小月半大”的說法,從初一到十二日皆為“月半”,這段日子不僅僅是舉家團圓的日子,也是祭祀祖先的日子。女兒會恰逢七月十二日,不僅體現了土家族人民對生與死的豁達態度,同時也包含了男女交往、繁衍后代的積極意義。此外,在土家族的文化傳統習俗中,一直有在親人正常去世時跳撒爾嗬、唱喪歌的習俗,這也印證了土家族人民的達觀的生死觀,等等這些都說明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的長期經驗中總結了很多富有智慧性和值得傳承的優秀文化。[6]
6 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與土司兵制
土司制度并沒有將“體育制度”單獨提出來,但是體育制度和體育文化是滲透在土司制度中的,如土家族土司就曾在《等級儀制告示》中講到“照得卯峒僻處一偶,乃朝廷之潘鎮,荊南之保障,世受宣撫使,守鎮邊夷”因此為了鎮守邊疆,維護土司統治,勢必要讓土司人民習武強身,提高軍事力量和軍事素質,保家衛國。因此要了解體育制度和體育文化就要對整個的土司制度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夠明白體育制度對于土司統治、保衛邊疆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
7 鄂西南土司體育文化與游戲娛樂
體育活動的本質是為了滿足個人強身健體、休閑娛樂的需求。因此土司體育活動除了是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的工具,也是普通民眾釋放壓力、休閑娛樂的緩沖劑,在西南很多土司的統治下,特別是某些豐慶節日里,會通過摔跤、捶丸、狩獵等來聯絡土司之間、土司與土民之間以及土民之間的情感,同時也起到強身健體,休閑娛樂的作用,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7]將體育與游戲相結合的形式使得土司統治者能夠最大限度的貼近普通民眾,而民眾也能夠安居樂業,安于現狀而推動社會的穩定發展。
鄂西南境內的很多體育項目都帶有民族特性和娛樂性,有很多項目甚至進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表1列舉部分),以利川市的“肉連響”為例,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將傳統的“泥神道”進行再創造,并且提煉出其中的舞蹈元素,加入“蓮花鬧”和鑼鼓形成了一種群體健身舞蹈,而這種被譽為“東方迪斯科”的土家族舞蹈具有豐富的娛樂性,究其起源來看,最早的“肉連響”也是巴人歡慶勝利、表達喜悅的一種形式。[8]因此,賦予創造和想象的恩施土司人民在游戲娛樂之中也無形中創造了豐富的文化。再如宣恩縣的三棒鼓就是能歌善舞的土家人和打薅草鑼鼓的歌師們將薅草鑼鼓中的大鑼換小鑼,將旗子鼓換成小巧精美的花鼓,以常唱的山歌、哭嫁歌、梯瑪神歌的音調演唱起來,并用織西蘭卡普中的“龍鳳呈祥”、“富貴牡丹”等圖案繪制到鼓皮、鼓身上,稱為“花鼓”或“喜花鼓”,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一種民間曲藝藝術。這種曲藝藝術不分場合,隨時隨地都可以表演,對于人們紓解壓力,休閑娛樂以及滿足精神文化需求具有深刻意義。

表1 鄂西南地區部分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體育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