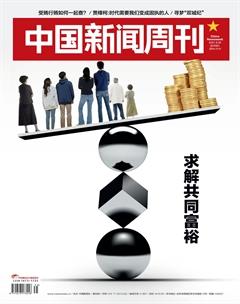賈樟柯:時代需要我們變成固執的人
倪偉

余華坐在餛飩店中央的桌子前,雙手捧著橫臥的手機,目不轉睛盯著屏幕。他突然發出一聲驚呼。鏡頭切到手機上,這位中國著名的先鋒作家,正在看一場美國的NBA球賽現場直播。
這是典型的賈樟柯式畫面:普普通通的中國面孔,帶著歷史痕跡的公共場所,以及突兀闖入的新科技和全球化景觀。這樣的場景在生活中司空見慣,而一旦放在鏡頭里被觀看,就變得耐人尋味。這是彌漫在賈樟柯電影的一種獨特氣息,他拍最普通的中國人的生活,卻總散發出陌生感。
這一幕出現在賈樟柯最新作品《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里。這是部紀錄片,于2019年拍攝。因為疫情等緣故,今年9月19日才在中國院線上映。電影里,馬烽、賈平凹、余華、梁鴻四代作家成為主角,由他們自己或家人講述親歷的共和國社會變遷。
賈樟柯一直保持著對故事片與紀錄片的雙重興趣,在他的作品序列里,兩者互相勾連又自成譜系。《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可以看作十多年前《東》和《無用》兩部紀錄片的延續,形成藝術家三部曲。但在他所有影片中,《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又有著獨特的位置:離開汾陽小城,第一次將鏡頭對準了他并不熟悉的農村。
9月9日,在北京工作室的放映廳里,賈樟柯向《中國新聞周刊》談起這部新作,以及他對文學、全球化、大銀幕和年輕影人的看法。
“電影最擅長的是記錄、紀實”
中國新聞周刊:電影里除了作家訪談,也抓拍了一些街頭巷尾老百姓的面孔、肖像,這是你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元素。你很早就有這種做影像記錄的習慣,這些畫面為什么會吸引你?
賈樟柯:電影這個媒介就是對我們生活的世界最直觀的呈現。現實生活中捕捉的這些畫面,形成了一種紀實美學。我一直對這種美感是感興趣的,真實、生動、自然,能夠呈現電影作為媒介的特點。我們說電影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紀實傳統,一個是戲劇傳統,但是電影最擅長的是記錄、紀實。
中國新聞周刊:你說過這部電影是記錄中國人的“心事”,幾位講述人都經歷過社會巨變,這些變革也體現在你以前的電影里。通過他們的講述,你有新的感受嗎?
賈樟柯:我過去比較多的還是小城經驗,小城跟農村雖然離得很近,但還是截然不同的。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是兩個世界。可以說這部影片是完整地進入到鄉村經驗。比如說馬烽的部分所涉及的社會運動、集體化,1949年之后,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人要被重新組織起來,確實是我過去思考之外的事情。
還有饑餓的問題,我經歷過一點。我五六歲的時候,食物種類太單一,只能吃窩頭,沒熱量,中午就餓了。在拍攝的時候,我發現每代人都有饑餓的問題,按理說梁鴻已經是70后了,但也有吃飯的問題。所以吃飯問題還是貫穿在這個國家之中的焦慮。我是一個歷史迷,原來有很多概念,但通過這個片子把概念變成了感受。
中國新聞周刊:你之前對鄉村經驗和鄉村敘事感興趣嗎?
賈樟柯:感興趣。我理解鄉村有兩個切入口,一方面是親身感受,一方面是通過閱讀。我有農村的親戚,會幫他們做些農活。在梁鴻的部分,我特別有感觸的是考學。我有個表姐是農村戶口,當時就在我們家住,她在汾陽中學借讀,高考連考好幾年,就是希望跳出農門。這完全就是我的個人經驗,完全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閱讀。中國文學一直到現在保持對農村的關注和書寫,像賈平凹老師一直還在寫農村。
中國新聞周刊:這四位作家哪一位的作品對你影響比較大?
賈樟柯:后三位對我影響都比較大。馬烽先生書寫的五六十年代離我比較遠,更多是通過改編的電影來了解他。80年代初上高中就讀賈平凹,讀過《雞窩洼人家》這些經典小說,小說呈現出來突破禁區、對人性的拷問,是一種文學精神,對我們是有影響的。讀余華是在《收獲》雜志上,中學快畢業或剛畢業時碰到了《活著》,小說帶有80年代以來的那種創新性,創新性本身是很吸引我的。讀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時,我自己也開始轉向一些非虛構拍攝,拍了《二十四城記》和《海上傳奇》,有很深的共鳴感。因為社會問題、鄉村問題以及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問題,都是我們同時代的話題。只不過我作出了電影的反應,她作出了文學的反應。
我覺得有趣的是,我比較關注同行的工作,電影不是孤立的藝術,是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大家有時候會有一種精神上的會心一笑,有時候也會發現差異性。這種對話關系,是通過觀看對方的電影、讀對方的小說形成的內在的對話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