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源流與寫作
郝建國 劉江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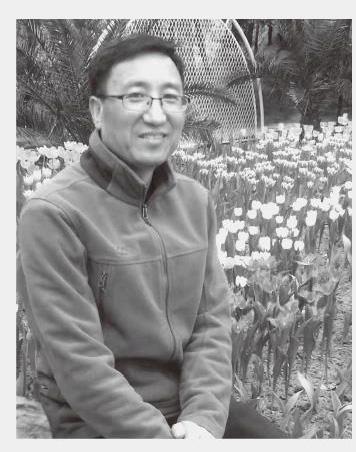

郝建國,文學碩士,編審,花山文藝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編輯學會理事,中國辭書學會理事,河北省作家協會理事,河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發表論著逾百萬字。責編圖書《多瑙河的春天》入選中宣部2019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
劉江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散文隨筆集《書窗書影》《當梨子掛滿山崖》等,參撰《中國當代散文大系》《張中行名作欣賞》等著作。曾獲河北省第八屆文藝振興獎、第二屆中國報人散文獎等,作品被選入多部文集。
關于散文的文體特質
郝建國:師兄好!期待很久了,今天終于能有時間和您聊一聊散文的話題,聊聊散文的文體特質,亦即散文和小說等其他文體到底有什么區別。我以為小說以塑造人物為主,傳統理論叫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通過人物來表達情感、思想。散文的特質是情感,不管是抒情,還是寫景、敘事、憶舊、寫歷史,最終都要回歸人本身,而人本身核心的東西就是情感。
從中國散文發展的源流來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散文,其實都屬于政論文,不管是語錄體、論說體還是寓言體,主要還是為闡述政治觀點、政治主張、治國方略服務,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功利屬性,即使老子的“無為而治”也是很高明的治國思想。漢代散文上承先秦,比如,賈誼的作品有一股氣貫穿其中,文辭上比先秦的時候可能更鋪張,士大夫氣也更足了。到了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建安文學這一段,以曹操為代表的鄴下文人集團形成,他們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這與先秦散文作者的政治家、思想家身份截然不同。當然,古代沒有純粹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官員寫作,“三不朽”之一即是“立言”,曹丕說“蓋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作文看得很重。文人主體意識的確立大抵就是從建安開始,有了魏晉風度、名士風流,文人的個性和趣味就鮮明起來了。
古代文人給自己設定了兩條路,一條是廟堂,一條是江湖,進退有據。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當然文人的最大抱負不是著述,而是建功立業、出將入相,“立言”排在“立德”“立功”之后。譬如像李白這樣狂放不羈的詩人其實做夢都想當大官。
劉江濱:中國是個詩文大國,詩言志,文亦言志。這個“志”是情志,更多是指志向和抱負。宋代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載的也是大道,而非小道。
郝建國:即使小道,小情小調這些閑情逸致也多是官場失意后的產物,比如柳宗元寫《小石潭記》,即是被貶到永州后才有這種心境,在他顯赫的時候肯定不會有這情調。其實散文寫作很難脫離開現實的環境和人物的身份,作為一個純純粹粹的抒情言志的東西,我覺得難度相當大,當下其實也是。散文從文體上來認識的話,從古代一直延續到現代,思想性還是第一位的。
所以衡量一個散文家是不是散文大家,主要還得看他是不是個大思想家。
劉江濱:對。嚴格來說小說也是一樣,作家都應該是思想家,一部作品的靈魂就是思想,有思想才有高度、深度和寬度。所不同的是,小說需要借助故事情節及人物“自然而然”地傳達思想,而散文則可以直抒胸臆、自由表達。退一步說,即使沒有高深的思想,也應該有所發現、有獨到體悟。
郝建國:作為一名散文寫作的實踐者,對散文一定有著深入的思考。您認為散文寫得好或不好,評判標準是什么?剛才提到思想性是一個方面,其他的呢?
劉江濱:除了思想,主要是語言、文體、情感。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和小說比起來,散文對語言的要求更高。小說有情節和故事支撐,語言似乎是載體和工具,但對散文來說,語言就是第一審美對象,是通行證,語言不行一切免談。語言大體有華麗和樸素兩種風格,但最重要的是準確,“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這個“安”就是準確,準確了就安穩了,心安了,卯榫就能相對了。初寫散文的作者有個誤區,以為語言華麗就是美,所以大量使用形容詞,使勁鋪排詞采,極盡渲染。有句話叫“絢爛至極歸于平淡”,還有一句 “唯造平淡難”。真正的高手反而是平淡的、樸素的,像周作人、汪曾祺、孫犁等大家,語言都很平實,近乎白描,但最見功力。
郝建國:我特別喜歡趙樸初的文字,像枯樹一樣只剩枝干和筋骨,沒花也沒葉,只留根脈,特別有震撼力。再如魯迅的《祝福》,祥林嫂穿什么樣的衣服我們可能記不住,但她“眼珠間或一輪”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劉江濱:我贊成你說的散文的核心是情感的觀點。林非曾說散文要寫“真情實感”,今天看來好像是一個常識,但當時提出有它特定的歷史背景。散文曾經歷過偽飾、矯飾、虛假的階段,能我手寫我口,卻不能我手寫我心,所以“真情實感”論的提出非常有意義。散文的特質是情感,我們讀散文首先考察是否被打動了、被感染了。讀完一篇散文,在情感上沒有被觸動,沒有泛起波瀾,很難說是一篇好作品。托爾斯泰說:“藝術起源于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別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喚起這種感情,并用某種外在的形式表達出來。”托爾斯泰特別看重作品的感染力,他提出:“不但感染力是藝術的一個肯定無疑的標志,而且感染的程度也是衡量藝術價值的唯一標準。”在他看來,感染力的形成有三個條件:獨特、清晰和真摯。
郝建國:托爾斯泰這個感染力標準應該也適合于散文。
劉江濱:沒錯。但我還找到了另外一個標準。一次讀德國文化哲學家卡西爾的《人論》,看到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所有的人都模糊而朦朧地感到生活具有的無限的潛在的可能,它們默默地等待著被從蟄伏狀態中喚起而進入意識的明亮而強烈的光照之中。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強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藝術之優劣的尺度。”這段話明顯對“感染力標準”有一個否定,他強調的不是情感感染力,而是對意識的“強化和照亮”。這段話就像推開了一扇窗,令我豁然醒悟。有些東西在我們的意識中處于朦朧的模糊的蟄伏狀態,看了某個作品以后被喚醒、被照亮了,就像一束陽光打在你的頭上,朦朧的變明確,模糊的變清晰。我以為,這是古典美學和現代美學的一個重大區別,一個是情感的感染力標準,一個是意識的強化和照亮標準。
郝建國:卡西爾提出的這個是更高層面的要求。除了感動之外,還能對你的意識和人生有照亮,這就是經典的作用。照亮是能夠穿越時空的,過一百年這個東西依然有意義,不會時過境遷。
劉江濱:強化和照亮,既有情感的因素,也有思想的因素,更有強度和銳度,這是對大作家的要求。
關于虛構
郝建國:有關散文的虛構問題,多年來一直存在不同意見,有的觀點認為散文應該絕對的真實,不能虛構,虛構是散文和小說的分界線;有的認為文學是一種藝術創造,虛構和想象是文學的本質屬性,那么,作為文學的一種,散文自然擁有想象和虛構的屬性。您覺得該怎么理解這個問題。
劉江濱:《史記》里面有許多細節、對話都是作者虛構和想象出來的,作為一部史學著作都可以,那么作為文學的散文為什么不可以呢?所有的文學都是想象的產物,虛構是文學的一個基本要素,所以散文肯定不可能排斥虛構,不可能像新聞報道那樣完全忠實于事件本身。當然散文和小說的主要區別是,小說以虛構為主,散文以寫實為主,但可以適當的虛構、合理的虛構、局部的虛構。
比如說范仲淹寫《岳陽樓記》,之前他并沒有到過現場,但這并不影響他寫出千古名篇,這里依靠的是作者豐富的閱歷和大膽的想象。鐵凝有一篇散文《河之女》,文中的“我”是一個年輕畫家,并且特別標明男性身份,“胡子拉碴”,很顯然是虛構的。鐵凝并由此生發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散文河里沒規矩。當然,也不是全無規矩,而是在自由率性中存在著隱然的規矩。
郝建國:許多散文是對往事的回憶,十幾年、幾十年前的事情你還能記得那么清楚嗎?其中一些細節恐怕就需要依靠虛構和想象。
劉江濱:對。報告文學有一個原則叫“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同樣也適用于散文。作者寫的事不是編的,是真實發生的,但是局部可以虛構一下。有沒有這個動作,或者發生在哪個時候,在春天發生的挪到秋天行不行?當然可以。不改變它的基本真實,合理的虛構完全可以。文學的真實不是對生活的照搬,而是本質上的真實。另外,散文還涉及“書寫他人的倫理問題”,如果要真實地描寫生活中的矛盾、沖突甚至是陰暗、丑陋,這時必須要采取一些技巧,比如用假名,或者像美國散文家菲利普·羅帕特說的“虛構一個我來繼續我的寫作”。這個時候,如果堅持否認虛構,恐怕就難以寫下去了。
關于散文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郝建國:您寫散文,也搞散文批評,那么,您認為當下的散文寫作是什么樣態?
劉江濱:自20世紀90年代初韓小蕙宣告“太陽對著散文微笑”,散文寫作的確改變了新時期以來的沉寂狀態,一批批散文家登堂入室,創作了不少優秀作品。一個重要的現象是,一批年老的學者加入了散文寫作隊伍,如張中行、季羨林、金克木、舒蕪等,大手筆寫小文章,大大提升了散文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力度,審美之外又加審智的特點。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現,可以說是散文創作的一個高峰,帶動和影響了一大批散文寫作者。這之后,散文一直保持著穩定與繁榮的態勢,出現了不少優秀散文家和散文佳構,但坦率地講并沒有出現“現象級”的作家,稍顯平淡了點。
郝建國:您覺得散文寫作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劉江濱:就我有限的閱讀視野,管窺蠡測,姑妄言之,不見得準確。第一,散文陷入回憶的沼澤。孫犁說過,散文是老年人的文體。也有人說,青年的詩歌,中年的小說,老年的散文。為什么這樣說呢?可能就是散文特別適合老年人回憶,那種回眸憶舊的歲月滄桑感、命運感非有豐富的閱歷不可。巴金的《懷念蕭珊》、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楊絳的《干校六記》等,都是回憶類的佳作。回望人生,敘寫往事,的確是散文的長項,可以說沒有任何作家能夠拒絕或排斥回憶類散文。報告文學和散文一個有趣的區別就是,一個喜寫當下,一個擅寫從前。往事歷歷在目,坐在書桌前沉湎于舊日的時光,筆下文字即可流淌出來。然而面對當下的日常生活卻無從下筆,無從把握,好像必須經過沉淀、沉積、發酵,才能釀出酒來。回憶成為散文寫作的一大源頭,自然也無不可,也可以出佳作,但如果成為散文的主流審美特征,那么散文無疑會出現夕陽晚照、暮氣沉沉的景象。
周曉楓有一篇文章《散文的時態》,我以為對改變這種狀況大有裨益。我們知道,英語是分時態的,現在進行時、過去完成時、一般將來時等。中國語言對時間的表述好像沒有時態這一說,只有昨天、今天、明天、此時此刻等這樣籠統的表述。周曉楓指出,中國散文充滿了回憶的味道,寫作都是終點的回望,從時態上說,就是過去完成時。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以正在進行時寫作”。這不僅是手段,還是思維方式的改變。我以為周曉楓此文非常重要。
第二,歷史文化散文存在的弊端。如果從時間上分,散文有兩大類,一是現實題材,一是歷史題材。題材并無優劣高下之分,寫好就行。以我個人的經驗,歷史散文比現實散文難寫得多,必須事先做好案頭工作,收集閱讀大量書籍和資料,準備停當了才可以下筆。寫歷史散文要有做學問的功夫,要準確,不能失實,不能信口雌黃、張冠李戴。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資料的堆積,沒有把資料化開,用文學性的語言再現。
再一個問題是沒有觀點、沒有思想、炒冷飯,或者只停留在講歷史故事層面。如果只是史事重述,即使再生動,不打上自己的烙印,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就成了霍俊明說的“歷史解說詞”或者導游詞了。歷史散文的出路是要“故事新編”,有新發現,出新觀點、新成果。比如關于曹操,歷史舞臺上曹操都是白臉、奸臣的形象,包括《三國演義》都是崇劉抑曹的,但是,郭沫若寫曹操最成功之處是替曹操翻案,把曹操文學形象正面化。這是郭沫若將歷史研究成果做了文學化的表述。
郝建國:寫歷史總得跟現實有所勾連才好,也就是知古鑒今,有現實意義,還得出來點兒規律性的東西,對當代有所啟發。如果純講故事確實沒意思,你講故事不見得比史書講得更精彩,那還不如讀《史記》原文呢。
劉江濱:對,司馬遷是最會講歷史故事的人,最后有個“太史公曰”,那段話是最閃光的,觀點在那兒呢。沒有觀點,沒有思想,歷史散文就沒有魂魄。
第三,創新不足。1980年代文壇有個說法,叫“被創新這只狗追得連撒泡尿的工夫都沒有”,但現在這只狗似乎懶得追人了。人們一般比較看重作品的內容,看重作品寫了什么,但作品的形式,即怎么寫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決定形式,但形式的反作用也很強大,一個比較新鮮的“有意味的形式”,可以使內容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現。一般寫作者容易輕車熟路,習慣重復自己,其實也是在重復別人或前人。所以有志向的寫作者提倡“有難度的寫作”,追求“陌生化”。
余秋雨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創造了一種歷史文化散文的新文體,將游記散文和文化散文融合在一起,以前不曾有人這樣寫過。比如同樣是寫“魏晉風度”,余秋雨和魯迅就不一樣。魯迅更接近于研究,也是隨筆。余秋雨把戲劇性的東西融入散文寫作,比如,嵇康打鐵;比如,劉伶讓仆人拿把鐵锨隨時跟著,如果醉死了可以隨地埋葬,等等,具有很強的舞臺視覺感。魯迅是不會這樣寫的,余秋雨是把歷史予以戲劇化的情景再現。
成功的散文家差不多也都是文體家。如魯迅、周作人、張愛玲、孫犁、汪曾祺等人,他們的作品都有鮮明的標識度,從語言到形式,一進入文本就能知道作者是誰。
創新不足的原因,我認為,首先是缺乏創新意識,有藝術的惰性;其次是缺乏示范、借鑒或引領,這一點和詩歌、小說比起來差了不是一星半點。按魯迅說的“拿來主義”,詩歌與小說可“拿來”的西方作品和理論太多了,幾乎從每一個成功的詩人或小說家身后都可以看到“洋大師”的影子。而散文在西方是很弱的,通常對文學的分類是三分法,抒情文學、敘事文學和戲劇,或者是詩、小說、戲劇,散文常常被忽略。即使我們常提及的培根、蒙田、愛默生等幾位西方散文家,其實他們都是思想家、哲學家,和我們的孔孟老莊一樣,高山仰止,夠不著。再次,散文理論不夠雄健。我們不缺對具體的散文作品的評論,更希望有真知灼見、獨樹一幟的散文理論的引領。
關于散文寫作的核心
劉江濱:當下有許多作者熱衷于寫草木植物,被稱作生態散文,或者自然散文,我也寫過若干,但我發現不少作者陷入了一個誤區。
郝建國:我一直有個觀點,如果把樹單純寫成樹了,畫個貓就是貓,那就沒味道了。那個貓一定不是貓,就跟芭蕾舞劇《天鵝湖》似的,形象是天鵝,但音樂家要表現的肯定不是天鵝,要是真單寫天鵝那就沒勁了。所以要在生態里面包含象征意味,含蓄蘊藉。你寫的是樹,其實說的還是人的事。文學是人學,無論寫什么、寫到哪兒,九曲十八彎,最終總要歸到人。
劉江濱:一個作者給我看她的一篇散文,寫秋天西山紅葉。我一看挺好,文筆優美,觀察仔細,寫葉子紅了,還有深紅、淺紅,很有層次感,有油畫般的美感。但是缺點就是你剛才說的,純粹寫景,沒有寫到人。
郝建國:寫到人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虛頭巴腦、生拉硬拽,為了升華硬加上一個哲理的尾巴。其實在這點上類似于寓言,寓言是要求故事里蘊含道理的。我認真研究過先秦寓言,好的寓言應該是道理蘊含其中,讓人去體會,而不點破,因為所有的東西只要你說出來就窄了。人們對寓言的解讀可能是十種,但是作者說出來,就只剩一種了,反而限制了讀者的閱讀想象空間。散文大略也是這樣。
關于散文的“融合”
郝建國:您覺得散文的未來發展方向是什么?散文文體會有什么變化嗎?
劉江濱:關于散文的走向,我曾在1992年《西北軍事文學》4、5期合刊“散文專號”上發表過《散文走向略論》一文,面對剛剛興起的“散文熱”,我提出了四個走向:一是解放散文文體,走多樣化之路;二是建構深邃、雄渾的審美氣象;三是語言形式的“陌生化”向度;四是呼喚“思辨散文”。發表后《文藝報》做了摘登。二十年后,即2012年,中國散文學會編輯的《中國散文》又全文做了轉載。而今已經三十年了,其中一些觀點我認為還是沒有過時且具有現實意義。
當下提倡媒體“融合”,也就是不同介質的媒體形態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多樣化的樣態,有的甚至產生質變促生新的品種。這里說的是新聞,那么文學呢?會不會也走融合之路?其實,散文詩就是散文和詩融合產生的新的體裁樣式。我以為,解放散文文體,“融合”或許是一條可以嘗試探索的路徑。
關于“融合”,恩格斯說:“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相互過渡。”現實世界里有“非此即彼”截然分開的事情,更多的卻是“亦此亦彼”的狀態。文學亦如此。散文的融合,就是吸取其他體裁的藝術成分或營養,比如詩歌的意象和象征、小說的故事和情節、戲劇的對話和沖突、評論的邏輯和思辨,甚至是繪畫的色彩、電影的蒙太奇、雕塑的造型、音樂的旋律,等等。如果就是固執地堅持散文文體的純粹,堅持彼此之間的差異和對立,恐怕就會陷入僵滯和枯萎的局面,將會走向絕境。周曉楓說過一句值得反思的話,“當一個寫作者被稱為‘散文家,等于昭告天下:他既不會寫詩,也不會寫小說,無能得可憐”,而“小說家和詩人,都會寫散文”。事實也的確如此,許多散文寫得好的作家恰恰他們的身份標簽不是散文家,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將自身的藝術因子自覺不自覺地帶入散文中,使散文的肌體變得充盈壯碩。還有一個說法叫“跨界寫作”,沒人規定也不可能規定一個作家只能寫一種體裁。各個文體之間越來越呈開放敞開的姿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邊界趨于模糊,融合或為大勢。
郝建國:文體的界定,實際上是理論家的事情,作家不一定腦子里非得有什么框框,一切形式都服從于自由表達的需要。
劉江濱:沒錯。西方文學的三分法,敘事文學就包括敘事詩、散文和小說。從中國文學史來看,古代就只有兩種體裁,一個是詩,一個是文,因為二者區別得非常明顯,即有韻與非韻。非韻的一概稱為文章,呈大融合之狀。比如《史記》,我們通常把《史記》視作歷史著作,它是“二十四史”開山之作。但它還是文學著作,是小說,是散文,是戲劇,是傳記。所以魯迅評價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按說歷史是不能虛構和想象的,但《史記》中就存在,比如說《鴻門宴》中那么多細節、對話、表情都是虛構想象出來的,樊噲“嗔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正常來講,作者不在場是不能這么寫的。《史記》開創了融合的先河,如果那時有那么多文學理論的框框,司馬遷就不敢那么寫了,也就沒有了這部皇皇巨著。
還有,詞本是詩的一個變體,是詩和音樂融合的產物;戲劇是詩詞和舞臺、歌舞融合的產物;小說則是從神話、寓言、筆記、故事、傳奇以及話本等衍生而來。可以說沒有一種體裁是完全獨立自足的。許多新的藝術品種、藝術體裁的產生,都是打破了原有的文體界限,在融合中裂變而出的。所以魯迅說:“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這與金人王若虛所言的文章“定體則無,大體須有”意思吻合。
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我所說的“融合”是要打破文體之間的自我局囿,自我束縛,勇于創新,大膽試驗,而并非要消弭散文的文體屬性。
郝建國:我很認同您的觀點,讓我們一起進行有益的探索,一起期待當下散文創作新的驚喜!
編輯: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