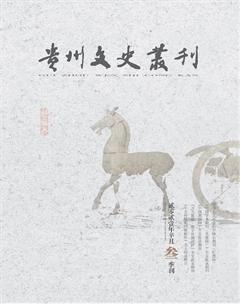南三閣《四庫全書》研究綜述
王婷
摘 要:綜觀南三閣《四庫全書》的研究歷程,涵蓋編纂補抄、庋藏利用、遷移保護、校勘補正等豐富內容。今從文獻保護的視角研究南三閣《四庫全書》,挖掘其在裝潢設計、建筑構建、管理流傳、文脈承繼等方面的保護實例,對完善書庫設計、促進四庫申遺、保護瀕危文化遺產等均有積極的實踐價值。
關鍵詞:庋藏研究 管理研究 毀圮復興 地域文化 文獻整理
清代江南乃形勝之地,人文淵藪。乾隆皇帝為實行文治,增藏《四庫全書》于南三閣,江蘇獨占其二。七部《四庫全書》,現僅存四部,文瀾閣《四庫全書》是南三閣全書中唯一幸存的一部。南三閣《四庫全書》的入藏與開放,在保存文獻典籍、推動藏書事業、發揚江南學術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然文匯閣、文宗閣毀于太平軍兵燹,文瀾閣棟宇半圮。今文瀾閣重建,其閣書幾經補鈔、輾轉遷移后重新影印出版;文宗閣已復建,并成功舉辦文宗閣暨《四庫全書》與鎮江學術研討會。前輩學人在南三閣《四庫全書》研究領域多所發闡,本文從文獻保護的視角切入,初步梳理南三閣《四庫全書》的整理研究概況。
一、庋藏研究
《四庫全書》曾經歷抽改禁毀、水火蟲霉、兵燹戰亂、怠職謀利等厄難,七閣藏書已去其三。其馀閣書能保藏至今,與其完善的裝潢設計、建筑功能、庋藏管理密不可分,且閣名意蘊里也飽含保護意義。
(一)裝潢設計
《四庫全書》卷帙浩博,采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配以四色裝潢,在裝潢設計方面頗具巧思。與《永樂大典》黃綾硬面“包背裝”稍有不同的是,《四庫全書》采用絹制軟面“包背裝”的裝訂形式,版心向外,憑紙捻加固書背,外裹絹面從而不露書腦,此舉于書中內容的保護較為有利。同時絹面材質高檔,體現皇家氣派;光滑綿軟,與內頁結合,較為伏貼;且翻閱觸感較佳,便于存放抽取。其中,南三閣《四庫全書》由江浙二省設局自購材料辦理,依木匣紙絹式樣照式裝潢并排架置庋。孫樹禮、孫峻《文瀾閣志》,李斗《揚州畫舫錄》等書目有相關記載1。陳東輝在辨證《四庫全書》絹面顏色方面有先期成果,其《〈四庫全書〉絹面顏色考辨》1依托文史論著中的記載,詳細比較諸閣《四庫全書》的絹面顏色。郭向東據絹面顏色、裝幀紙張、所蓋御印等方面比較北四閣與南三閣《四庫全書》的區別2。翟愛玲在《四庫全書》設計系統層面有所闡說,通過書籍裝幀設計、封面色彩設計等比較諸閣《四庫全書》的細微差異3。值得一提的是,南三閣本為一式三份抄寫,所用紙張、樣式及鈐印相同,浙江圖書館的童正倫《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別》4以浙圖所藏的《癸辛雜識》《詩經通義》等實物進行比勘,從封面顏色、樣式等方面來鑒別南三閣《四庫全書》。張群《〈四庫全書〉南三閣本封面考》5通過浙圖所藏《癸辛雜識》《荀子》《伊川易傳》等南三閣《四庫全書》零本比較,考證出封面絹色、絹質及題簽上存在差異。以上論斷為判斷南三閣各閣本提供有力依據。前輩學者從封面顏色、封面材質、開本大小、紙張品種、鈐印落款、書架函匣配備等裝潢設計方面,指出南三閣《四庫全書》與北四閣《四庫全書》存在一定差別,對紙張、鈐印、開本、函套、夾板等裝潢保護的具體功能未作過多延伸。
(二)閣名意蘊
南三閣《四庫全書》命名方式與“天一閣”的立意相仿,是基于“天一生水”命名基礎上的延續。其中文匯閣、文瀾閣皆從“水”旁,惟文宗閣無,乾隆皇帝《再題文宗閣》釋為“百川于此朝宗海”6,賦予其水之意,章采烈《文宗閣與乾隆御制詩》7提及這點。以文宗閣為例,徐蘇、裴偉、李金坤等學者在研究文宗閣《四庫全書》閣址、閣名方面有系列成果,徐蘇《文宗閣名議》《鎮江文溯閣溯源》8指出文宗閣興建與《四庫全書》無直接關系,“文宗”寓意乾隆皇帝對祖宗傳書的尊崇,此舉有利于文獻的繼承保護和中華文脈的傳承。裴偉《〈四庫全書〉·鎮江文宗閣》《“文宗、文匯”命名揣測——談乾隆敷行文治的潛臺詞》9指出文宗閣江水環繞的地理位置,“宗”有江南在內的各地文化歸宗一統意。李金坤《鎮江文宗閣建造之理由與閣名之意蘊脞說》《鎮江文宗閣名稱意蘊之脞說》10等論文肯定乾隆皇帝以水喻閣、文化懷柔的命名思想。還有學者有類似觀點,不再一一說明。以上學者在考證閣名意蘊方面,闡釋了文宗閣雖無“水”旁,但含“水”意,與文獻保護中“以水克火”的傳統保護理念相通。
(三)建筑功能
寧波天一閣設計精巧,在滿足基本藏書作用之馀能發揮有效的保護功能。南三閣建筑格局在外部裝潢與內部構造上,皆取法于范氏“天一閣”,并有所發展創新。于靜斯《明清時期我國公私藏書樓造景藝術探析》11,于嘉《清代皇家園林寫仿剖析——四庫七閣寫仿意象及復原研究》12,楊菁、于嘉、王笑石《“四庫七閣仿天一”所反映的清代皇家園林寫仿江南的三個階段》13等論文提及南三閣在建筑形制、外觀裝飾、環境布局等方面對天一閣的寫仿,其造景藝術手法,符合古典園林美學原理,同時還具備保護藏書樓的功能。范開宏、許雅玲、王作華、王靜、肖銀杉等從書閣選址、建筑規制、水源配置方面反映建造者強烈的防火意識,是實施藏書保護的有力舉措。1此外,陳曉華《論〈四庫全書〉的世界記憶遺產價值》2結合《四庫全書》刊刻、裝幀、典藏方面表現出的精湛工藝及建筑水平,揭示其蘊涵的“五行學說”“寓藏于修”等保護理念。徐瑩瑩《杭州文瀾閣建筑文化探析》3講述文瀾閣在建筑構建、形制變遷、內部典藏方面的獨到保護,突出“陰陽五行”的建筑觀。何宗美《〈四庫全書〉申遺芻想與研究前瞻》總結道:“從文化角度來說,這種皇家藏書樓的杰作從命名、結構、格局、色彩和環境等方面,鮮明突出了中國建筑文化和藏書文化的完美統一。”4將七閣建筑文化和藏書文化進行了糅合,充分肯定其文化遺產價值。
前輩學者充分挖掘了七閣建筑外在的實際保護功能及內里蘊含的傳統保護理念,然研究對象相對籠統,缺乏對南三閣相對集中的論述。
二、管理研究
(一)官方態度
在《四庫全書》編纂、庋藏、管理過程中,清廷官方的態度至關重要。如朱杰人《論乾隆在〈四庫全書〉編修、庋藏過程中的作用》5分析乾隆皇帝作為《四庫全書》編修工程的總策劃者和組織領導者,對《四庫全書》的保藏和利用所發揮的具體作用,重新審視其功過是非,肯定其珍視中華文化傳統的價值乃至動用國家力量予以保護傳承的功勞。戚福康、何峰、汪濤、吳建等學者將乾隆諭旨、乾隆南巡等作為研究對象,亦有類似觀點輸出。6
相宇劍《兩淮鹽政與〈四庫全書〉的編纂》7、劉敏《論清代兩淮鹽運使對文化的貢獻》8等文則從兩淮鹽政、兩淮鹽運使等官員角度,記載其負責書閣建造、日常運作、經費開支以及管理人員的選派等事項。張紀天《揚州文匯閣》9、張樹忠《四庫全書與揚州》10、張曉春《鎮江文宗閣的入藏書籍及日常管理的考證》11等文亦有涉及。兩淮鹽運使本是掌管鹽業大權、嚴察場灶戶丁、水利等事務的朝廷官員,受兩淮鹽政管轄監督,他們為保護《四庫全書》付出了很多心力,在資金、聘人等方面支持南三閣的管理運轉,功績值得肯定。以汪中為例,汪中曾受兩淮鹽政戴全德所聘,任鎮江文宗閣典書官,主持校勘《四庫全書》事宜,彭義《文宗閣〈四庫全書〉校勘史跡述略》12等文就汪中校勘文宗閣《四庫全書》事作資料鉤沉。在乾隆皇帝統領之下,兩淮鹽政等官員承擔閣書的入藏管理等事宜,他們的立場態度對南三閣《四庫全書》的精心裝制與妥當保藏起到重要作用。
(二)開放閱覽
南三閣的借閱制度相較北四閣更為開放寬容,《纂修四庫全書檔案》1保存了不少南三閣借閱管理的檔案。潘猛補《古代官方藏書流通之先河——文瀾閣借閱史實考》2、劉清《中國最早的圣諭公共圖書館——江南三閣〈四庫全書〉的續藏與管理》3、彭義《七閣〈〈四庫全書〉開放閱覽史跡考辨——并考文宗閣開放閱覽史實》4、徐蘇《南三閣的社會作用》5、李文昌《南三閣〈四庫全書〉與江南學術文化》6等論作強調南三閣的社會功用,述及南三閣在提供閱覽謄錄服務,加速文化傳播,推動藏書事業發展,促進江南學術文化繁榮上做出的重要貢獻。賀建、張田吉、石瑩等學者論作有一定相關性7。實踐證明,針對文獻的有效保護,不宜沿用束之高閣、秘不示人等舊法,化藏為用、傳播傳承才是文獻保存綿亙持久的良方。
三、毀圮復興
(一)毀損原因
盡管前期在裝制與保藏《四庫全書》方面花費了巨大心血,凸顯了對《四庫全書》保護的重視。然而,四庫文獻的毀損仍無可避免。黃愛平《〈四庫全書〉與四庫七閣的坎坷命運》8概述七閣《四庫全書》自成書至毀損的跌宕命運,其中南三閣《四庫全書》的毀損原因多樣,包括兵燹、散失、不當使用等。黃勛華、楊茜、章易、李理、程顯靜等學者有相近觀點9。在清晚期時局動蕩、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南三閣《四庫全書》難以獨善其身,其命運與國運興衰相連。南京圖書館藏莫友芝《上曾國藩書》,記載文匯閣、文宗閣及庫書被毀經過。趙昌智《揚州文匯閣典藏〈四庫全書〉被毀原因初探》10以莫友芝奉命訪查文匯閣劫后殘書為線索,將《兩淮鹽法志》作為文獻依據,對文匯閣典藏《四庫全書》被焚情況以及深層原因作初步探討。曾學文等有相似論述11。史革新、陳忠海等從“書厄觀”角度對南三閣《四庫全書》損毀事實進行了解析12。筆者以為,強大安穩的政治局勢、科學多樣的文獻保護方法是《四庫全書》免于損毀的重要保障。只有從政治、戰爭、人為、自然等方面深入剖析文獻毀損原因,才能更有針對性地對《四庫全書》實施妥善保管。
(二)護書壯舉
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四庫全書》毀于太平天國戰火,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亦遭重創,幸賴藏書家丁申、丁丙等人奮力搶救,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日后的恢復打下基礎。《文瀾閣志》1《浙江圖書館志》2等書目;林祖藻《江南三閣·文瀾獨存》3,裘樟松、葉軍《補抄歷史的人——記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幾代功臣》4,顧志興《浙江人對〈四庫全書〉的貢獻》5,劉瑛、昭質《抗戰期間保護中國文脈的仁人志士》6等論文綜合梳理了丁氏兄弟、譚鐘麟、錢恂、張宗祥、陳訓慈、竺可楨、毛春翔等浙江有志之士在搶救、補抄、遷移文瀾閣《四庫全書》過程中盡最大可能保全文瀾閣《四庫全書》的事跡。
對護書人加以專門研究者,如陳訓慈《丁氏興復文瀾閣書紀》《丁松生先生與浙江文獻》7等文記錄丁申、丁丙兄弟搶救、掇拾、資助、補抄、重建等護書事跡。張群、吳忠良、徐忠友、張凱、任彥馨等學者以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陳訓慈為研究對象,根據陳訓慈日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等史料來還原陳訓慈在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遷徙過程中的諸多艱難保護舉措8。浙江圖書館為紀念丁丙、陳訓慈,特編《丁松生先生百年紀念集》《陳訓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9,輯錄不少珍貴資料。陳學溶、何長鳳、楊斌等學者圍繞浙大校長竺可楨在西遷運力緊張時協助庫書遷移展開論述,包括對庫書入藏貴陽地母洞后進行曝曬、防潮等具體保護事宜10。劉亮《張宗祥與文瀾閣〈四庫全書〉》11、張晰《博學多才實難得,愛國之心更可貴——記著名學者張宗祥先生對傳承中華文化的杰出貢獻》12、朱煒《江南有完秩,補闕到文瀾——張宗祥與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半個世紀情》13等文以張宗祥先生為研究對象,著重闡述其組織文瀾閣《四庫全書》抄校補全及主持抗戰內遷等保護事跡。王火紅、王娟《嘉興人對〈四庫全書〉的貢獻》14,李菁、陳心蓉《嘉興學者與〈四庫全書〉淵源考略》15反映以張宗祥和張元濟等為代表的嘉興籍文人在《四庫全書》的保護、校補和研究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聶樹平《蔣復璁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節鈔——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入黔秘藏相關檔案摘記》16主記蔣復璁針對文瀾閣《四庫全書》由貴州省立圖書館代管所作出的指示、建議與協商,涉及曝曬去潮、設立保管員等具體事項。由此可知,藏書家、學者、官員等組成的保護者隊伍,在時局動蕩的緊要關頭,定制書箱搶運文瀾閣《四庫全書》,并綜合應用曝曬、通風、整修等一系列原生性保護舉措,殊為不易。
對庋藏地點加以研究者,如徐永明《文瀾閣〈四庫全書〉搬遷述略》1曾按時間先后敘述文瀾閣《四庫全書》搬遷十二次之地點,肯定一代圖書館人無私的家國情懷和敬業奉獻精神。抗日戰爭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曾經浙、閩、贛、湘、黔五省,后運至重慶青木關,最后運回杭州浙圖,毛春翔參與整個遷移過程,其《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2具有較真實的文獻史料價值。呂洪年、鮑志華、孟國祥等有相關論述3。此外也有圍繞某一具體地點展開者,如趙春華《護衛國寶 青史永記——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時初遷富陽漁山記述》4,趙曉強、鐘海珍《貴陽地母洞與〈四庫全書〉》5,李海默、肖瀾《小記文瀾閣四庫全書典藏史上的一件事》6等文擇取富陽漁山、地母洞、青白山居等頗具代表性的遷移庋藏地點,細致記錄護書史實。
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過程中,貴州省立圖書館曾給予大力支持。袁媛、劉勁松《抗戰時期貴州省立圖書館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考察》7,袁媛《抗日戰爭時期貴州省立圖書館研究》8,楊斌《抗戰時期浙江省文瀾閣四庫全書內遷史料》(上)(下)9,趙曉強《抗戰期間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遷黔史料輯錄(補)》10,雷有梅《探尋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前世今生——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貴州之行》11,李柳情《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內遷史料述略》12等論作注重運用檔案史料,從曝曬防潮、庫書管理、加強保衛、改進庋藏、遷移轉置等方面闡釋對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及時有效保護,突出貴州省立圖書館為保存庫書、促進文化傳播所作出的貢獻。羅應梅、黃凱《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遷黔軼事》13記述貴州知識分子傳抄與西南相關的文獻珍本事宜,此舉屬于文獻的利用保護范疇,既豐富了貴州的文化典藏,也有利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延續傳承。此外,呂洪年《文瀾閣庫書抗日大轉移》14,鄭文豐《一場鮮為人知的“文化保衛戰”》15,蔣肖斌《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秘藏貴陽》16等報刊文章真實記載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秘藏貴州期間的相關文件、電文、信件、經費支出及各種憑據。
上述內容從護書者群體、護書者個案、護書地區角度考證南三閣《四庫全書》在戰亂時期較為完好保存的原因,其中不少內容自檔案中輯出,較珍貴可信。
(三)復修復建
復修復建主要包括兩方面:其一,修復內容層面,主要指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內容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曾歷太平軍戰劫,閣圮書散,后經丁氏兄弟“光緒補抄”、錢恂“乙卯補抄”、張宗祥“癸亥補抄”三次補抄才勉復原觀,且補抄所據底本,很多優于《四庫全書》原本的底本,賦予了庫書獨特的文獻價值。張宗祥曾考論補抄史實1。崔富章關注補抄本的底本著錄,并實例舉證有些補抄本的價值勝于原抄本,有《四庫提要補正》2等系列成果。趙冰心、裘樟松《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鈔本之價值》3,顧志興《風雨滄桑話文瀾——細說文瀾閣〈四庫全書〉之一》《文瀾閣〈四庫全書〉的三次補抄》4,童正倫《丁氏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述評》5,吳育良《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補鈔及價值》6,陳東輝《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及其他》7等文從補抄階段、補抄人、補抄價值幾個角度全方位剖析,在填補缺漏的庫書內容基礎上,實現內容質量的提升,可視作內容層面的有效修復與保護。
其二,修復載體層面,包括修復書閣、復建書閣、重置裝具以及修復閣書。南京圖書館藏有清抄本《修繕揚州文匯閣工料函牘》一卷,反映文匯閣屋脊漏雨、卍字河無水實情,是記載修繕文匯閣的重要史料8。《揚州將復建“文匯閣”》9,梁寶富《揚州文匯閣復原路徑與價值研究》10,趙國平《揚州文匯閣何日君再來》11等報刊文章述及文匯閣從修繕到倡導復建的過程。不論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修繕文匯閣,還是當今時人對文匯閣復建的倡議,都旨在通過對文匯閣外在載體形式的恢復,延續《四庫全書》的文化影響。
文宗閣被毀后,有識之士呼吁復建之聲不絕。鎮江吳寄塵以恢復文宗閣為己任,興建“邵宗國學藏書樓”,魏志文《從文宗閣到紹宗樓》12等論文述及此。2011年10月26日文宗閣圓滿復建,《文宗閣暨〈四庫全書〉與鎮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3里收錄徐平、邵孟大、王亞南、郭祥明、李金坤等復建綜述。文宗閣的復建是鎮江歷史文化形態的再現,對于四庫文化的保護、江南文脈的賡續有著深遠意義。
《文瀾閣志》收錄《修建文瀾閣布政使照會》,鄒在寅《重建文瀾閣紀事》等文,保留了重建文瀾閣的文獻資料14。顧志興亦費相當篇幅記錄此事15。梅叢笑《文瀾閣相關史實考證》16就文瀾閣的相關史料及實物材料進行收集,從文瀾閣的歷史沿革、建筑平面變遷、建筑名稱演變以及維修細節四方面進行考證,力求為文瀾閣修繕和恢復提供可靠的歷史依據。此外,乾隆年間配置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格架書匣等,毀于清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戰火。光緒二十年(1894)清政府出資,“分別部居如舊,惟易架為櫥”“惟撙節經費,易楠木匣為銀杏夾板,改絹面為紙”1。可見即便經費受限,仍注重對《四庫全書》物質載體的保護投入。后修繕青白山居時,又制作了樟木書箱用于存放閣書,并放置防潮紙、樟腦丸等物,達到防潮、避蠹等保護目的。
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注重對破損閣書的修復保護:“雖然主事者曾派人清查,標明待修之本,但限于經費而未能實行。1933年,經過陳訓慈努力,浙江省教育廳撥給專項經費用于修補閣書,于是陳訓慈聘請李炳煒專門負責古籍裝訂修補,選擇破損之書換面重裝,務求整齊。”2在陳訓慈日記中也有相關記載。王曉紅《〈四庫全書〉破損檔案:貴州省圖書館修舊如舊》3針對貴州省立圖書館建立的代管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出現的紙張老化、掉渣、蟲蛀、粘連、鼠嚙等破損狀況,遵循“整舊如舊”的修復原則,主要采用托、裱二法,妥善科學地修復好二百七十三頁珍貴檔案。此種修復方式多以傳統手工修復為主,可視作對四庫檔案史料的原生性保護。
四、綜合研究
(一)編纂研究
目前所見,國外針對南三閣《四庫全書》的專門研究相對較少,典型的有美籍學者蓋博堅(R.Kent Guy)的《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4,將《四庫全書》的纂修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在“學者的回應”“圖書采集和審查”等方面闡述江浙學者、士紳和商人對《四庫全書》編纂的支持。國內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5、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6、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7、江慶柏《〈四庫全書薈要〉研究》8、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9、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10、劉鳳強《四庫全書館發微》11等著作對《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纂修機構及保護措施做了全面研究,然對《四庫全書》保護層面的具體內容涉及較少。
(二)書閣歷史
吳嶺梅《文匯閣與〈四庫全書〉》12,韋明鏵《心祭揚州文匯閣》13,肖夢龍《鎮江金山寺文宗閣藏〈四庫全書〉始末》14,徐蘇《鎮江文宗閣溯源》15,張崟《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16,何槐昌、鄭麗軍《一部具有特色的〈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1等論文對南三閣《四庫全書》今昔歷史進行了考稽介紹,并考證江浙文人為傳承文脈所做的貢獻。此外,陳曉華、付寶新、陳學平、王忠偉等學者從文化史角度解析南三閣《四庫全書》在緊密結合書閣歷史、加強民族文化認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作用2。《四庫全書》作為我國的文化遺產,具備物質性和精神性雙重性質,上述說法與文獻保護中的精神性保護較為契合,是讓文獻活起來、提升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徑。
(三)地域文化
南三閣《四庫全書》自成書始,便與揚州、鎮江、杭州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衍生出鮮明的地域文化。以揚州而言,文匯閣及所藏《四庫全書》被太平軍付之一炬,成為揚州文化之痛史。今揚州市委、市政府將揚州國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策劃制作、商務印書館出版、揚州恒通集團捐贈的原大、原色、原樣仿制版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天寧寺萬佛樓,是對歷史負責、對后世負責的文化保護體現。《再生式保護〈四庫全書〉功在千秋——〈四庫全書〉(文津閣本)原大原色原樣出版專家審評會專家訪談》3、《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原大原色原樣出版——專家寄語:文宗文匯,雙閣同輝》4、《天寧別館書樓聳 文昌永古煥重甍——原大原色原樣版《四庫全書》(文津閣本)入藏天寧寺萬佛樓紀實》5、王春江《〈四庫全書〉與藏書閣》6等報刊文章記錄《四庫全書》影印及入藏揚州天寧寺的盛事。上述影印本是借助古籍數字化手段,實現了對《四庫全書》的再生性保護。以鎮江而言,不僅實現了從興建邵宗樓到復建文宗閣的歷史跨越,還有徐蘇所編《文宗書韻:文宗閣與四庫全書》與《文宗閣》7兩部研究普及性著作,對保護文宗閣暨《四庫全書》的人、事等記載翔實,涉及文宗閣與《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與鎮江城等內容,有利于四庫文化的長久保護傳承。以杭州而言,2004年杭州出版社與浙江省圖書館簽署整理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協議,2014年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出版,最大程度地還原了庫書內容,實現了庫書的再生性保護,也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得以繼承的重要保障。陳東輝將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加以影印出版,為學者研究、利用提供極大便利,同時也進一步推廣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獨特價值,在內容保護層面實現更加細致的保護8。顧志興在研究浙江藏書史、浙江文化等方面卓有建樹,其中《文瀾閣四庫全書史》是在其所著《文瀾閣與四庫全書》基礎上修訂增補的新研究成果,介紹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編修、入藏、重鐫、建閣、補鈔、遷移、出版等內容,全面覆蓋了載體與內容層面的保護舉措9。此外,王火紅從歷史、文獻、文化三個維度探討《四庫全書》與嘉興地區的關系,對陳其泰、張元濟、蔣復璁等嘉興人護書舉措多有挖掘10。上述舉措是《四庫全書》的再生性保護和精神性保護的綜合體現,同時因地域的不同而煥發出別樣的文化特色。
(四)文獻整理
與南三閣《四庫全書》有關的文獻散見于各類古籍記載及各大圖書館中,需要進行專門的文獻整理。江慶柏《揚州文匯閣文獻錄》1依照文匯閣《四庫全書》的入藏、規制、管理、讀書、修繕、毀壞、改良等方向輯錄文獻,其中不乏南京圖書館藏《修繕揚州文匯閣工料函牘》等稀見文獻。孫葉鋒《〈揚州文庫〉收錄稿鈔本稀見文獻舉隅》2中亦有說明。唐宸、黃漢《臺灣藏文匯閣〈四庫全書〉目錄抄本考》3注意到臺灣所藏清抄本《文匯閣〈四庫全書〉目錄》是反映文匯閣《四庫全書》面貌變遷的重要史料,同時《文匯閣目錄》所記載的庫書辦理細節,對探討文匯閣與文宗閣關系等亦提供諸多線索,可與王菡《〈文宗閣四庫全書裝函清冊〉說略》4,琚小飛、王昱淇《嘉慶朝文宗閣〈四庫全書〉裝函清冊考》5相參看。薛冰先生收藏有江世榮作于1953年的《文宗閣小史》6手稿本六章,他處未見,征引書籍文獻達二十馀種,是研究文宗閣《四庫全書》的珍貴資料。此外,前文記述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入黔時,趙曉強、楊斌等學者在檔案史料整理方面出力甚多,不再贅述。綜上,通過規范的古籍整理,利用圖書館等文博單位所藏稀見文獻及檔案,可為南三閣《四庫全書》的保護研究提供原始珍貴的史料支撐。
目前學術界關于南三閣《四庫全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編纂、庋藏、管理、補正等方面,成果豐碩,成就矚目。然對文獻保護角度的研究多為個案舉證,如“整舊如舊”保護原則、“原生性與再生性”保護舉措、“化藏為用”保護理念等的零星列舉,缺乏系統性。南三閣《四庫全書》在制作、收藏、利用、修復等保護過程中表現出很強的區域性特征,其精湛設計、科學管理、護書理念及文化內涵等方面,尚有不少待挖掘空間。
責任編輯: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