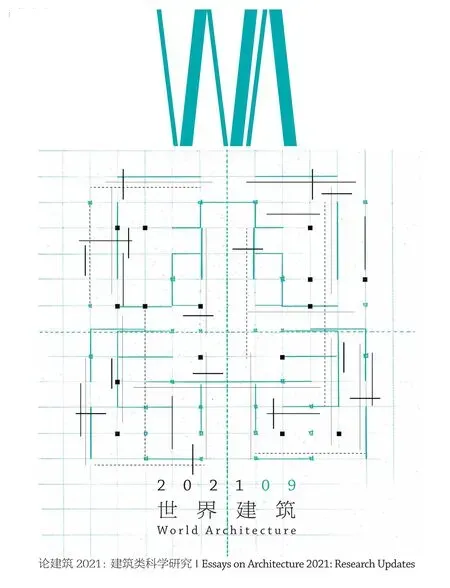主體回歸與虛空策略
——第八屆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作品“重現”的形式邏輯及內在追尋
張長文,宋聚生,胡潤澤/ZHANG Changwen,SONG Jusheng,HU Runze
0 引言
自2005 年至2019 年,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共舉辦了八屆。本界展覽在深圳中心區設立主展館,主題為“城市交互”;在深圳大鵬所城設立分展館,主題為“時間之海”。大鵬所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距今已有600 余年歷史,是明清兩代中國海防的軍事要塞,曾多次抵御了葡萄牙、英國殖民者和倭寇的入侵,有“沿海所城、大鵬為最”之稱,深圳的別稱“鵬城”即源于此。2001 年,大鵬所城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次分展館展覽在海邊歷史悠久的大鵬所城里展開,為時間之海的命題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延續性。我們選擇了古城東北角的城墻遺址廣場,參展的作品命名為“重現”,試圖以時間為刀筆,來表達重現歷史、重現時光、重現一座“古城”的意味。展覽自2019 年12 月下旬開始至2020 年5 月上旬結束。
1 環境認知與設計策略
重現作品位于大鵬所城的東北角,選擇這樣的位置是因為在設計之前做過考察,發現在諸多預設展場中,東北角展場的城墻是古城中唯一古代遺跡的存留,其他部分的城墻已然拆除,其他的展場建筑如南門樓則是新建復原。
1.1 時代背景與主客逆轉
過去,所城是海防體系,城墻更是防御的主體。而今,城的概念已很多元,城墻不再是防御的邊界,而成為心理的邊界、地價的邊界、身份認知的邊界、戶籍管理的邊界。東北角的城墻遺址,給予我們很大的啟迪,他就是最好的“作者”,將和我們一起創作。時間之海的主題,需要歷史的縱深才能得以更好的展現,600 多年的殘垣斷壁可以作為歷史那一端的真實載體,與現代作品的詮釋者溝通交流,從而在場所中挖掘出最為深邃的歷史時光。東北角的廣場是狹窄逼仄的古城中難得的一塊開敞空地,如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言,得以展示大地是住居的載體[1]。從而可以詩意地棲居,作品也可以詩意地佇立。
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論述了消費社會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即消費控制了當代人的全部生活,消費主體在消費結構中被控制和盤剝的問題[2]。他描述了大眾、信息、媒體、商品等客體無限增殖,最終逃脫了主體的控制,實現了主客體之間的角色逆轉[3]。他的理論充分反映在當代藝術作品之中,科幻電影《黑客帝國》系列表現的就有他所描述的景象。城市是生活的主體,聚集與交易注定導致喧囂。深圳隨著經濟發展、資本擴張也形成了消費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大鵬所城受大勢影響也變得商業化氣息濃厚,原住民為了盈利而努力促進消費,游客則為了別人的關注而消費古城。人們紛紛來此打卡拍照上傳,然后活在他人的點贊之中,變為大眾希望的模樣(圖1)。這種現狀充分體現了現今社會中比商品實際的使用價值更重要的是它的華麗外觀和展示性景觀存在的趨勢[4]。

1 大鵬所城十字街(攝影:吳漢廷)
1.2 場所精神與虛空策略
相比防御的古城,我們要重現的“城”會是何種意象?顯然,他絕不該是一個絕對封閉的樣貌,他所創造的邊界應該不同。相對喧囂的景區,我們要重現的該是怎樣的場景?是生活的熱鬧場地還是喧囂中的靜謐之所?在此我們非常認可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在《思考建筑》中的表達:建筑有一種優美的靜謐,使我聯想到諸如沉著、自信、耐久、風度、正直,還有溫暖與美感等本質;一個建筑正在成為它自己,成為一個建筑藝術,而不是扮演任何東西,只是它自己[5]。
場所給我們的提示,即虛空策略。我們試圖創造一個內向性的沉靜空間,通過留空的方式去營造靜謐,讓其建立與自然萬物之間的聯系。正如安藤忠雄評述直島當代美術館時所說:利用空白釋放內省的體驗,從而觸發觀者內心的感悟。虛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容納參觀者內心的擁塞使其可以倒空心靈,一方面可以映射參觀者內心尚未被消費文化徹底擠占的那份空白。有利于參觀者重新思考自身是否應該被客體所占有,有助于參觀者思考自身主體的回歸。空白(emptiness)、或者虛空(voided void)變成了內心寂靜的反應,從而體驗幸福的感受并投射事物之美[6]。我們試圖創造一個作品,他并不是表演的舞臺,而是一處靜思空間;他未必有很多人來參觀,但看到的人都有收獲。以沙粒、木材、布質、紅土來塑造,再以新建的部分與城墻遺址共同圍和,形成作品的整體(圖2)。參觀者經由城墻遺址及木構之間的通道走入作品,盡頭左轉便看到紅土擋墻,作品新建部分的入口便在此處。由此通過一系列連續不斷回旋的廊子,步入一個內向虛空的中庭空間。中庭的圍合界面敷以紅土,增強了向內封閉的體驗,這種封閉隔絕了內外,從而使人漸漸沉靜下來,感悟自然給予的那種樸素而本質的能量。也在虛空中喚醒內心、體會寧靜、反思生活,從而擺脫客體的控制、關照真正的自我、實現主體的回歸。

2 作品整體呈現(攝影:上-胡潤澤,下-上啟藝術)
2 概念演進與邏輯建構
確定策略之后,開始著手概念的演進以及建構的選擇。形式邏輯的建構,材料、色彩的選擇,構造做法的確立都將決定作品成立與否。
2.1 色彩能量與土地倫理
人類接觸光色而影響視覺與心情,并不是單一的只是視覺感官所產生的反射現象,更是能夠感受為生活創造生機與活力的能量。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建筑或景觀設計因為受限于不一樣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及生活習慣,所以會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人文與色彩互動的表達,例如,在西方代表危險、狂熱的紅色在中國則是喜慶與活力的象征。
在英語世界,有時同一顏色也代表著截然相反的含義,“藍領”代表普通民眾,“藍血”則代表貴族。當然,在法國現代主義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眼里藍色更為獨特(圖3)。他認為藍色本身象征著天空和海洋,象征著沒有界限:“什么是藍色,它是從可見的轉變成不可見;這種藍色,消除了地平線的分界,喚起了天地的統一”[7]。同時,他也承認虛空的觀點,用他的思維方式理解,這并不只是真空或者空白,而是代表了一種開放和包裹的狀態,一種看不見的能量場。此外,虛空滲透著一種基本元素,空氣或者精神,它是能量的媒介[7]。

3 克萊茵作品:單一性(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5])
受克萊茵的啟迪,我們也在尋求一種色彩,既有能量的蘊含又有虛空的屬性。美國著名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在其被譽為“綠色圣經”的《沙鄉年鑒》中提出土地倫理的概念,將一切人類生命和非人類生命整合在一起,構成整個生命共同體。利奧波德對人類的絕對權威性提出質疑,同時賦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以價值。土地倫理觀提醒我們需要跳出土地征服者的思維,徹底思考土地帶給生命的意義。土地給予我們能量,土地給予我們生命。在人類與土地情感關系疏離,在人性被金錢所異化的時代,發掘大地這一生長環境對人性形成與發展的根性作用,就成為我們思考的重心,于是我們選定土質及其代表的褐色作為作品的基調(圖4)。

4 材質色彩選擇(攝影:胡潤澤)
2.2 材質選擇與工藝表達
色彩并非獨立存在,也和材質息息相關。以褐色系作為色彩基調,選擇了紅土、木材、織物、沙粒等幾種材質。
當地的紅土是第一選擇,大鵬所城城墻的構筑材料就是如此。將城墻上日久經年被雨水沖刷下來的紅土,轉譯為作品的素材,更能表現“重現”的意味。同時也以散落的紅土進行立體重鑄,表達作品是由土地中生長而出的概念,籍此探索作品的初衷及建筑的本源。在西班牙語里,木質(madera)、材質(materia)、母親(madre)幾個詞非常相似[5]。在中國,木質更是古典建筑之母,沒有木材幾乎就沒有中國古典建筑這一文化體系的傳承;也就沒有了《詩經》中“如鳥斯革、如翚斯飛”贊頌像羽翼一樣舒展的屋頂和出檐[8]。同時,木質的構想也來源于場地邊存在已久的傳統木構亭子,我們將它轉換為當代木構形式,來回應場地所蘊含的信息以及遵循自然傳統的構建法則,由此與歷史交融、并感悟時間的存在。織物的選擇來源與場地上原有的遮陽網,由于其輕,依風舞動,久久不息。以當代快速生產的輕質織物作為媒介,來捕捉空氣流動的韻律、自然投射的光影,感悟時間在空間中的延續(圖5)。沙質的選擇是與海邊之城的映襯。重現之城座落于沙中,猶如所城佇立于海濱。沙是作品的序言,同時又如沙漏一般過濾著時間(圖6)。

5 場地原有木亭及織物

6 大鵬所城的海濱(5.6攝影:吳漢廷)
材料與工藝密不可分,由傳統的榫卯及銷釘工藝來呈現時間延展及文化傳承便是不二之選(圖7)。然而傳統工匠的缺失卻成為工藝構想的最大敵人,面對建筑傳統的喪失真的是痛心疾首。經過艱難的找尋,終于在大鵬所城周邊小鎮找到了擅長榫卯工藝的工匠,時間與工費的付出都遠超預算。但也正如此,才能體現在市場上充斥著快餐制作之時,真正的手工藝工匠是多么的難能可貴!研究日本伊勢神宮的“造替”制度可以發現,為了讓打造神宮的木工、刀工、漆工、織工等工匠技術能世代傳承,設定了每隔20 年一次的造替,使每一位工匠在有生之年至少有兩次機會可以磨練技巧,防止傳統工藝消失(圖8)。這種保留傳統工藝的思維與做法確實值得我們借鑒。

7 展覽作品節點工藝圖紙(繪制:胡潤澤)

8 伊勢神宮造替制度的相鄰場地(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6])
3 場景設定與空間塑造
材料及色彩確定之后,作品的氛圍營造及形式的邏輯建構就非常重要了。在此著重進行設計手法的深入探索及工藝材料的系統組合。
3.1 內外反轉的形式邏輯建構
作品的概念是重現一座“城”,而完全不需要防御功能的“城墻”該是何種呈現?我們的邏輯構建是將“城外”——也就是作品對外——的界面設計得柔和甚至通透;以織物包裹于木構之外,看似封閉實則通風、透光,甚至施加一點力量就可以穿過。而在內側,則用織物浸染紅土泥漿,風干后形成堅硬的土質界面,強化內部空間的封閉,從而加深內部中庭的靜謐之感。觀者可以在這份靜謐之中暫時忘卻古城商品社會的喧囂,反思在消費社會之中的迷失,感悟寧靜帶給自身的力量,喚醒被客體左右的自我。這種內外反轉意象的處理手法借鑒了馬巖松進行巴黎蒙帕納斯大廈的改造設計“都市蜃樓”。蒙帕納斯大廈建成時代表著那個時代的驕傲和成就,而今卻與巴黎城市環境格格不入(圖9)。馬巖松利用光學原理,使得整個大樓成為一個凹面鏡,將城市及建筑通過反射倒掛在空中,形成都市里的蜃樓(圖10)。其做法表達了一種觀念,雖然不能讓這座大樓和它所帶來的歷史遺憾徹底消失,但應該建立一個新的審視角度,思考人類該如何與我們的內心以及周邊的環境相處。我們也無法改變大鵬所城在城市發展中的資本化、商業化的趨勢,但我們希望通過作品內外反轉的意向,來探討在繁華的商品社會中,人們如何與其內心以及自然相處。

9 蒙帕納斯大廈現狀

10 蒙帕納斯改造方案(9.10圖片來源:http://www.i-mad.com/)
3.2 流動回環的空間形體塑造
展品設計與建筑設計不同,如何以建筑師的背景做藝術家的思考也是我們深入探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認為藝術家現象是迄今為止最透明的[9]。其“最透明”之意是指本質上最能夠為人們所理解,能夠把某樣尚未進入其存在的東西自行建立,讓他呈現他自己。蘇聯至上主義(Suprematism)的奠基人卡西米爾·馬列維奇(Kasimier Marevich)便是一位“最透明”的藝術家。其作品“白上之白”脫離了文藝復興時期所發展的具象的美學要素,拋棄了由它們所支撐的美學價值,進而創造了以抽象的幾何形態及簡素的色彩構成來表達其思想觀念的方法(圖11)。馬列維奇希望作品中的正方形看起來是漂浮的、透明的,傳遞著寧靜和永恒。同時作品也沒有被其畫幅本身的邊界所圈囿,而是產生了一種沒有限制肆意生長的可能性。他曾說我已經克服了彩色天空的襯托……在白色的深淵中游泳,而無限就在你面前。

11 馬列維奇作品:白上之白(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7])
我們的作品在設計思想及平面構成上充分借鑒了馬列維奇的白上之白,而在空間構成上受到西班牙藝術家豪爾赫·奧泰扎(Jorge Oteiza)的影響。為了表達向馬列維奇的致敬,奧泰扎將“白上之白”的方形作為一個單元延伸到了空間的創作之中[10],產生了若干個多面體鋼板界定的不同狀態的空間。在他最終形態的雕塑中,能清晰地看到由一系列不同收放程度的鋼板所界定的虛空,來闡述沉靜層級的不同(圖12)。在解釋其創作理念之時,他表達“恒星與星系之間、原子核與電子之間的空間似乎都是空的,而后一個空間被非常強大的電磁場所占據,該電磁場將粒子保持在一起而不會發生碰撞。”空的狀態中蘊含能量,而這種能量又維持著秩序。

12 奧泰扎作品:空盒子系列(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8])
作為建筑師,在強調作品與自然對話的同時,我們也進行了空間感與立體結構元素在作品中的充分運用。首先設計的是正方體的套疊,運用小角度的扭轉來呼應場地的銳角(圖13)。以木構織物體系與城墻之間狹小的空隙作為參觀入口,由此進入回旋的廊道。然后在廊道中通過正方體在三維方向上輕微的扭轉,形成復雜的收縮及開放。本來狹小的廊道因收窄變得更加局促,卻可增進觀者的流動。這種流動,與其是主動的進入,更希望是內部空間能量的抽吸。不只進入,從中庭走出的路徑也由收分與擴張形成,從而使觀者可以停駐與前行。我們希望外部場地與內部中庭能夠通過其不同的場所蘊含,促使內部空間的“虛空”與外部空間的“實有”聯系,從而形成一種靜止與交流的復合狀態(圖14)。

13 夜景中呈現的作品總平面(攝影:上啟藝術)

14 作品進入路徑與內部中庭的實景照片(攝影:胡潤澤)
4 空間蛻變與時間永恒
大鵬展覽以“時間之海”為主題,就是試圖探討藝術與時間的關系。對于建筑師創作展覽作品,更是著重探討空間與時間的關系。在設計之中,沒有時間的空間片段也就失去意義,所以研究空間與時間的共同呈現便尤為重要。
4.1 光影捕捉與光陰呈現
自然的法則使得宇宙在大爆炸開始便一直走向未來而不能回頭,星系運行使得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產生每日時間的周而復始。時間的兩個特性展示無疑,一曰永恒,一為韻律。陽光在作品上的投射形成的陰影變化,恰恰記錄了這種時光的周期。建筑學專業出身的西班牙雕塑大師愛德華多·奇利達(Eduardo Chillida)對材料、光影的處理具有獨到之處,他癡迷于希臘、羅馬和普羅旺斯等地古遺址中細密卻具有半透光性的材料呈現的光影,從而以蠟石作為雕塑的材料。密實的石材會造成陰影,半透明性又導致光的滲漏,兩者的交融使得雕塑呈現的狀態極其豐富(圖15)。我們借鑒這種處理手法,也以作品為光的容器,以光影的捕捉來表現時光的流動。我們以紅土的界面模擬密實感,以織物的界面模擬半透明性,以此在作品的內外界面呈現不同的光影狀態。每天日升日落,陽光在作品上的投影逐漸移動且變化深淺,記錄了時間的刻度與向度,記載了周期與韻律(圖16),從而達到夜晚時作品的呈現(圖17)。

15 奇利達作品:深如空氣系列(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9])

16 作品不同時段光影變化的模擬(繪制:胡潤澤)

17 作品夜景(攝影:上啟藝術)
在古希臘,光線被視為知識、藝術以及理智的象征。通過奇利達的提達雅山紀念館可以感受到光線帶來的天啟一般的智慧(圖18)。13 世紀但丁(Dante Alighieri)也說神光貫穿宇宙的情形依其神性而定。我們通過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這種“神性”(圖19)。光線帶來的不只是空間的形式拓撲,更是基督教的神靈、受難、教義與虔誠。安藤以光為工具雕刻建筑,讓人看到光的十字,體會宗教的本質,而空間的形狀漸漸消隱。光是銳利的,他的投射塑造了空間;光是隨型的,光影的呈現弱化了空間;光也是無形的,隱匿了自己也便消失了空間。

18 奇利達作品:提達雅山紀念館(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9])

19 安藤忠雄作品:光之教堂(圖片來源:參考文獻[20])
4.2 自我映射與主體回歸
德國哲學家瓦爾特·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書中指出,由于攝影術的發明,顛覆了古典繪畫中寫實主義傳統所依據的知識鏡像論,畫出現實圖畫已然成為過時之舉[11]。繪畫不再享有復制的專利,標志著寫實藝術的沒落。所以印象派畫家所要表現的不再是客觀的“像”,而是其心中所見,如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的《日出》(Impression Sunrise)、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星空》(The Starry Night)。我們在設計之時,也是試圖創造一個作品,來體現我們對藝術的虔信,表達我們對建筑的真誠。希望它具有經驗性(empirical),可以用我們身體五官體驗感知,能夠被語言描述,也可以被直覺掌控。希望它能具有超驗性(transcendent),超越概念思維的范疇,無法用言語訴說,不能用思想把握。同時,也希望它能具有內省性(introspection),批判現今世俗的表象,觸動心底的麻木,喚醒沉睡的自我,將心中的本原意象映射到作品之中。
我們在作品中給予觀者兩個引導,第一個是與自然交融。作品在水平界面上設計了不同程度的收分,而在縱向方向上給與了絕對的釋放。這樣可以讓虛空得以與天地回應,讓觀者以更加開放的狀態去面向自然。停留在中庭里的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到古城墻上生長出來的形態,可以看到場地原有木亭的坡頂、廣場中許愿樹的樹梢、遠處蜿蜒的山脈、天空中漂浮的云朵,也可遠望向浩瀚的宇宙。另一個引導是與內心的交流,我們與參觀者做過互動實驗,讓他們在中庭內閉上眼睛,幾分鐘以后,觀者反饋他們聽到了觀看展品時沒有在意到的聲音,呼吸、鳥鳴、風聲、水聲……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獲取信息的主要通道,視覺占85%,聽覺為10%。人們因為視覺方便獲得信息形成依賴而往往忽視聽覺的部分。只有視覺被屏蔽之時,聽覺的意義才得以充分體現。同理,我們是否過度依賴于視覺、聽覺等外在感覺而忽視了心靈的感知?我們是否因為世界上太多的聲色喧囂、媒體泛濫而麻木了視聽進而麻痹了心靈呢?
商品經濟社會中,每個人都看到他想看到的,每個人看到的都是別人想讓他看到的。當然,此處的“看”是“感覺”“體會”之意。每個人都因其經驗或其中狹隘的一面選擇關照的對象,同時又在別人的影響之中變為他人認知的模樣。鮑德里亞在論述消費社會中大眾、信息、媒體、商品等客體逃脫人類主體的控制最終控制主體之時,悲觀地認為這一趨勢無法改變。我們認為社會在物質文明極大發展之后,主體一定會脫離消費社會對人的異化,擺脫金錢及物質的控制從而回歸。而藝術創作是引發這一行為的觸媒,我們的作品就是想以在虛空中引發思考的方式,喚起觀者心中未因物質誘惑而完全喪失的精神價值觀念,使之可以深入反思、從而找回真正的自我。
4.3 空間消逝與時間永恒
建筑現象學學者諾伯格-舒爾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tz)談到時間時說到,時間是恒常與變遷的向度,使空間與特性成為生活事實的一部分,在任何時刻中使生活事實成為一個特殊的場所,賦予其場所精神[12]。我們在展覽作品的探索中,就是想從場地的場所精神出發進行創作,進而挖掘作品所蘊含的場所精神,即物質的暫時性與時間的永恒。展覽作品的創作,與時間關系非常密切。首先是物理的存在,通常雙年展的展期為3 個月,之后展品都會消亡。物質的易逝性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呢?40 年不短,但對一個城市來講還是處在生長時期,遠沒有積淀出一定意義上的城市精神和文化基質。深圳的大鵬所城雖因成為國保單位而得以保護,但更多體現城市風貌及文化積淀的城市基底也應得到保留。還有一種存在,即精神的存在以及延伸。空間是我們周圍的事物中最具活力的,就像精神的本質。大鵬展覽中每一個作者都希望將精神付諸于作品之中,這種精神會比作品的物質形態存留得更久。
馬丁·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深入思考“存在的意義”。他認為一切存在論問題的中心提法都根植于正確看出并解說了的時間現象以及它如何根植于這種時間現象。存在是一種時間性存在,而時間正是存在之領悟的境域。海德格爾的目標就是對時間進行闡釋,表明任何一種存在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13]。作品的存在依賴于時間,空間也依附于時間,漸漸地時間對空間產生了特權。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曾宣稱:時間的影響力在經濟生活中成了比空間的影響力更為根本的東西。而時間也通過時空的轉換和科技的發展,將空間瓦解成瞬時的同時性[14]。所以空間會慢慢消亡,而時間永恒。
5 結語
展覽開幕僅一個月便遇到新冠疫情,社會經濟生活似乎停擺,整個國家都處在隔離之中。市場可以關閉,街道也會蕭條,但時間不會停止,仍會繼續前行。期間,我們去過場地,看到一些意外場景。疫情雖隔絕了作品與參觀者,但也減少了人為干擾,反而加大了時光的參與程度,延長了展覽作品自身的生命力。經歷無人光顧的兩個多月,搭建時拂去的自然痕跡全然回復,鑒證了作品——我們試圖重現的“古城”——從建設到荒蕪的歷史(圖20)。

20 疫情期間作品現場照片(攝影:胡潤澤)
疫情延伸了我們對作品的思考,也加深了我們想表達的觀念。即我們應該如何與自然相容,如何與內心相處?病毒源頭尚未完全清晰,但顯然逃不脫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所以敬畏自然、生命平等應該是我們更要深入思考的。以家庭為單位的隔離,也凸顯了現今生活中的矛盾。一方面是個體已不習慣于密集的群居,即已不擅長與家人相處;另一方面,很多人甚至已經不會面對獨處的自我。所以,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是否應該更多地思考如何回歸家庭、如何回歸生活、如何回歸自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