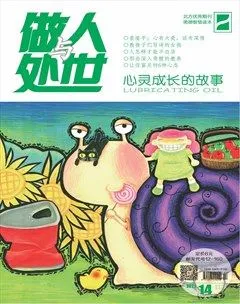我渴望成為這樣的人
李佳純
歷經歲月仍不屈不撓的精神,終將帶來真正的希望
四月的末尾,我讀完了《編舟記》。說起來我和這書特別有緣分,高一,我剛進辯論社,老師要求分組,高二的學姐充當組長,招攬合適的組員。當時,有一個學姐在介紹時說:“我曾讀過一本書,叫《編舟記》,書里的主人公是辭典編輯,他們熱愛編著辭典這項事業,并把它形容為編舟,即‘編出一座承載著綿綿不絕地從太古延伸向未來的人類靈魂,在豐饒的詞匯之海上航行的小舟。我認為辯手的使命與之殊途同歸。我們作為辯手,要探索出一條抵達真理的路,造出一座用妥帖的修辭和多元的思維支撐起的小舟。”聽她一席話,我很受鼓舞,于是選擇加入學姐的團隊,我們隊也正式起名為“編舟隊”。
于是,我找來《編舟記》一字一句地讀完。這本書的主角馬締光也,是個很容易被貼上“死板、無趣、工作狂”標簽的人。他和編輯部的幾位成員,都在編纂辭典這件事上狂熱到不被人理解。他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要為編辭典讓步,就算是吃飯時聽新聞,也要放下碗筷,拿筆記錄應該被收進辭典里的詞匯。即使是談戀愛,也要帶上“只有真正地體驗過戀愛的感覺,才能精準地寫出完美的戀愛”釋義這一目的。每一個詞匯的釋義都要百般推敲,既要做到準確、客觀、完整,又要考慮受眾,也就是讀者的感受。說起來平常,我舉一個書中的例子,以便于更直觀地感受辭典編纂人員的功底和努力。
“那么,‘しま這個詞又怎么解釋?”
“條紋、島嶼、志摩這個地名、‘旁門左道和‘上下顛倒里也包含這個讀音,還有‘揣摩臆測的揣摩……”馬締光也一個接一個列舉出發音為“shima”的單詞,荒木連忙打斷了他。
“我指的是島嶼的島。”
“我想想……‘周圍被水所包圍的陸地嗎?不,這個解釋不夠充分。比如江之島,雖然有部分與陸地相連,依然被稱作島。既然如此……”馬締光也歪著腦袋小聲地自言自語。他早已把荒木晾在一邊,忘我地思索著詞匯的意義。“解釋為‘周圍被水所包圍或被水隔離的小面積陸地比較好吧?不對不對,這也不夠全面,沒有包含‘黑社會的地盤這層意思。‘與周圍分開來的土地這個解釋如何呢?”……
這段對話,是即將退休的編輯荒木在離開編輯部之前,為了不讓他和松木老師的愿望落空,發誓要找到代替他完成新辭典《大渡海》的編纂的新人的片段。回答問題的人是馬締光也,小說的主人公。從這一個小小的測試就能看出,辭典編輯這一職務對人的要求有多高。只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詞,就要動輒查閱資料、模擬情境、打磨語言。厚重辭典包含了數以萬計的詞匯,這需要編者花費多少時間精力?已經是讓人感到恐怖的程度。
但是編纂辭典僅僅是這樣嗎?不是的。大至篩選將要收錄的詞條、委托專家撰稿、編輯部共同撰寫文稿范例,小至選擇字體、排版設計、制作專用紙,這些事有多么繁雜,多么考驗人的意志力呢?這么說吧,馬締光也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事們,足足用了15年,才得以打造出《大渡海》這一兼具指向性與品質的辭典。而在這15年中,馬締光也就已經在反復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磨平了指紋。
是不是很令人驚異呢?作為高中生,我學過《咬文嚼字》這篇課文,知道就算是在文學領域,對于作家或詩人而言,精準把控每一個字、詞的含義,并在使用過程中做到百分之百的妥當,都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更何況不是人人都擁有這種“咬文嚼字”的意識,在日常生活中,“的地得”不分、標點符號誤用或亂用、分不清近義詞、對成語望文生義……這些常見錯誤不勝枚舉。人們日復一日地消遣文字,厭倦閱讀,早已失去了對表達這個動作本身的敬畏,對表達的要求,也從“準確、妥當、得體”降至“大致意思對了就行”。
那么,既然人們普遍輕視詞匯的力量,馬締光也這群人,又是怎么做到為式微的紙質辭典傾注畢生心血呢?答案無他,唯熱愛爾。因為熱愛,所以永遠懷揣敬畏,甘之如飴;因為熱愛,所以懂得詞匯的力量是為了去守護、去傳達,為了和他人彼此相連;因為熱愛,所以誓死捍衛詞匯的自由,不讓其沒落。擁有這份珍貴的熱忱,既靠天賦,也靠人事。真正懷揣熱忱的人,在成就事業的同時也被事業成就。如雙耳不聞窗外事的馬締光也,如真正意義上為《大渡海》付出一生的松木老師,他們的靈魂是豐滿的、充盈的、有厚度的,他們的內心炙熱敏感,纖塵不染。他們賦予《大渡海》以“人性”和“人的價值”,《大渡海》也如真正的舟楫,承載他們徜徉在天地之間。我渴望成為這樣的人,我相信我會成為這樣的人。
指導老師? 熊芳芳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