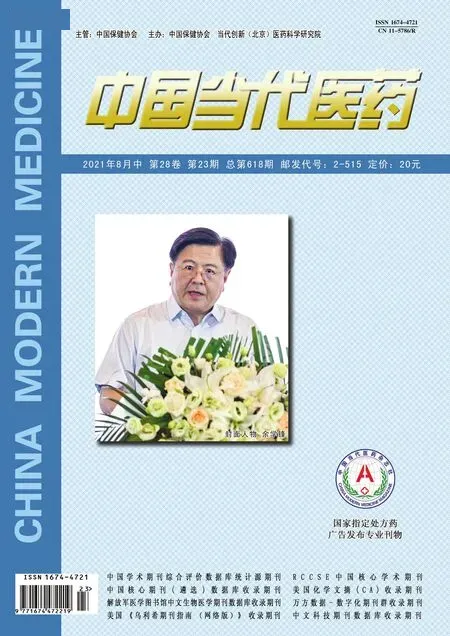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29例臨床分析
邵麗芳 田 蓉 趙 廣
空軍特色醫學中心皮膚科,北京 100142
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最早是Hardy 和Anderson 于1968年提出的一組病因不明、血及骨髓嗜酸性粒細胞持續增多、組織中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為特征的一類疾病[1],為病譜性疾病。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僅有皮膚嗜酸性粒細胞的浸潤,而不伴它組織器官受累,預后相對較好,是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的輕型或者該病的良性端。國外報道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發病率約為0.001%[2]。近年來隨著對該病發生的分子機制的深入研究,治療方法有了較大進步。但由于本病發病率低,臨床少見,皮疹表現無特異性,易導致漏診、誤診,甚至延誤治療。本研究就29 例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分析其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及對治療的反應,以提高對本病的認識。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2年1月—2019年12月空軍特色醫學中心皮膚科住院的29 例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的臨床資料。本研究經過空軍特色醫學中心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參考文獻納入標準[3]:①嗜酸性粒細胞增多:2 次檢查(間隔≥1 個月)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1.5×109/L;②骨髓中嗜酸性粒細胞增多;③具有紅斑、丘疹、結節等皮膚損害且皮損組織病理可見嗜酸性粒細胞浸潤。排除標準:①藥物過敏、支氣管哮喘、過敏性鼻炎、腫瘤患者;②糞便中查見寄生蟲蟲卵者;③骨髓涂片中有異性細胞及寄生蟲者;④肺部斑片狀陰影抗生素治療無效者;⑤近半年新發的無明確原因的心肌炎、心包炎、心內膜炎等心臟損害者。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的一般資料、發病誘因、臨床表現、血常規、生化、腫瘤標記物、組織病理、骨髓穿刺、基因檢查、影像學檢查、治療情況及治療后不良反應進行回顧性分析。
1.2 數據處理
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計數資料用率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29 例患者中男22 例,女性例,男女比例為3.1∶1;入院年齡27~87 歲,平均(61.30±14.18)歲,其中60 歲以上17 例(58.62%);病程1 個月~50年,其中18 例(62.07%)患者病程在1年內,其余11(37.93%)例患者病程在1年以上,最長者50年,病程中位數為1年。
2.2 發病誘因
29 例患者中1 例自覺與熬夜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有關,1 例自覺與季節變化有關,其余均無明顯誘因。
2.3 臨床表現
29 例患者均有劇烈難以緩解的瘙癢,夜間較重,其中11 例(37.93%)嚴重影響睡眠,4 例(13.79%)患者需要口服失眠類藥物改善睡眠。患者皮疹多累及或者泛發全身。原發皮疹主要為紅斑、丘疹、結節、斑塊,繼發性皮疹多為鱗屑、苔蘚化、抓痕。少數患者可出現水皰、水腫。患者皮疹特征及人數統計見表1。

表1 HED 患者皮疹特征

圖1 全身泛發浸潤性鮮紅斑

圖2 堅實的丘疹、結節,明顯血痂
2.4 血常規及生化檢查
29 例均行血常規及生化檢查。1.5×109/L<嗜酸性粒細胞計數<5.0×109/L 定義為中度增高,≥5.0×109/L定義為重度增高。除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增高外,白細胞計數、乳酸脫氫酶、α-羥丁酸脫羧酶增高患者比例較高。部分患者丙氨酸轉氨酶、天冬氨酸轉氨酶、β2微球蛋白、血清總蛋白、血清白蛋白等指標可見異常(表2)。
2.5 腫瘤標記物
21 例患者行腫瘤標記物檢測,15例為陰性,6 例患者有輕度升高(表2)。其中AFP 升高患者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伴肝硬化病史。

表2 HED 患者血常規及生化檢查臨床資料
2.6 皮膚組織病理檢查、骨髓穿刺及基因檢查
所有患者均行組織病理檢查,病理表現為真皮淺層及血管周圍淋巴細胞浸潤,可見較多嗜酸性粒細胞。29 例患者行骨髓穿刺檢查示各期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未見異型嗜酸性粒細胞。其中18 例患者接受FIP1L1/PDFRα 融合基因和Wilms 瘤基因(Wilms tumor gene,WT1)檢測均為陰性。
2.7 影像學檢查
7 例患者超聲心動圖示左室舒張功能降低,其中1 例示部分心肌缺血。心電圖示T 波改變1 例,ST 改變1 例。胸片示胸腔積液1 例,該患者同時伴有低蛋白血癥。雙肺間質性改變2 例。腹部超聲示肝囊腫3例,膽囊息肉2 例,膽囊結石2 例。
2.8 治療
所有患者均口服抗組胺類藥物聯合糖皮質激素軟膏作為基礎治療。在此基礎上所有患者均給予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劑治療。其中6 例未使用激素。4 例僅口服雷公藤多苷片(遠大醫藥黃石飛云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20201201)60 mg/d,出院前雖然癥狀緩解,皮疹好轉,嗜酸性粒細胞計數有所降低,但其中3例均未<1.5×109/L。其余1 例口服羥氯喹片(上海上藥中西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200871),1 例口服雷公藤多苷片配合羥氯喹片。23 例患者單用激素或激素配合免疫抑制劑治療。僅使用激素者11 例,激素用量15~45 mg/d,嗜酸性粒細胞計數用藥后2~10 d 降至正常。7~20 d 皮疹消退大于80%。激素配合免疫抑制劑者12 例,其中9 例為雷公藤多苷片,其余3 例分別為沙利度胺(常州制藥廠有限公司;生產批號:19102531)、甲氨蝶呤(上海信誼藥廠有限公司;生產批號:03619 1203)、環孢素(杭州中美華東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200354)。激素用量10~50 mg/d,嗜酸性粒細胞計數用藥后4~13 d 降至正常,9~30 d 皮疹消退大于80%。
2.9 不良反應
1 例患者使用激素1 周后出現繼發性血糖升高。1 例患者使用激素后即出現多汗、精神興奮,激素減量后癥狀消失。1 例患者因病程較長,服用激素2年后出現股骨頭壞死。
3 討論
3.1 臨床特點
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癥是一組異質性疾病,其特征為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持續性增多,嗜酸性粒細胞增多致器官損傷。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的病例中高達70%的患者具有皮膚受累[4]。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是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的良性端,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進行早期診斷和治療,可以阻斷嗜酸性粒細胞介導的器官損傷。本研究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以加強對該病的認識。
本組病例中男女比例為3.1∶1,平均發病年齡(61.3±14.18)歲,提示本病多累及中老年男性。這與國內外文獻報道一致[5-6]。該病病因不明,本組病例中絕大部分患者發病及病情加重無明顯誘因。臨床皮疹表現多樣,累及范圍較廣泛,往往具有劇烈難以緩解的瘙癢。雖然皮疹表現多樣,但本組病例主要皮疹表現可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種為浸潤性或腫脹性紅斑;一種為丘疹、結節樣損害,常伴苔蘚樣改變及皮膚干燥脫屑。此外國內外尚報道了蕁麻疹樣、血管水腫樣、扁平苔蘚樣、潰瘍性紅斑樣皮疹及黏膜潰瘍的損害。一般認為蕁麻疹樣和血管水腫樣皮疹預后稍好[4,7-8]。實驗室檢查中乳酸脫氫酶、α-羥丁酸脫羧酶升高較為突出,并且本組病例中7 例患者超聲心動圖示左室舒張功能降低。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患者心臟損害最常見,損害多樣無特異性[9],是導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無臨床心臟癥狀,但此兩項升高是否提示心肌損傷已經開始文獻并無報道。此外值得關注的是6 例腫瘤標記物陽性患者中3 例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稍高。該酶是神經元細胞中的糖酵解酶,具有特異性。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患者神經系統受累高達56%[10]。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稍高是否與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進展至神經系統受損尚無相關報道。需要大樣本資料及長期隨訪監測。
3.2 發病機制
對嗜酸性粒細胞炎癥發生的免疫機制深入了解將推動該病的治療。正常條件下嗜酸細胞的動態平衡被細胞因子網絡調控。嗜酸性粒細胞起源于CD3+、CD4+的骨髓造血干細胞。促進嗜酸性粒細胞增多和活化最主要的細胞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5(interleukin-5,IL-5)、粒細胞巨噬細胞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和白細胞介素-3(interleukin-3,IL-3)。活化的T 淋巴細胞、肥大細胞、基質細胞均可以產生上述細胞因子。嗜酸性粒細胞釋放生物活性分子,例如嗜酸性粒細胞過氧化物酶、嗜酸性粒細胞陽離子蛋白、堿性蛋白和其它多種因子造成組織損傷。持續性激活的情況下,嗜酸性粒細胞會引起微環境的變化,通常會導致纖維化,血栓形成或兩者并存,從而嚴重損害器官。持續性嗜酸性粒細胞激活的患者中,組織標本有時因為嗜酸性粒細胞崩解沒有大量嗜酸性粒細胞浸潤,但可以檢測到嗜酸性顆粒沉積,也具有同樣意義[1]。生物活性因子和標記物的監測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選擇將提供更精準的信息[11]。
3.3 治療
目前將HES 分為6 種臨床亞型,分別為:①骨髓增殖型(M-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該型FIP1L1/PDFRα 融合基因可為陽性,包括慢性嗜酸粒細胞性白血病及具有骨髓嗜酸性細胞增生特征但無單克隆性增生證據的患者。②淋巴細胞型(L-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該型為T 淋巴細胞免疫表型異常或者T 淋巴細胞克隆性增殖。③重疊型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嗜酸性粒細胞損害局限于一個特定器官或者是某些已被定義的綜合征,這些疾病具有獨特的臨床表現和并發癥,因此,與其他形式的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相比,通常有不同的治療方法。④繼發性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基于已知的病因,嗜酸性粒細胞反應性升高,例如藥物超敏反應綜合征、寄生蟲感染、免疫缺陷。⑤家族性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⑥特發性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不屬于以上任意類型[8]。既往認為除了FIP1L1/PDFRα 融合基因陽性者治療首選甲磺酸伊馬替尼外,其它所有類型都可將糖皮質激素作為一線治療。Khoury 等[12]認為糖皮質激素是否有效跟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亞型診斷密切相關。即使FIP1L1/PDFRα 陰性的M-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患者對糖皮質激素反應仍較差。超過三分之二的L-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受試者需要中到高劑量的糖皮質激素來控制疾病。對于L-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患者可以配合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綜合征管理的二線藥物包括酪氨酸激酶抑制劑羥基脲、干擾素α、甲氨蝶呤、嗎替麥考酚酯、環孢素等[13]。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一般歸為淋巴細胞型和特發性,限于條件本研究未能做淋巴細胞表型分析。本研究病例治療中23 例使用了小劑量激素(大部分為30 mg/d)配合或不配合免疫抑制劑(以雷公藤多苷為主)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但該病激素一般需持續用藥,減停過程中容易反復。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的副作用較多,目前生物制劑在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疾病中得到了廣泛關注。已報道的生物制劑包括針對IL-5、白細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細胞介素-13(interleukin-13,IL-13)、CD52、Siglec-8的抗體[14-16]。其中抗IL-5 單克隆抗體(如美泊利單抗、瑞利珠單抗)臨床數據較多。大量的臨床試驗發現該抗體具有起效迅速、副作用小及對激素抵抗的患者仍有效等優點[17-19]。此外,治療帕金森氏病的多巴胺激動劑普拉克索可引起持續性嗜酸細胞減少,該藥引起嗜酸性粒細胞減少的確切機制尚不清楚,目前仍在研究中[20-21]。
綜上所述,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臨床發病率低,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提示對難以緩解的瘙癢性皮疹,需盡早完善相關檢查,早診斷,早治療,避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進一步向惡性端發展。對于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皮炎的治療,目前臨床中激素仍是一線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