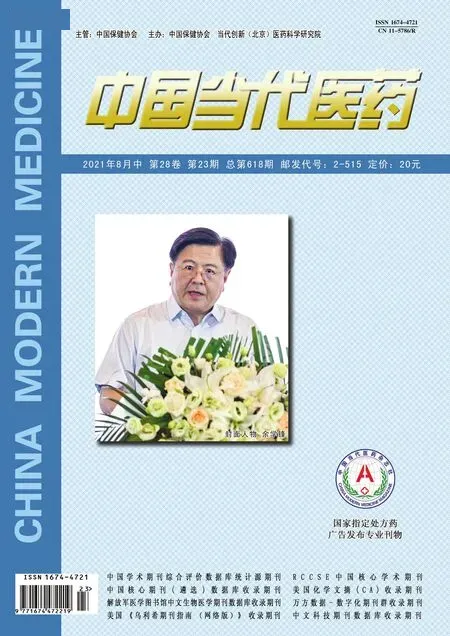2011—2020年我國藥品價格壟斷典型案例研究
王維維 陳 梅 張 煥
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藥學部,江蘇連云港 222000
1996年我國對藥品價格實現全面管控[1],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外,取消原政府定價,由生產經營成本和市場供求情況,自主制定藥品交易價格[2]。2019年底國家醫療保障局印發了《關于做好當前藥品價格管理工作的意見》,提出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促進經營者加強價格自律[3]。2020年國家醫療保障局發布《關于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濫用自主定價權導致藥品漲價、實施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且拒絕糾正”等行為,會被作為失信事項列入評價范圍,并已對數十家企業的藥品價格問題展開調查,并對20 多家企業進行了約談告誡[4]。可以看出國家不斷提高對藥品價格壟斷的監管力度,基于此本文收集2011—2020年出現的藥品價格反壟斷執法典型案件并進行回顧性分析,以期為藥品價格壟斷監管提供有益的參考和探討。
1 2011—2020年我國藥品價格壟斷典型案例概況
筆者通過輸入關鍵詞“藥品價格壟斷”,查詢官方網站及搜索引擎進行篩選,篩選標準:①經藥品價格反壟斷執法機構正式立案處理的案例;②案例影響較大,被多方報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通過篩選總結2011年1月—2020年11月我國藥品價格壟斷典型案例共17 起[5-21],并對案例從涉事主體、涉及藥品、壟斷行為、處罰結果、執法機構進行了整理分析,具體案例信息詳見表1。

表1 2011—2020年我國藥品價格壟斷典型案例統計表
2 2011—2020年我國藥品價格壟斷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以2015年6月為時間節點,從壟斷案例數量、涉及壟斷企業、壟斷類別/類型、反壟斷處罰力度等角度進行對比分析。
2.1 壟斷數量分析
搜集的17 起藥品價格典型壟斷案例中,2011年1月—2015年6月,即藥品由政府全面控價時,出現壟斷行為的案例僅僅為5 例;而2015年6月—2020年11月出現藥品價格壟斷行為的案例為12 例,壟斷案例相對增加。但從數量上看,與藥品企業受到的其他行政處罰相比,反壟斷的處罰案例較少。與其他行業所受反壟斷調查的力度相比,我國藥品行業的案件數量也不高。
2.2 壟斷主體分析
2011年1月—2020年11月涉及藥品壟斷的企業/單位共31 家,包括25 家藥企,5 家事業單位,1 家民辦非企業單位。在涉事的25 家藥企中,民營企業占92%,非民營企業僅占8%;企業人數規模為100 人以下的企業占比為48%,企業人數規模在100~499 人(含100 人)占比也為48%,超過500 人的僅為4%。由此可見,壟斷易發生在中小型民營企業中。
2.3 壟斷類別分析
搜集案例中涉及原料藥的價格壟斷案例有11例,占總比例的65%,而藥品成品制劑出現價格壟斷的案例相對較少,僅占12%;此外在藥品集中采購行為中也會出現一些壟斷行為,占比為23%。由此可以看出原料藥容易出現壟斷情形,我國是原料藥生產大國,一些原料藥的生產批文被部分企業壟斷,導致原料藥容易出現市場壟斷。所以未來應加大對原料藥壟斷的專項檢查和監管,完善原料藥的關聯審批制度。
2.4 壟斷行為分析
從2011年1月—2020年11月藥品壟斷的17例典型案例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案例占比為59%;橫向壟斷案例占比為12%;行政壟斷案例占比為29%。總體來看,壟斷行為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較多,橫向壟斷相對較少。從結構上看,藥品行業所涉及的壟斷違法行為以傳統的體制性壟斷行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橫向壟斷協議和行政壟斷為主。
2.5 處罰結果分析
2015年放開藥品價格管制以前,對7 家涉事企事業單位共計處罰743.9 萬元罰款。2015年放開藥品價格管制以后,先后處罰涉及藥品價格壟斷的企業或機構共25 家,處罰金額共計3.606 億元,其中2016年對8家涉事企業罰款共計709.54 萬元;2017年對6家涉事企業及機構處罰共計277.3132萬元;2018年對7家涉事企業處罰共計2526.52 萬元;2020年4月對涉事3 家企業處罰高達3.255 億元罰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藥品價格壟斷的處罰力度逐年加大。
2.6 我國藥品行業價格壟斷特點分析
通過對以上藥品價格壟斷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藥品價格壟斷案例呈現出以下特點:①壟斷案例頻發,并以中小型企業原料藥價格壟斷居多,以傳統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及橫向壟斷協議為主;表現為同類原料藥企業聯合漲價,如復方利血平原料藥案、別嘌醇片案、艾司唑侖片及原料藥案、冰醋酸原料藥案;以及原料藥經銷商聯合對外的不公平高價及不合理交易行為,如鹽酸川芎嗪案、撲爾敏原料藥案、葡糖糖酸鈣原料藥案。原料藥品價格壟斷案例頻現,主要原因是我國原料藥企業多,但獲得審批生產的企業少,相當一部分原料藥的生產僅掌握在極少數企業中[22],而原料藥生產商被藥品制劑生產商所依賴,從而導致原料藥市場容易出現壟斷行為。②壟斷監管和處罰力度逐年加大,從處罰力度和監管機構來看,我國在藥品價格反壟斷中不斷加大監管和處罰力度。表現為監管機構高度合一,處罰金額屢創新高[23]。2018年開始我國進行機構改革,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不斷加大對藥品招標采購行為的規范性和監管力度,從2018—2020年11月間的壟斷案例數量可看出,隨著查處力度加大,2018年至今行政壟斷行為在大大減少。
3 建議
3.1 增加處罰力度
筆者在搜集的藥品壟斷案中特別是原料藥案例中顯示,壟斷主體通過壟斷行為獲取幾十倍的暴利,但受到的處罰一般僅為涉事企業上一年銷售額1%~10%的罰款。我國對于壟斷行為的處罰力度遠遠不及美國和歐盟[24-25],即使2020年對葡萄糖酸鈣原料藥案給予了史上最高罰款3 億多元,但相較于其他國家地區的罰款仍然偏輕,2002年歐盟委員會就對靈北制藥等4 家企業罰款1.46 億歐元,美國根據《克萊頓法》(1990年修訂)允許聯邦政府采取三倍損害賠償制度,通過激勵受害者提起反壟斷訴訟,使得受害者獲得最大利益來威懾加害者[26-27]。整體來說我國法律懲罰力度較弱,違法成本太低,應增加處罰力度。
3.2 增加法律責任種類
重新梳理涉及藥品價格壟斷法律法規可以看到,對壟斷行為進行刑事追究是由美國《謝爾曼法》開創,俄羅斯、日本、英國、法國等在其反壟斷立法中相繼規定了壟斷行為的刑事責任[28]。我國現行《反壟斷法》對壟斷行為的法律制裁側重于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但都未涉及到刑事責任[29]。可以借鑒國際執法經驗完善我國反壟斷規制,改變我國目前單一的懲罰模式,嘗試制定多個處罰機制。
3.3 加強行政干預
我國目前已建立健全長效監管機制,綜合運用監測預警、成本調查、函詢約談等措施,引導企業合理定價,自覺規范企業的行為及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要加強對原料藥流通環節的行政干預,尤其從原料藥審批制度著手,加大對原料藥流通渠道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