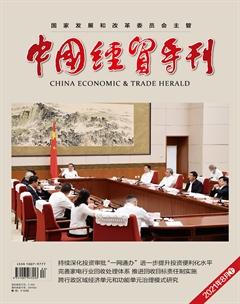“十四五”時(shí)期構(gòu)建持續(xù)高效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要注重實(shí)現(xiàn)六個(gè)轉(zhuǎn)變
王皓田

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是我國積極應(yīng)對人口老齡化帶來老年人生活危機(jī)、家庭危機(jī)、以致形成社會危機(jī)挑戰(zhàn)的關(guān)鍵舉措,也是重塑中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就業(yè)結(jié)構(gòu),實(shí)現(xiàn)全面建設(sh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qiáng)國的重要基礎(chǔ)。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構(gòu)建居家社區(qū)機(jī)構(gòu)相協(xié)調(diào)、醫(yī)養(yǎng)康養(yǎng)相結(jié)合的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我國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全面進(jìn)入新階段。一直以來,我國養(yǎng)老服務(wù)業(yè)發(fā)展中存在著局部化、碎片化、有效需求與有效供給雙向不足等內(nèi)在問題,站在“十四五”開局之時(shí),本文從完善我國養(yǎng)老服務(wù)內(nèi)在支撐體系整體性入手,對構(gòu)建持續(xù)高效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提出六個(gè)方面政策轉(zhuǎn)變的發(fā)展建議。
一、問題提出:我國養(yǎng)老服務(wù)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雙向不足并存
根據(jù)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達(dá)到2.6億人,占總?cè)丝诘?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占總?cè)丝诘?3.5%,相比于2016年分別提高2個(gè)百分點(diǎn)和2.7個(gè)百分點(diǎn)。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未來我國老齡化速度會以較高斜率上升,“十四五”時(shí)期我國將進(jìn)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的快速發(fā)展,意味著老年人對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日益增長。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我國養(yǎng)老機(jī)構(gòu)和床位的建設(shè)也不斷加快,“十二五”時(shí)期以來得到快速增長,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shù)從2011年的19.1張達(dá)到2019年的30.5張。但是,床位的利用率卻在一直下降,空床率不斷上升(見圖1)。
服務(wù)需求的日益上漲與床位利用率的不斷下降凸顯了養(yǎng)老服務(wù)業(yè)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雙向不足并存的矛盾。突出表現(xiàn)為一是養(yǎng)老機(jī)構(gòu)提供的服務(wù)不必要。日間照料中心、中低端養(yǎng)老機(jī)構(gòu)設(shè)施設(shè)備條件有限,醫(yī)護(hù)人員缺乏,只能提供一日三餐、家政等基礎(chǔ)性服務(wù),且服務(wù)質(zhì)量一般。二是提供的服務(wù)買不起。以北京市為例,根據(jù)2016年北京市養(yǎng)老相關(guān)服務(wù)設(shè)施摸底普查顯示,北京市老年人收入的中位數(shù)大約是在3300元,而養(yǎng)老機(jī)構(gòu)涵蓋床位費(fèi)、餐費(fèi)和護(hù)理費(fèi)三者,最低需要花費(fèi)3000元,最高需要花費(fèi)1萬元以上,存在較大的收支缺口。三是需要的服務(wù)沒提供。長期照護(hù)作為養(yǎng)老服務(wù)中最為核心的內(nèi)容,許多養(yǎng)老機(jī)構(gòu)不具備提供的能力;對于居家養(yǎng)老服務(wù)來講,上門類的長期照護(hù)是關(guān)鍵,而目前我國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不夠清晰、服務(wù)類別不夠具體,多數(shù)日間照料中心等社區(qū)養(yǎng)老平臺無法提供居家養(yǎng)老的長期照護(hù)服務(wù)。
二、發(fā)展歷程:我國養(yǎng)老政策體系發(fā)展脈絡(luò)
我國的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體系建立比較晚,一直是作為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國家通過建立公辦福利院、五保制度,提供救濟(jì)型的養(yǎng)老服務(wù),并嵌入到整個(gè)經(jīng)濟(jì)體制中。隨著國家對老齡化的重視,制度變遷導(dǎo)致傳統(tǒng)保障功能的減弱,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逐步建立起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體系,大致分為三個(gè)階段。
(一)早期探索(1982—1999年):“福利性”轉(zhuǎn)向“社會化”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我國進(jìn)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農(nóng)村人民公社的取消,城市單位制的瓦解,國有企業(yè)改革,原先的集體保障、單位保障各類養(yǎng)老服務(wù)機(jī)制逐漸消失,只剩下對農(nóng)村五保戶和城市三無人員的救濟(jì)政策,老年人對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無法得到保障。國家開始正視人口老齡化與傳統(tǒng)保障功能弱化的事實(shí),1982年“中國老齡問題全國委員會”成立,全國各地也開始建立了老齡工作機(jī)構(gòu),中央到地方的老齡工作網(wǎng)絡(luò)逐步形成。1983年民政部提出“社會福利社會化”的社會福利事業(yè)改革思路,推動社會福利由國家包辦向國家、社會、個(gè)人共辦轉(zhuǎn)移,社會機(jī)構(gòu)開始興建為老服務(wù)的福利機(jī)構(gòu)。1993年,民政部等14個(gè)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了《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社區(qū)服務(wù)業(yè)的意見》,首次將“養(yǎng)老服務(wù)”從社會福利概念中獨(dú)立提出。1994年,原國家計(jì)委等10個(gè)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中國老齡工作七年發(fā)展綱要(1994—2000年)》,明確了老齡事業(y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了家庭養(yǎng)老與社會養(yǎng)老相結(jié)合的原則,擴(kuò)大老年人社會化服務(wù),這是我國在國家層面對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體系的早期探索。
(二)初步建立(2000—2012年):社會養(yǎng)老概念、體系開始形成
1999年末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cè)丝诒戎爻^10%,開始進(jìn)入老齡化社會。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頒布《關(guān)于加強(qiáng)老齡工作的決定》,養(yǎng)老服務(wù)”開始作為一個(gè)專有的概念被使用,為推進(jìn)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奠定基礎(chǔ)。2001年我國第一次把老齡化事業(yè)納入了更大范圍的國家五年規(guī)劃之中,老齡事業(yè)規(guī)劃綱要進(jìn)入五年為期常態(tài)化的制定過程。2006年全國老齡委等十一部門聯(lián)合頒發(fā)了《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養(yǎng)老服務(wù)業(yè)的意見》,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養(yǎng)老為基礎(chǔ)、社區(qū)服務(wù)為依托、機(jī)構(gòu)養(yǎng)老為補(bǔ)充的服務(wù)體系”,明確了“居家”“社區(qū)”及“機(jī)構(gòu)”三種養(yǎng)老方式。2011年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社會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規(guī)劃(2011—2015年)》,對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的內(nèi)涵、功能定位、指導(dǎo)思想和基本原則等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自此,“社會養(yǎng)老服務(wù)”的概念基本形成,明確了國家福利制度外的養(yǎng)老服務(wù)的制度定位。
(三)逐步完善(2013年至今):社會化和體系化進(jìn)一步延伸
黨的十八大作出應(yīng)對老齡化的戰(zhàn)略部署,明確提出“要積極應(yīng)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fā)展老齡服務(wù)事業(yè)和產(chǎn)業(yè)”,我國養(yǎng)老服務(wù)的政策、法規(guī)紛紛出臺。2016年《民政事業(yè)發(fā)展第十三個(gè)五年規(guī)劃》,將醫(yī)養(yǎng)結(jié)合直接納入到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中。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quán)益保障法》再次進(jìn)行修訂,明確指出不再實(shí)施養(yǎng)老機(jī)構(gòu)設(shè)立許可,這意味著國家全面放開了社會力量進(jìn)入養(yǎng)老服務(wù)領(lǐng)域,國家從準(zhǔn)入管理向綜合監(jiān)管邁進(jìn)。2019年4月《關(guān)于推進(jìn)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的意見》,提出建立由民政部牽頭的養(yǎng)老服務(wù)部際聯(lián)席會議制度,各地要將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落實(shí)情況納入政府年度績效考核范圍。2019年11月,《國家積極應(yīng)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guī)劃》印發(fā)實(shí)施,從財(cái)富儲備、勞動力供給、為老服務(wù)和產(chǎn)品供給體系、科技創(chuàng)新、社會環(huán)境五個(gè)方面部署了應(yīng)對老齡化的工作任務(wù)。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積極應(yīng)對老齡化上升到國家戰(zhàn)略,推動養(yǎng)老事業(yè)和養(yǎng)老產(chǎn)業(yè)協(xié)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