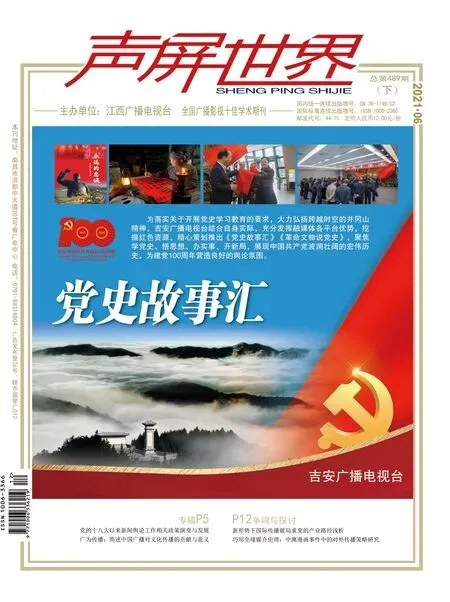新民謠中城市符號(hào)的情感投射研究
□陳靜 楊歡歡
2015年可謂新民謠的繁榮年。借助浙江衛(wèi)視,張磊的一曲《南山南》唱紅大江南北。同年,趙雷的一首《成都》在湖南衛(wèi)視《我是歌手》斬獲大量粉絲,2016年,此歌在網(wǎng)易云音樂(lè)上架,隨后聽(tīng)眾在各大音樂(lè)社交媒體轉(zhuǎn)載和討論,“成都”瞬間成為歌者和聽(tīng)眾心中隱秘的情感所在地。隨后“民謠熱”席卷了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市場(chǎng)。此前身處于主流音樂(lè)之外民謠歌手,在各大音樂(lè)選秀節(jié)目和新媒體平臺(tái)的推波助瀾下,迅速進(jìn)入大眾視野。
本文選取網(wǎng)易云音樂(lè)APP中10首新民謠為觀察對(duì)象,運(yùn)用話(huà)語(yǔ)分析和網(wǎng)絡(luò)民族志的方法,探討歌詞文本如何對(duì)城市進(jìn)行符號(hào)化編碼,聽(tīng)眾在評(píng)論文本如何進(jìn)行選擇性情感解碼,城市符號(hào)情感化投射如何實(shí)現(xiàn)都市青年的情感認(rèn)同。
歌詞文本中城市符號(hào)的情感編碼
新民謠歌詞文本用質(zhì)樸的詩(shī)性話(huà)語(yǔ)和真誠(chéng)的情感訴說(shuō),傳達(dá)歌者對(duì)城市的理解和體驗(yàn)。地域化、意象化、懷舊化敘事對(duì)城市符號(hào)進(jìn)行情感編碼,影響著聽(tīng)眾的情感認(rèn)同。
筆者選取10首網(wǎng)易云音樂(lè)APP上評(píng)論數(shù)較高的新民謠,對(duì)歌詞文本進(jìn)行分析,提取城市、城市意象關(guān)鍵詞和情感編碼關(guān)鍵詞,總結(jié)城市符號(hào)的三重情感編碼意蘊(yùn)。(見(jiàn)表1)

表1 10首具代表性的新民謠(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時(shí)間2019年6月)
一、“故鄉(xiāng)”的記憶與“他鄉(xiāng)”的尋忘。對(duì)新民謠創(chuàng)作者來(lái)說(shuō),歌詞中的“城市”指“故鄉(xiāng)”或“他鄉(xiāng)”,或有故事的地方,傳達(dá)創(chuàng)作者的回憶。城市間漂泊是生活的常態(tài),但對(duì)“故鄉(xiāng)”的記憶又是歌者情感的原鄉(xiāng)。
趙雷的《成都》中“成都”并非歌者的故鄉(xiāng),而是曾生活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城市。作者說(shuō):“成都是我最?lèi)?ài)的城市”,有著他鄉(xiāng)和家鄉(xiāng)雙重屬性。歌詞中將“小酒館、玉林路”等地點(diǎn)與“九月、依依不舍、為難、思念、眼淚、自由”等詞意動(dòng)性的組合,構(gòu)成對(duì)成都的回憶,引起聽(tīng)眾共情。《廣東十年愛(ài)情故事》中,“廣州”是十年漂泊的無(wú)奈與失去的唏噓。用粵語(yǔ)與普通話(huà)的不同方言的結(jié)合,成為歌者感受城市最外在的文化表征,有意用語(yǔ)言的混合完成地域文化的交融,模糊文化身份,在漂泊中的完成情感尋根。《安和橋》通過(guò)北京一個(gè)叫安河橋的地方,講述著城市里熟悉的地方、平凡的故事和故事里親切的人。橋作為意象性的地域景觀,有顯著的懷舊化特性,建構(gòu)具有個(gè)人化的情感故事和社會(huì)空間,用底層化敘事話(huà)語(yǔ)將文化鄉(xiāng)愁編碼進(jìn)歌中。
二、成長(zhǎng)的迷惘與愛(ài)情的向往。如果說(shuō)成都、蘭州、廣州成為了連接歌者文化鄉(xiāng)愁的城市符碼,那么《關(guān)于鄭州的記憶》,歌者通過(guò)反復(fù)出現(xiàn)的“火車(chē)、她、巷子、煤爐味道、霧氣”等意象與城市聚合編碼建構(gòu)意義。在火車(chē)經(jīng)過(guò)的鄭州,歌者觸景生情想起的那個(gè)“她”,訴說(shuō)著人類(lèi)成長(zhǎng)中的情感母題:愛(ài)情、理想、自由和信仰,折射出青春的情感體驗(yàn)——懷疑、追問(wèn)、反思、向往與遠(yuǎn)方。人們總在與外在世界的創(chuàng)傷性體驗(yàn)背后呈現(xiàn)出自我精神成長(zhǎng)的歷史。《春風(fēng)十里》中,象征大都市的“二環(huán)路”,象征鄉(xiāng)野的“遠(yuǎn)方的山上”。一段沒(méi)有結(jié)局的愛(ài)情,“我在二環(huán)路的里邊想著你,你在遠(yuǎn)方的山上春風(fēng)十里”。《一個(gè)西藏》這首歌里,“西藏”已成為連接我與世界的符號(hào),象征著理想和信仰的情感圣地。
三、邊緣的徘徊與生活的無(wú)奈。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新民謠有特定聽(tīng)眾群體,底層化敘事反映著他們的“階層”屬性。正如巴赫金指出“符號(hào)的形式首先由使用該符號(hào)的社會(huì)組織,由他們相互作用的最接近的環(huán)境所決定。”英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齊格蒙特·鮑曼用“流動(dòng)性”來(lái)形容現(xiàn)代社會(huì)。歌手周云蓬表示,新民謠歌手“更多是在城市魚(yú)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環(huán)境中掙扎的邊緣人”,將無(wú)處安放的情感與精神困惑投射歌中。如《去大理》中“是不是對(duì)生活不太滿(mǎn)意,很久沒(méi)有笑過(guò)又不知何?既然不快樂(lè)又不喜歡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音樂(lè)社交用戶(hù)評(píng)論文本的情感解碼
從用戶(hù)評(píng)論文本的內(nèi)容來(lái)看,多元化和分散化是熱門(mén)評(píng)論內(nèi)容的兩大特點(diǎn)。筆者選取點(diǎn)贊量排名前10的精彩評(píng)論,共105個(gè)樣本進(jìn)行分析。
霍爾認(rèn)為,“符號(hào)學(xué)的編碼——解碼模式之間存在諸多差異性。在信息的傳遞和接受過(guò)程中既存在主導(dǎo)文化秩序不對(duì)等,又存在著私人、個(gè)體和不同形式的解碼過(guò)程。對(duì)于同一編碼的他者文本至少有順從性解碼、妥協(xié)性解碼和對(duì)抗性解碼,三種不同解讀的可能性。”(見(jiàn)表2)

表2 105條熱門(mén)評(píng)論分類(lèi)
一、順從性解碼。民謠歌詞淺顯易懂,聽(tīng)眾根據(jù)自身經(jīng)歷選擇性感知歌詞的敘事話(huà)語(yǔ)。因此,懷舊的故事、抒發(fā)個(gè)人經(jīng)歷的評(píng)論一般同樣出現(xiàn)在此類(lèi)歌曲后,聽(tīng)眾用自身經(jīng)歷去回應(yīng)編碼者的意圖,順從性的和信息編碼者保持理解與情緒上的一致,達(dá)到情感認(rèn)同與共鳴。這類(lèi)評(píng)論詳盡敘述較多具體細(xì)節(jié),其他聽(tīng)眾讀到會(huì)產(chǎn)生很強(qiáng)的代入感,進(jìn)而后續(xù)點(diǎn)贊和追評(píng)。在音樂(lè)社交評(píng)論區(qū)中將藏于心、難于啟齒的故事、情感通過(guò)歌詞評(píng)論互動(dòng),實(shí)現(xiàn)部分情感傾訴的需求,同時(shí),避免與熟人社會(huì)的碰撞,更真實(shí)地表達(dá)情感。
二、妥協(xié)性解碼。“妥協(xié)性解碼是解碼者既部分的認(rèn)同主導(dǎo)性編碼意義,又部分抵制或偏離編碼意義的過(guò)程。”評(píng)論內(nèi)容是對(duì)原歌詞進(jìn)行“文本再生產(chǎn)”的過(guò)程。英國(guó)學(xué)者朱莉·桑德斯(Julie Sanders)認(rèn)為“在所有的改編中都存在一種對(duì)作品的內(nèi)在感覺(jué),這種感覺(jué)部分地是由人們感覺(jué)到的文本之間的相同或相異喚起,是期待與驚喜相聯(lián)系的相互影響。”聽(tīng)眾常常運(yùn)用相同或類(lèi)似的語(yǔ)句,仿照原文本中的句式進(jìn)行恰如其分的改編。如《春風(fēng)十里》最熱門(mén)評(píng)論:“春風(fēng)十里/五十里/一百里/體測(cè)八百米/海底兩萬(wàn)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八喜可可布朗尼/榴蓮菠蘿蜜/芝士玉米粒雞汁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黃燜辣子雞紅燒排骨醬醋魚(yú)/不如你/全都不如你”。雖然杜牧《贈(zèng)別》詩(shī)最早出現(xiàn)“春風(fēng)十里”這個(gè)詞,作家馮唐的詩(shī)《春》中有“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風(fēng)十里,不如你”,但現(xiàn)今“春風(fēng)十里不如你”成為俗語(yǔ)在大眾中流行,卻得益于新民謠作品《春風(fēng)十里》。聽(tīng)眾照著原歌詞的句式和格調(diào),運(yùn)用象征手法,組合多重意象,加個(gè)“不如你”作為結(jié)語(yǔ),創(chuàng)造性的解碼使評(píng)論文本呈現(xiàn)出新詩(shī)意、與原文本情感互應(yīng)。
三、對(duì)抗性解碼。“對(duì)抗性解碼是以某種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顛覆編碼規(guī)則,表現(xiàn)對(duì)一切意義的解構(gòu)。”這類(lèi)評(píng)論以純調(diào)侃、虛無(wú)、批判和灌水居多。如“沒(méi)故事沒(méi)酒”“姑娘在哪里”因研究意義不大,不作贅述。
吟唱消費(fèi)中情感想象共同體的建構(gòu)
人類(lèi)在集體生活中產(chǎn)生了種種共同體,其中,地域和人群是構(gòu)成共同體兩大要素。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huì)》中認(rèn)為:人類(lèi)歷史的發(fā)展是一個(gè)理性不斷增長(zhǎng)的過(guò)程,由契約關(guān)系和現(xiàn)代機(jī)械文明所構(gòu)成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必然使人類(lèi)生活的形式從強(qiáng)調(diào)地緣的共同體時(shí)代過(guò)渡到強(qiáng)調(diào)精神歸屬感的社會(huì)團(tuán)體時(shí)代。
當(dāng)今世界,隨著城鄉(xiāng)間的流動(dòng),現(xiàn)代生活中的社會(huì)關(guān)系變得疏離,互聯(lián)網(wǎng)深刻的改變著群體的生活方式,也重構(gòu)著社會(huì)空間。如滕尼斯所言“共同體的天然狀態(tài)建立在有關(guān)人員本能的中意或習(xí)慣制約的適應(yīng),或與思想有關(guān)的共同記憶之上。”媒介是意指的工具,通過(guò)意指過(guò)程建構(gòu)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其終極目的是從“反應(yīng)共識(shí)”轉(zhuǎn)向“制作認(rèn)同”。吟唱消費(fèi)中的新民謠,借助音樂(lè)媒介,在歌詞文本符號(hào)化“編碼-解碼”互動(dòng)中,滿(mǎn)足了歌者和聽(tīng)眾懷舊化的文化鄉(xiāng)愁。越過(guò)城市生活中的區(qū)位距離,進(jìn)行著跨時(shí)空的人際交往,基于精神交往與心理想象的情感投射,在虛擬空間里建構(gòu)想象共同體,實(shí)現(xiàn)某種社會(huì)秩序、心理歸屬和身份認(rèn)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