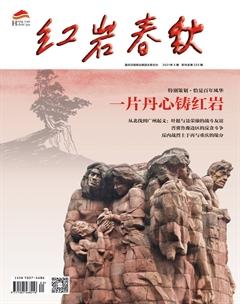周恩來第十三次住留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之謎
方海興
《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刊載的陳答才、呂越穎撰寫的《周恩來住留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及其歷史貢獻》一文,考辨周恩來住留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情況部分指出:“第十三次,1940年7月27日,周恩來從重慶飛西安到辦事處,約于30日返延。八辦負責人伍云甫1940年7月27日日記記載:‘下午6時左右,周副與童小鵬自機場來,12時半就寢。同月30日日記又記載:‘因準備飛機接周副事,下夜1時就寢。而30日日記中‘接周副顯然是筆誤,應為‘送周副。筆者推斷是伍云甫當時筆誤,或是后來文稿整理者校對有誤。因為30日周恩來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并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報告,伍不可能再次‘接周副。”言下之意,周恩來第13次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住留時間是1940年7月27日至30日,大約四天。
筆者認為,此處伍云甫日記中的“接周副”并非筆誤,后來文稿整理者的校對也沒有出錯。筆者查閱史料,認為1940年7月,周恩來第13次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僅27日住宿一晚,28日上午即飛回延安。
帶“中央提示案”返延安
周恩來此次由重慶返回延安的具體背景是:繼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國民黨頑固派正在醞釀發(fā)動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方面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陜甘寧邊區(qū),縮編八路軍和新四軍,并限制其防地。周恩來此次就是帶著“中央提示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yún)R報并商討應對之策。此事緊迫且事關國共關系大局,國民黨中央也急于知曉中共中央的態(tài)度,因而全程派飛機接送周恩來。
陳伯鈞(開國上將)此時正在延安學習,他在7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駐抗大。早飯后無多事,只看新聞與《解放》報。接著就是看飛機。本來早已聽到飛機的輕微響聲,但因云霧低接大地,飛機不敢降落。又耽誤了半小時,日出云升,大地較前顯露,飛機才從天而降。著陸前后,四周有很多人圍攏去看熱鬧。我們亦遠站山坡上用望遠鏡看飛機場上的一切活動,并能判斷機上下來之人員。不久,周副主席招待飛機師到抗大小坐,藉資休息與喝水。于是我同光達(即許光達,時任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三分校校長)跑到山下政治部辦公室前面去歡迎副主席。”他在次日的日記中又寫道:“晚間歸來,遇許校長由西北菜社歡宴周、董、徐的席上回來。”
由陳伯鈞的日記內容可知,周恩來7月28日上午便飛回延安。《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1940年“7月27日”條目記載:“飛延安,帶回國民黨的‘中央提示案。”《周恩來傳》則明確寫道:1940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來坐飛機返回延安”。 這表明,此兩著作也未能厘清周恩來此次由重慶飛回延安的具體行程。
日記全文揭開謎底
《周恩來住留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及其歷史貢獻》引用伍云甫1940年7月30日日記時只選取了最后一句話,伍云甫這天日記的全文是:“上午5時起床。上午整理本處人員名冊。下午訪空軍總站張站長,郭喜生、陳宏謨二聯(lián)絡參謀。因準備飛機接周副事,下夜1時就寢。”
20多天后,伍云甫聯(lián)系好的這架飛機出現(xiàn)在延安的機場。
陳伯鈞在1940年8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晚飯后正同光達等打網(wǎng)球,有一架飛機來到,當時機場無人照顧,也無信號和警戒,于是我們停止打球而專門看飛機去了。光達臨時叫抗大學生為之警戒。來機為兩個發(fā)動機的運輸機,可載廿人左右,主要是送款和接周副主席出去的。”他在次日的日記中又寫道:“晨為機聲所擾,故起床較早。今日天氣清和,周副主席之出發(fā)必很順利。”
另據(jù)《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0年“8月25日”條目記載:“從延安經(jīng)蘭州飛抵重慶。”
顯然,伍云甫拜訪“空軍總站張站長與郭喜生、陳宏謨二聯(lián)絡參謀”,就是在向國民黨方面接洽派飛機赴延安接周恩來回重慶事宜,此即“準備飛機接周副事”一語的含義;此處的“接周副”并非伍云甫在西安迎接周恩來,更非“送周副”之誤。
《周恩來住留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及其歷史貢獻》一文指出,1940年7月30日周恩來已經(jīng)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并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報告。而當天下午,伍云甫才開始往訪國民黨西安空軍總站,與站長接洽飛機飛行事宜,并一直為此事工作至翌日凌晨1時。顯然,該文所持的周恩來“約于30日返延”的判斷與事實及邏輯均難吻合。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1940年7月周恩來由重慶回延安,僅27日在西安辦事處住宿一晚,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