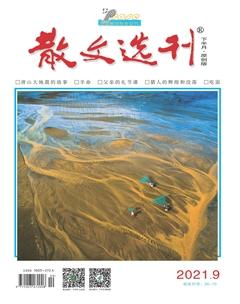我的運水哥
徐群

運水哥大我八歲,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們兄弟倆很是投緣,我從會走路起,就愛跟在他屁股后面轉。
幼年喪父的運水哥孤兒寡母,生活艱難,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耕田割稻,撐船捕魚,燒窯制磚,運水哥是村民眼里數得上的務農能手。少年時光的綿長春雨,帶給我和運水哥無限的漁趣。雷雨停歇的次日清晨,地勢頗高的田畈紛紛開溝排水,運水哥就帶我到那些田里撿魚。淺淺田溝中,隱隱現出一尾尾菜花魚黑黑的脊背,令人激動不已。運水哥挽起褲管走下田塍,魚們嗅到了響動,嘩啦啦如箭似的四處穿梭,身手敏捷的他,瞅準水花,一次次成功地將魚捉住。
我在旁看得眼熱心癢,也學著捉魚。我赤腳踩進田里,屏住呼吸,慢慢接近魚群,那魚兒鱗光一閃,沒了蹤影。定定神,又看到了,我心急火燎,一不小心撲倒在爛田里,怎么也爬不起來,運水哥見狀扔了魚簍,飛奔過來,一把將我扯起,一邊大聲叫我,一邊忙不迭地為我擦去臉上的污泥水草。
到了汛期,運水哥就在湖邊撐起一頂四四方方的扳網,頗有些執著地捕上一個通宵達旦。而我坐在他身邊,看他一下下起網。魚兒在網中活蹦亂跳,我在岸上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直到母親再三呼喚,才依依不舍回家睡覺。
從這個村子的祠堂小學出發,我進了城里的中學,后來,又如愿以償考進了省城的一所重點大學。
那日,運水哥來送我上大學,他告訴我,走遍天下是他自小的夢想。有些事如果年輕時不去做,將來會后悔一輩子的。說完這話,運水哥用他寬厚的手掌撫了下我的頭發。我仰視著年方二十幾歲、高大魁梧的運水哥,看出他目光里掠過的一絲強烈渴望,這樣的夢想看似樸素,實則意味深長,但當初的我并不明白他內心深處的心思。
大學畢業后,我在省城安家落戶,去湖山村的次數自然少了。十幾年間也就那么幾次。記得一次是運水哥新樓房落成的進屋酒,另一次是他的結婚喜宴,好像還有一回,真的記不得了。我結婚生子后,去得更少了,湖山村于我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了。
但我仍然對這個小村心存美好的向往與深刻的記憶。就在數月前,我無意中看到了一則報道,說的是牟山湖環湖即將大開發,周邊村莊將悉數動遷,湖山村也列入其中。那晚,我輾轉反側,竟然為這個村莊的去留而失眠了。我為村子里一座座百年老屋的消亡而憂傷,也為久未謀面的運水哥的生計而惶恐,他從事了半輩子舟楫往來,春播秋收,從此即將選擇離開。我知道,對這座村子而言,我是一陣吹來吹去的風,而運水哥卻是一棵根深葉茂的樹,他離不開這片賴以生存的土地。
去年楊梅季,我送朋友去車站,在車站廣場遇見了運水哥。他頭發蓬亂,滿臉土色,帶著生活的滄桑站在那里,像被歲月風霜無情刈割的一株櫟樹。他對我說,剛賣完楊梅,準備回去上夜班。他現在在一住宅小區做保安,養老金也已拿了兩個月了,加上自家山上的楊梅和茶葉,以及空閑時間捕點魚蝦賣,幾項合起來,一年下來也有十來萬的毛收入。就是兒子不爭氣,我掙的鈔票遠不夠替他還債。說起他兒子,運水哥不住地搖頭嘆氣,臉上浮現一層沮喪的神色。兒子賭博成性進了監獄,欠下一屁股外債,債主三天兩頭找上門來,媳婦也跟著人家跑了,留下孫子讓我們老兩口養。說到小孫子,運水哥眉目舒展了許多,他朝我笑了,可我始終笑不起來。望著他獨自遠去的背影,心里很長時間不是滋味,為他?抑或為他們這一代人?
這天中午,剛從食堂用完餐,忽然下起瓢潑大雨,讓人猝不及防。
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我突然接到運水哥女兒的一個電話,說是她父親因突發腦溢血,醫院下了病危通知,家里人決定放棄治療,現在他人已回到村里。電話那頭,他的女兒幾度哽咽失聲。聽完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我的心頭像是遭受了重重一擊。來不及多想,趕緊處理下手頭的幾件要緊工作,倉促地向湖山村趕去。此番,看似倉促,其實思量已久。我知道,盡管我以后還會再去,但這個曾經于我留下真愛與夢想痕跡的地方,以后必定會和原先不一樣了。是的,會不一樣了。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會有自己一座山一條河,以及過去的一個村莊。
此刻,急駛的小車載著我,正與它一點一點靠近,正在一點一點地逼近我的內心。我本不寧靜的心陡生出一股莫名的悵然若失,仿佛是去赴一場深情的告別。
遠處的地平線上,一輪太陽即將落下,它斂起耀眼的光芒,變成通紅通紅的一張圓臉。晚霞映照下的湖面,與天空一般色澤豐富,猶如千條萬條飄飄閃閃的綢子,撫慰著我躁動不安的心靈。故鄉這個叫牟山湖的湖泊,比起西湖、太湖的聲名簡直不值一提,可在我的心里,它的美好與熟稔卻遠勝過那些江南名湖。
暮色四合,落日的余暉讓大地顯得凝重起來,那條向著湖山村而去的鄉道以及周圍的景物,漸漸融入一片蒼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