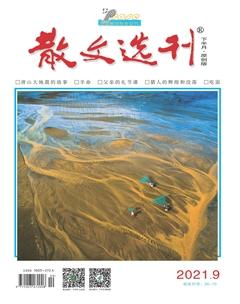消失的一星期
朱未

毫無征兆,在一個周日的早上,我開始腹痛。
這天,如往常一樣起床,洗漱完后,我坐在沙發上準備吃愛人烤的面包。這時,腹痛開始了。我想,或許是餓了,或是岔氣,吃完早飯也許就恢復了。然而,飯后疼痛加劇,那是一種肺部以下、腹腔中間位置的疼痛,痛感呈環狀,放射到后背。于是,在冬季一個暖陽杲杲的日子,我踩著香樟樹黑色的果子,佝僂著走進了醫院。
經過問訊、觸摸、驗血與CT檢查,被告知得了急性胰腺炎,需住院治療。疫情期間,住院須先做核酸檢測,所以,當天只能在門診掛水,一直到深夜一點。從星期一的早上開始住,彼時,我并不清楚要在醫院里度過幾個白晝與夜晚。
病房號711,和愛人開玩笑說,我住進了便利店。病房三人一間,一位43歲的大哥早我一天人院,他與我是同樣的病癥,不過我是初次發作,而他卻因為急性胰腺炎第七次入院。聽到他報出的數字,我驚訝不已,他是到底放肆自我到了何種程度才會如此反復地進出醫院。大哥說他每隔一兩年就會發作一次,人院、治療、恢復,繼續酒肉生活,如此循環往復,不加節制。
“我現在喝一碗白粥,感覺都是最香的。”他從昨天開始就沒有吃東西了。
住院第一天,身體處于余痛的振動之中,護士通過機器設定流速,我被24小時不間斷地注射藥物。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天,我的身體被禁錮在床上,不能自由活動,我肉眼所見的世界是病房,四肢所能控制的區域是病床。手臂的疼痛是隱隱約約的,又是永不停息的,每一滴藥水的滴落,帶來一段陣痛。到后來,血管受到不間斷的沖刷刺激,腫脹起來,胳膊比原來胖出許多,像一條飽滿的牛蛙腿。
戳入手臂的針頭,像是閃著寒光的鐵鏈,被囚禁在病房的時間,仿佛幾個世紀那樣無聊而漫長。我打開手機,可有可無地回復幾條消息,一只手舉著手機,不一會兒就累得放棄。藥水和營養液不停地流人體內,讓我得以存活下去。每天,不同的護士來給我注射和換藥,我不能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我活著,然而,僅僅是活著而已。
住院前三天,我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吃東西。前兩天,疼痛覆蓋了一切的欲念,因為有輸液的加持,感覺不到饑餓,我甚至忘記了人類還需要吃飯這個事實。第三天,身體漸感舒適,干裂的嘴唇就像龜裂的土地,渴望著甘霖降世,想吃東西的欲望復蘇了。愛人切了幾片黃瓜給我擦拭嘴唇,我貪婪地把黃瓜含在嘴里吮吸,如此甘甜、如此美味,仿佛三萬六千個毛孔都吃了人參果。那一刻,黃瓜的汁液就是最好的玉液瓊漿。第四天,醫生開了一罐營養粉,用溫水攪勻,乳白色的液體,真正的可以浸潤口腔直通腹部的液體,小時候,喝豆奶粉之類的固體飲料我會吐,而此時,杯中美好的營養粉,是如此的動人。第五天,護士在住院牌飲食那一欄,貼上了四個字:清淡流食。這意味著我可以吃食物了,我終于理解了同病房那位大哥對白粥的渴望。
住院期間所要忍受的痛苦,可不僅僅是胳膊的腫脹和腹部的饑餓,還有屋內環繞的無休止的呼嚕聲。那位大哥的父親六十多歲,五短身材,頭大臉圓,一副憨厚樸實的樣子,然而他的呼嚕聲并不樸實。他鼾聲如雷,一旦開始,一刻不停。他睡著時,張著嘴巴,大口吸進氧氣,大口排出二氧化碳,各個音階的聲音從他口腔和鼻腔噴涌而出,那鼾聲轟轟隆隆,勢不可擋,就像拖拉機駛過夜晚寂靜的街道。
住院一周,我擺脫了社會所賦予我的一切角色。不再是一名文學工作者,不必處理瑣屑的工作,不須回復那么多的微信群消息。疾病成了最好的防火墻,把社會關系擋在了墻的另一面。醫院外的世界運轉良好,我參與或是不參與,都是無足輕重的。詩人穆旦寫過:“你給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正如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這一周,我胳膊疼痛、饑腸轆轆,身心卻獲得了清風徐來一般的平靜。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生病會讓一個人明白,只有存在本身才是存在的意義所在,存在之外的種種不過是存在的附加而已。那些天里,“想到故我與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人難為情”,夜晚從7樓的窗戶眺望這座城市,那樓房里的點點星火是如此溫暖而溫情。
住院一周,我所經歷的那些瑣碎,仿佛光束中飛舞的塵埃,細微而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