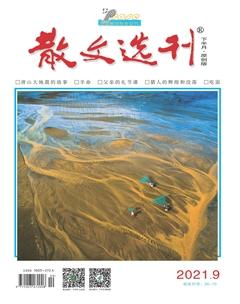父親
韓琨瑤

父親是一位地質工作者,他們一會兒這兒,一會兒那兒。山越多、越險、越閉塞的地方,就是他們要去工作的地方。
逢暑假,媽媽便帶著我和弟弟去尋父親。父親的單位夾在大山的中間,我們乘坐著解放牌汽車在崎嶇的山路上轉暈了頭,才看到山坳里的一大片青磚樓房。車子在那幢略高些的房前停下來,司機跑進去連叫了幾聲“韓工”,才見父親不緊不慢地走出來。他蓬松著頭,滿臉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像山中燒炭的老農,怎么看父親也不像是個工程師。走進父親房里,我們看到滿屋的零亂,一大攤鋪開的繪圖紙,紙上精致的標志以及密密麻麻像機器印制的細線,這才意識到,父親真的不一般!
父親的地質隊離家二百余公里,那時交通不方便,父親每年只在我們寒暑假期間回來。
每次聽說他要回家,我和弟弟都很欣喜,整天地盼著。等他拎著大包小包走進家門時,我們卻又很惶恐,一來可能是由于很久沒看到父親;二來呢,是父親對我們要求嚴格的緣故!每每這時,我和弟弟總躲進內屋悄悄偷窺父親,而父親總是不慌不忙地打開黑皮包,頭也不抬地喊:“樹紅!樹昆!過來拿你們的東西。”這句話是我們一年中最感到驚喜的。我倆會丟掉羞怯爭先恐后地湊上去。父親翻了翻,拿出兩個鐵殼文具盒和繪圖鉛筆,分我們一人一份(那時綠顏色的這種繪圖鉛筆最好了,使勁兒削都不斷頭),又摸出一些糖果給我們。我和弟弟拿著糖果去四合院中吃,左鄰右舍的小朋友羨慕地望著我們,分享著我們有個當工人的父親的快樂。
第二日,我們就再也快樂不起來了。因為父親開始查問我們的學習,檢查我們的考試成績,并為我們制訂假期學習計劃。計劃很緊湊,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由他帶領,到房后的田問路上跑步,做早操。熱了便回屋去洗臉(那時父親總會用手摸我們的頭看是否淌汗了,如淌就算鍛煉好了,沒有,還得再跑一下),然后拿著語文課本去朗讀,讀聲要洪亮,吐字要清晰。讀一個半鐘頭,回到老屋對面的小磚房里寫假期作業。有時一進去,我和弟弟如釋重負,把門倒關了耍鬧,聽到父親腳步聲,又趕緊鴉雀無聲地做作業。就這樣,一天天把假期度完。
于是,我們便盼著父親快走。父親走了,媽媽就會放我們去“小白房子”用彈弓打谷雀子,或是到“機械閘”下的溝里摸魚。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一天天長大。父親照常每個假期回來幫我們補習功課。讀完小學五年級,我和弟弟以優異的成績考進陸一中。但父親絲毫沒有放松對我們的嚴格管教,每每送我們到校,都嚴肅叮囑:“學習最重要,你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讀好書。”
初二時,父親發現我們英語成績不太理想,便試著輔導我們。但他學的是俄語,只好以百倍的毅力,堅持自學英語。“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他的輔導下,我們英語水平逐漸提高。
六年的中學生活轉瞬即逝,我和弟弟考取省內重點大學,父親的教誨常響在耳邊。我和弟弟的大學生活極其勤儉。冬天穿著父親寄給我們那種他登山穿的“翻毛皮鞋”,戴著媽媽織的毛線手套。大學四年,父親每隔一周便要寄封信給我們,信封是父親用很厚的牛皮紙做的,沉甸甸的,有時一拆開里面還會掉出幾張十元的鈔票來。信上寫的是些鼓勵我們加倍努力的話。字里行間,折射著父親望子成龍的心愿。父親每次到學校看我們,都身著藍布工作服,肩挎帆布包,手捏長把黑雨傘,還刻意把胡須剃得很干凈。找到我們后,帶我們到學校附近的小館子坐下,點幾個我們喜歡吃的菜。父親默默地低著頭,一個勁兒夾菜給我們。吃完了,他又嘮叨些專心學習之類的話,然后便徑自去了。
四年后,我們步人社會。分工作時父親根本不考慮走關系的事,他鄭重地說:“我這輩子是不求人的,不會走后門,凡事你們多靠自己。什么工作都是人做的,重要的是把每件事情做好,接下去該走什么樣的路,自己選擇。”于是,我們被分到最基層山鄉農村工作,每日里上山下村串戶,田邊地角踏遍,真是好辛苦好累。有時幾個月回家一次,曬得臉皮黑里泛著紅光。但父親并不同情我們,他寫信說:“這正是鍛煉你們吃苦耐勞的好機會,你們年輕,不吃點兒苦怎么行!我五十多歲了還不照樣在登山,每天還要走幾十公里山路!”我們聽了,縱有千苦萬苦也難張口了,漸漸地,習慣了基層生活。我每日除了工作還背著畫夾,去畫一些松林村落、鳥石山水。仔細觀察和體驗農民的生活,感受他們的質樸和憨實,細細品味那份濃濃的鄉情。隨著我們的成家立業,漸漸懂得了父親的話。知道現在我們擁有的一顆完整獨立、忘我的事業心和那種對待困難的堅強毅力是與父親長期的諄諄教誨分不開的。我們沒有了對家的依戀,我們對事業一往情深,我們耳中無時無刻不在響著父親的聲音:“你們少操心家事,努力干好工作是大事。”
終于有一天,父親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帶著頗具榮耀的無數榮譽證書,永遠回來了!這個工程師,除了鋪蓋行李,就帶回一大箱存書和繪圖工具,加上一捆他認為能留做紀念的得意之作——大大小小的圖紙。父親開始閑下來,閑下來的他不知所措,做什么呢?他不擅長閑暇度日。我們開始教他釣魚,這個時候,父親好像個孩子,不時地對我們問這問那,我們心中不禁暗暗好笑。我們的子女也圍著父親一個勁兒地喊著“爺爺、爺爺”,而父親卻又重復著原先教育我們的方法去教育他們。有時一個小學三年級的數學題會弄得他頭腦發漲,但他總不肯認輸。他兩鬢斑白,行動漸漸遲緩。他真的老了!當我們去上班,他會裝得很平靜地問一句:“幾時回來?”再也沒有了那些極其嚴厲教訓人的詞句了。
我們現在已成父親,在重復父親原來教育我們的樣子,這是多么神圣而神奇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