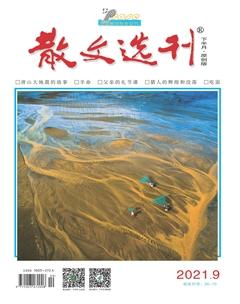夢里夢外
張東曉

曾經有過一位很要好的朋友,那晚我夢見與她在學校外的水壩邊游玩。
清風徐徐,水波不興。原野安靜如畫,連一聲蟲鳴都聽不到。我和她手牽手,依靠在水庫邊的欄桿上。那情形,正如宋詞中寫的“滿目山河空念遠,不如憐取眼前人”。第二天一醒來,我就急不可待地想告訴她。在她樓下等了許久,只等來她一句“早上好”。她的語氣淡得如初夏的天空,落在我的心里變成了寒冬飛雪。
我已很久不曾夢見她,也已很久沒有她的消息了。時光悄然過去了15年,以至于現在我都不確信在水庫邊那一日的溫柔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只是我的一個夢境。生活越雜亂就越顯得不真實,我曾懷疑我的記憶出了問題。因為不僅是她,就是那個自己生活了四年的城市,自己卻好像從來未曾去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而自己卻拿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明。
記憶中,她帶我回過承德,那是個美麗的城市,在城外的大山之間,時刻都在上演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的浪漫。
他們是一個小女孩和一個大男孩。
小女孩是我們本家的孩子,大約十來歲時在她家前面的水坑里淹死了。聽說有人落水了,半村的人都圍了過去看熱鬧。我也在人群之中。我看見有人把她從水坑里撈上來。我看見她被放在地上,赤身裸體。那應該是我第一次見到女性的身體,在喧囂的人群中,她被人舉起,倒立著,拍打腹部、胸部,水從她嘴里淅淅瀝瀝地往外流。她母親哀號著,從坑邊往村外跑,邊跑邊喊她的名字,想把她尚未走遠的魂魄喊回來,但終歸無濟于事。后來一天夜里,我冒雨從縣城往家趕。走到她家門前時,鬼使神差地跌了一跤,差點滑進坑里。在那個雨夜,我仿佛丟掉了魂魄,落荒而逃。現在那塊區域,依然是我生命的禁地。大男孩也是我本家的,比我小上幾歲,但卻長一輩。他是在南方工廠干活時被電打死的。當時本家派了幾個有面子的人去跟廠里要賠償,父親也跟著去了。父親回來之后,帶了當地的兩瓶豆腐乳。乳白色的那種,看起來毛茸茸的,很是疹人。現在我還對豆腐乳有心理的抗拒,大抵就是那時留下的陰影。我在村里向來是個悶葫蘆,與年齡較小的他幾乎沒有交集。但有一次,他欺負一個小女孩,被我用暴力阻止了,為此,我還吃了父親一頓坡鞋板子。
前幾日,我跟父母說我夢見了魚魁。
魚魁是我們村一個人的外號,他特別喜歡捕魚,撒網、拉網、扒網,等等,各種漁具用得得心應手,于是也就有了這么個外號。我父親也喜歡捕魚,是魚魁的學生。小時候家里窮,寫作業的本子和鉛筆都是用雞蛋換的,根本沒有錢買肉吃。怎么辦?好在那個時候坑里、河里水都是滿滿的,有水就有魚。父親他們就跟著魚魁到處跑。尤其是逢年關,更是徹夜不休息,因為魚不僅可以吃,還可以拿到集市賣。那時鱔魚比較貴,父親就帶著母親到處下網捉鱔魚。白天父親在附近村上轉悠,尋找下網處。鱔魚與其他魚不一樣,它們不喜歡水多的地方,而是喜歡水洼子,并且多在夜里出來覓食。晚上天一落黑父親就帶著母親下網。那種網猶如連環套,約兩三米長,往水洼里放上幾道,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天門陣”,鱔魚只要進去,肯定出不來了。第二天天不亮他們就得去收網,若是去晚了,就被人收了去,白忙活了。一到冬天,父親母親就白天趕集賣魚,晚上下網捉魚,跟打仗似的。
“你咋夢見他了?”母親的反應有些大了,這讓我很是意外。就聽母親繼續說:“他都死好幾年了!”我一聽,驚聲說:“他死了嗎?我怎么記得他還活著?”我不確信母親說的,就把目光轉向了父親。父親嘆了口氣,點了點頭。現在我才確信他是真的死了,而且如母親說的,已經死了好幾年。那我為什么夢見他?風馬牛不相及的世界和人,竟然在夢里相遇。父親沉默了一會兒,沉聲說:“你別看他整天沒個正形,但他是個好人,心好著呢。”父親出了口氣,又說:“你還記得你上大學那年的學費吧?家里錢不夠。我看他剛賣完麥子,就問他借錢。他知道你上大學,二話沒說,就拿了兩千塊錢給我。”說完父親轉身回屋了,許久又傳出一聲輕嘆。
這事兒我以前也聽父親說過,只是現在聽來,別有一番滋味。他死的消息,父母也應和我提過,許是我潛意識里不相信或者不愿接受而已。他應該還在村里,披著條破棉襖,背著魚簍子,到處捕魚才是,因為他是魚魁。魚不會死,他怎么會?
我最喜歡的夢是回到小時候。院墻外的竹林,正爭先恐后地往外發芽,有些不安分的竹竿芽子也都發到馬路上了;竹林外的麥田,綠油油的,都綠到了天邊……我真想走進當初的夢里看一看,看看現在的自己是否與夢中一般。
前一段時間,父親告訴我,院墻外的竹林被鏟除了。因為村里要電路改造,竹林剛好在線路上,又那么高那么大一片,不得不削平。父親像是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情,那一片破竹竿本來也沒有什么用,但在我心里卻是夢被折斷的苦楚。我關于家鄉所有的美夢都破滅了。竹林沒有了,我的“夢”還有依托嗎?我想起在竹林不遠處的小廟,那是村里祭祀的地方,無論紅白喜事,人們都要在小廟前放上一掛鞭炮,燒上一沓黃紙,敬上一把清香。這間破舊磚房,孕育了村里人的夢想,也容納了村里人的靈魂。它離拆掉還遠嗎?
大黃是我們家養的一條狗,渾身長滿了黃毛,長得又高又大。小時候我和姐姐常騎到它身上,它也不生氣,就是汪汪地干叫。很多時候,它都是跟在我們屁股后面,是我們為數不多的玩伴,后來它被人藥死了。父親就把它埋了,從此,我們家再也沒有養過狗。前些天,女兒和我說她想養只狗,我就想起了大黃,想起和它一起曬太陽的情形。一切恍如昨日,恍如從夢中走來。
人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走過的路與將來的路,都像是一場夢的延續。但無論如何別忘了,夢醒后要繼續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