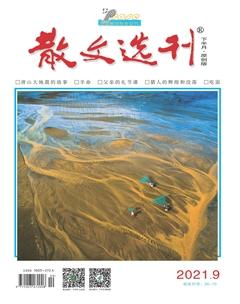寺溝之冬
畢華勇

冬日,我又一次走進吳堡縣的寺溝村。在陜北,冬天的黃土地上,那些夏日里瘋長的樹木草叢都變成了褐墨色,時常飛過一群鴿子或麻雀,偶爾還有些不知名的小鳥在草叢里跳躍、歡呼,就像一幅濃墨的國畫,氣勢磅礴。溝壑丘陵、山川河流將個性大開大放地張揚。太陽升起來,將一層薄霧推開,所有的村子露出祥和與溫暖,天藍、土厚,人在其間。
寺溝村亦如此,神秘而內斂,讓人不勝其煩地走來,靜聽、靜觀。
我就這樣走進了柳青文化園。
園口,巨石是一部大書,橫豎相疊,厚重如山。這樣的門很少見,站在門前,你便會思緒萬千,這樣意味深遠的門,無論是讀者,或者是目不識丁的老農,只要看見它,就會明白。在你一生所經歷的人和事中,有些注定要遺忘的,有些則會刻在腦海深處。寺溝人最引以為豪的便是從門里出生的柳青,一個大寫的“人”給我們留在記憶深處的精神財富,就像如書的巨石,隱藏著那些智慧的文字,要讀懂他,必須心懷敬仰和虔誠,要有宗教般的儀式。
寺溝的冬季,安靜得猶如一泓水,神秘而內斂,那條曾經潺潺流淌的河水,已被瘋長的水草掩蓋,在寒風的吹打下,水草褪去了綠色,在河道中悄悄地等待著又一個春天。寺溝的村民,三三兩兩地在“文學之門”前見證著南來北往的人,操著各種腔調探詢或談論有關柳青的點滴,也許他們此刻才明白,柳青不僅僅是個念書識字的人,而是會寫文章的標桿,他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個“大人物”。
是的,這個“大人物”是我們當代文學界的靈魂,也同樣是精神上的一面旗幟。
寺溝的山和陜北所有的山一樣,無規則地連著,一條溝一道梁排列開來仿佛又有順序,柳青文化園就在這山溝中,從門口走進去,一條上坡的路用本地大大小小石塊鋪就,一眼望去,20多個院落,77孔窯洞以它特有的元素和風格靚麗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右邊,青石刻像順山勢逐漸攀升的“作家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些曾在陜北工作和生活過的全國有影響的作家,還有陜北籍作家,在文化園里讓人們駐足,使人們從記憶深處懷念他們的輝煌以及他們對年輕人的影響。上臺階,沿著寬窄規律、彎折有序的石路走,從“柳青故居”開始,我尋找園中主人生活的痕跡,仿佛在某一個空間,某一個時間,我與柳青相遇,在米脂呂家鹼那個穿著大襠褲、黑棉襖的鄉文書,就坐在碾盤上,抽著旱煙,說著他的人生奇遇,和一群老漢后生掰手腕耍輸贏,雖然是短暫的遐想,亦回味無窮。我就是這樣聽呂家鹼老漢講述的,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愛的人,在人間煙火中,活出了自己。
作為后輩,在這個冬季專門來看這位“老人”的故園,陽光落入寺溝窯洞的院子,無風的冬季顯得如此暖和,這里所有的文字、書籍,還有作家墻,仿佛像陽光一樣熾熱。我知道自己的軀體激蕩著不一樣的情緒,前輩們一雙雙睿智的眼睛,越過光陰、山川、河流,給你和我人生與書寫的啟示。仰望明天,尊敬文學,如在夜間,透過窗紙,我能看見一盞燈光……
這園子就是一個文學的大觀園,也是陜西乃至中國文學史的縮影,無論誰走進這個園子,都必須仰起頸項,望著柳青,他會給你傳遞一種信息,像和鄰家一個老頭敘說著生活的當下、未來。于是,我感覺到,自己有一模一樣的心,想把一扇天窗敞開,深度地去理解寺溝出生的柳青,從那個窯洞,那個院子一步一步走出去,以愛和無畏的名義,開始《創業史》的征程。
柳青給我留下的遺產太豐富、太厚重,當那些文字對我的心有暗示時,我多么夢想有一刻自己能走進文學的神殿,去領悟、去朝拜,去把人世間所有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把春風與嫩綠、夏日與生長、深秋與落葉合在一起,從所有黃土山的回聲里,尋找屬于自己的文學。我知道,這很難,寺溝的這個園子,以一種精神的張力,開啟了陜北人文化自信的啟幕。
碑石是安靜的,文字是安靜的,而有一種巨大的沖擊力,使我滾燙的靈魂與寺溝之冬燃燒著。
我覺得從走進這個園子開始,已經與梁生寶、梁三老漢、郭世富以及石得富、李銀風、金樹旺們拉話了,這種相遇,有久別重逢的感覺,我早已俯下身來,把心交給了大地。在這大俗大雅的人間,柳青文化園為我們精心營造了一個溫馨的家園。
這是2020年寺溝的冬,我從柳青文化園又一次走過……有了這些,一生一世活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