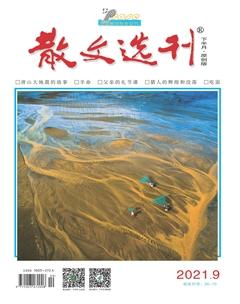微弱的光亮
任天軍
我的奶奶,把給鄰居端飯當作一件大事。要選擇最大的碗,裝得滿滿的,如果有肉,還要多挑幾塊放進去,這樣才顯得心誠。要在客人沒有端碗之前,安排家里的人端過去,以示對對方的尊重。到鄰居家,要把碗恭恭敬敬地呈給長者,還要說一些“做得不好,嘗一嘗”之類的客氣話。鄰居家吃完飯,會在碗里放一個饃饃,或者盛一碗面,同樣由大人還回來,分享一些生活中的樂趣。
這個習俗,一碗熱氣騰騰的飯,繚繞著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扶助、友善,也延續著一種質樸、美好的情義。
饑饉的年月里,能聞到葷腥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鄰居老楊家來了親戚,佝僂著腰的楊奶奶,給我們家端來一碗干拌面。那是一個粗瓷大碗,上面小山似的堆著洋芋、蘿卜和肉丁做的臊子,還有一坨鮮紅的油潑辣子。清湯寡水的腸胃,根本無法抵御那碗飯帶來的巨大沖擊,那氣味、形狀和色彩,讓人噴嚏不斷、涎水連連。我們的一雙雙目光變成了筷子,都想隔空撈取。不過,吃飯是有規矩的,奶奶端著碗,象征性地嘗了一點,就把碗遞給父親,父親粗大的喉結動了一下,隨便扒拉兩口,又把碗給了母親,母親負責給我們分配。我迫不及待地想用手抓,卻因姐妹們戒備森嚴無從下手。最后分到的一點飯食,來不及咀嚼就被猛烈蠕動的腸胃吸了進去。
我后悔自己吃得太快,舔著嘴唇,眼巴巴地望著小妹,她的小碗里,還有半碗飯,油潑辣子均勻地鋪開,微黃細碎的油花漂在上面,那是一團炫目的火焰,灼燒著我焦渴的心。此后多年,味道和顏色在我的感覺系統中建立了深刻的聯系,小妹碗里的油潑辣子,宛如瑰麗的花朵,長久地盛開在記憶的天空中。
老楊家的那碗飯,因為有辣椒熱烈的紅色,我的感覺中,凡是帶有葷腥的飯菜,那香味都像火苗子一樣上下躥動。那么,青菜蘿卜的香味就是粉紅的,瓜果的香味是桃紅的,莊稼成熟的香味是橘紅的,燒洋芋的香味是焦黃的,而母親的體香是乳白色的,父親的汗味是古銅色的。還有,草木的清香是嫩綠的,野花的香味是淡紫的,土地的氣息是深灰的,雨水的味道是藍色的……這種關聯,讓我深深地著迷。世間萬物總是有著隱秘的聯系,這種聯系,蘊含著豐厚詩意,尋找和捕捉這種詩意,心靈會有如沐春風、如淋細雨的感覺。
鄰里之間的那碗飯,用的都是尋常的食材。洋芋、蘿卜、小蔥、芹菜,來自自家的田間地頭,施的是農家的羊糞牛糞,吸納星月光輝,吞吐山野氣息,雨露滋潤,清風撫摸,坦蕩自在地生長,散漫而壯碩,有一種清新自然的味道。這樣的飯菜吃起來讓人神清氣爽,耳聰目明。那些做飯的手,布滿老繭,有時候并沒有洗干凈,或許沾著灰土和汗漬,但那些手對待食物總是小心翼翼,極其虔誠,絲毫不敢玩弄和褻瀆;每一種糧食和蔬菜,從一粒小小的種子進入泥土,而后破土、發芽、長葉,到收獲,都離不開手的操持和侍弄。手,見證了農作物成長的艱難,手,帶著一種莊嚴神圣的情感采摘和加工食物,那樣的食物,就不僅僅是飲食意義上的飯菜,而是飽含著濃郁愛意的心血之作。還有那只用來盛飯的碗,無論是簡陋的木碗、石碗,還是樸拙的陶碗、瓷碗,都裝滿了綿長而細微的情思,這些情思,傳承了千年萬年,在一代代人的心里埋藏、發酵和擴散,氤氳出一幅幅溫暖的鄉村場景。
互相端一碗飯,是回贈、是分享、是友好,也是彼此之間的問候。平時雞毛蒜皮的一點摩擦,一碗飯端過去,說明人家不計較這些,對方也就心氣平和了。端過去的那碗飯,鄰居家可能每人只吃一口,但端過去的飯不在于多少,是看得起對方的表現,心中就會升起一種感激之情。一個村莊的幾十戶人家,隔三岔五總會有親戚來訪,因此,村莊的巷道里,總能看到從這家到那家端飯的情景。每戶人家,飯菜的做法各不相同,精細程度也不一樣,但那種樸素、厚道、真誠的心意是相同的。
如今,那一碗帶著泥土氣息的飯正在被淡忘。農村里陸續拆掉了老房子,搬進了新居室,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寬敞明亮,住在樓房里的人,卻不知道自己的鄰居是誰,更不要說端飯了。防盜門固然比柴扉堅固,但門內沒有了雞犬之聲,門外沒有了牽牛花和蜂蝶,進進出出的人都步履匆匆,甚至憂心忡忡,關門的同時,也關閉了彼此之間的真心和溫情。
飯雖然還在吃,但家里動煙火的次數越來越少了,街頭的小飯館熙熙攘攘,豪華的大酒店人流如織,年輕人更是足不出戶,點一份外賣就是一天。我們常常請別人吃飯,也接受別人的吃請。但請或被請的飯菜里,卻吃不出原來的味道,都有一種明確的“目的”在里面。城市的味道是濃烈的,又是紛繁蕪雜的,甚至是混亂刺鼻的。在城市里,我的嗅覺失靈,視覺模糊,心思散漫,聯想枯萎,再也沒有能力建立起味道與色彩的聯系了。
閉上眼,那一束來自遠古的微弱光亮,應該不會消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