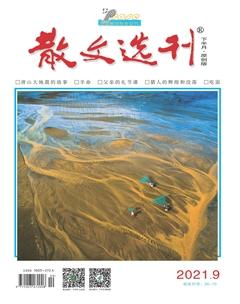懷念
易格滋
父親走后,母親一人獨守著老家的屋院,拒絕了我要她來城里一起住的建議。我說,你守著這院落,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母親指著趴在她腳邊的黃貓道:“有它Ⅱ阿!”這只貓是父親走的那年冬天流落到我家院子的,十余年來它享受著跟母親相同的食宿待遇。
田地征用后,不能種麥種稻的母親,喜歡上種黃豆、白菜、空心菜、蘿卜等,松土、鋤草、施肥,實在沒事兒,她便在那塊土地上晃悠,她那時大概覺得自己像個女王,她想這樣就這樣,想那樣就那樣。母親嗅嗅空氣里的土腥味兒、青草味兒,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四月底爬滿院墻的金銀花綻放如一片初雪,端午節(jié)還沒到,池塘邊那棵她從老宅基地移植過來的,已有十多歲的梔子樹,一片油綠的葉子里浮起潔白的花骨朵,初夏的風吹得骨朵們顫顫悠悠,母親嗅嗅香氣,得意地攤開雙手道:“城里有它們嗎?哈!沒有吧?我當然不會去你那兒。”
菜地在屋子后面,地是人家蓋工廠剩下的“邊角余料”,形狀也是曲里拐彎,母親一鋤一锨開墾出來。冬天里,蘿卜、白菜,青蔥一片;春夏之際,黃瓜、番茄、南瓜、冬瓜、西瓜、香瓜,綠藤紫莖,滿地瘋長,姹紫嫣紅。田野里的野兔、野雞和各種小獸,紛紛趕來會餐。母親從不在地里下農(nóng)藥,也不驅(qū)趕它們,久之,那些野物不再懼怕她,見她走來,頂多讓一讓。母親蹲在那里鋤草,小動物吃一口青蔬,望一望她接著吃。菜蔬吃不完,先是送鄰居,再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將菜蔬送給進城務(wù)工的農(nóng)民。
母親娘家貧窮,窮不當長子,富不做幺兒。母親是長女,下面有四個弟妹,童年時她牽引著一頭黑水牛,放牧到坡崗、河灘,狗尾巴草、絲茅草纏著她的褲腿,荊棘和野花粘滿她的衣服。放牛多年也不知“牛”字怎么寫,母親說:“一個字,兩個叉,它認識我,我不認識它。”母親嫁過來,靠種地為生。
“這老家伙肯定怕嚇著我,一次也沒回來過。”母親說父親走了十余年,居然從沒夢見過他。我不太相信母親的話。很可能,父親在某個漆黑或皓月當空的夜晚,從磙子河堤腳出發(fā)(父親安眠于磙子河邊),像生前那樣擺著兩只手,踩著鋪滿星光的小路,路過曾經(jīng)耕種過的田地時,他在田頭坐了坐,他吸著煙,煙頭在夜氣里明明滅滅。他甚至在與母親打過架的那塊水田邊,默默站立了一小會兒,輕輕地自語道:“別記恨我,主要是那時太窮了,整天愁吃愁穿,心里煩得要命,才忍不住動手打了你……”父親回到老家,院子里的桂花樹和樟樹,葉子上沾著露水,濕漉漉的,像下過一場小雨。父親腳步極輕地走到母親的窗口,透過玻璃他看到了熟睡的母親,只是母親不知道這一切。
母親曾在一個夏日午后對我抱怨:“你父親這個死鬼,把我忘了。”隨后又自說自話:“唉,他就是那樣一個人,怕打擾任何人。”其實母親也是如此,她甚至在臨走前的那個夜晚,對守護的我們說:“人都是要走的,只是,我舍不得它們。”她說的“它們”,大概是指院子里的植物、地里的菜、那只黃貓。
沒有父親和母親的屋院,寂寞如一只空洞的蟬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