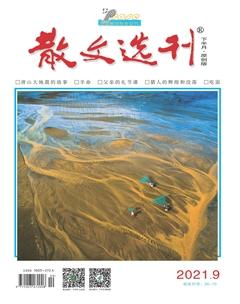也學牡丹開
惠永臣

低矮的、樸素低調的苔蘚,在別人眼里并不起眼,偏偏是我非常喜歡的。
苔蘚低矮,甚至比大地上任何一株草都要低矮,仿佛是植物世界的侏儒,和那些灼灼艷艷的花朵、挺拔俊美的大樹、隨風擺動的蘆葦們相比,著實不怎么起眼。苔蘚謙卑地生活在我們的周圍,從不和人類擠占空間,它愿意選擇人不常去的地方去生長,譬如墻頭、屋腳,山野里的石頭上,野草的根部,樹干上。
“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很小的時候,我讀到了袁枚的這首詩,便喜歡上了苔蘚。那么樸素的苔蘚,米粒般小的苔花,竟然也學牡丹開。牡丹是花中的貴婦,人人都艷羨它的美艷,但苔花并不覺得自己卑微,要開出自己的花兒。其實,它開的并不算花,它們屬于“最低等”的高等植物,屬無花、無種子、以孢子繁殖的植物。雖這首詩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但并不影響我對它的喜愛,它的美讓我迷戀。
苔蘚對空氣指標的要求極高,敏感度極強,是監測空氣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當人類對所處環境中空氣的污染程度還沒有感知到時,苔蘚已經提前告訴我們了,然而大多數人沒有細心地觀察過它們。一次,我約朋友去山里看苔蘚,被他狠狠地回絕了一句:“苔蘚有什么看頭?”他的認知竟然如此簡單粗暴,不知看似簡單的事物,往往有著復雜的內里和不為人知的道理。
那一年,外地的作家相約到我單位所在地的磁窯遺址去轉一轉,我作為向導,特意推薦他們在看磁窯遺址的同時,不要忘記了去那里的山上看看苔蘚。那里有滿坡的石頭,或臥或立,或大或小,但每一塊石頭上,都披著一層金黃金黃的外衣,像金縷衣一般的漂亮。一到山腳,仰首而望,一片的金黃色,燦爛得很。他們興奮得要命,忙掏出手機拍照。我提醒他們,不要急,慢慢欣賞,要俯下身子,與苔蘚近距離地接觸。你越交心,苔蘚越能給你呈現它的美。我們從山腳下,慢慢地往山頂爬,每一塊石頭都不放過,看有著黃金般的色彩的苔蘚,在干硬的石頭上,卻生長得這么恣肆,像誰刻意撒下的金箔。滿坡的金箔,迷人的金箔,閃爍著你,誘惑著你。
當然,這樣壯觀的苔蘚,平常是難以見到的,但總還是有苔蘚會生活在我們周圍,就看你留意過它們沒有。我們家的墻頭上,也有不錯的苔蘚,墨綠色的,趴在墻頭,一抹一抹的,密密實實,擠擠挨挨。一場雨后,它們不約而同地從墻頭長了出來,樸素得要命,但你貼近它們,再貼近它們,會看到,一根一根的,像針插在墻皮里。它們平常得和塵土一般,誰會在意呢?我曾經用手指摳了一下,它們就帶著泥土,來到了我手上,也不驚乍,也不悲戚,猶如平常,這也太淡然了。過不了幾天,那一塊墻皮上,很快又長出一層苔蘚,像破損的皮膚長出了新的,依然那么密密匝匝的,螞蟻走在上面,像走在絨毯上,愜意得很,伸展的腿腳,懶散地不想走了,想躺在上面曬太陽。偶爾有鳥雀也會落在上面,用細小的喙不停地啄食,而苔蘚并不會因為它們的到來而受寵若驚,仍然是平平淡淡,安然處之。
行色匆匆的我們,不妨學一下苔蘚,或許會活得更快樂,更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