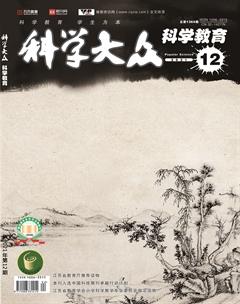圖像在高校中國史教學中的價值與運用
羅權
摘 要:圖像是歷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近年來圖像史學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和學術增長點。高校歷史教學需要緊跟學術前沿,故圖像的使用也應當得到充分重視,特別是古舊地圖、各類圖畫、老照片等。教學中對圖像的運用要對圖像所反映的歷史真實性進行考辯,對圖像所反映的歷史進行深入挖掘,注意圖像選擇的貼切性,并在圖像與文字之間的配比中尋求合理平衡。
關鍵詞:圖像; 歷史; 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41? ?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6-3315(2021)12-133-002
近代以來的史學變革浪潮中出現了眼光向下的視角,提出歷史的研究不應局限于政治軍事的宏觀歷史,也不是研究帝王將相的家族史,而開始注重普通民眾社會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官方文獻的記載中,這類材料往往受到忽略甚至被刻意涂抹,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一些障礙。因此要推動史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新史料的挖掘是必由途徑。高校教學與中小學的教學相比,有著其獨特性,即不僅要向學生傳播正確的知識,更要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主動探索問題的能力,掌握一些初步的研究方法,即不僅要授人以魚,更要授人以漁。因此,高校歷史教學應緊跟學術界的研究前沿和關注的熱點,培養學生更多關注學術發展的方向,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近年來圖像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也作為一個要點在高校歷史教學中得到更多重視。
一、圖像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史料是歷史研究最基礎且重要的部分,史料的深度挖掘體現了歷史研究的嚴謹性和科學性。歷史研究中的史料形式豐富多樣,概而言之可分成文字、圖像、實物、口述四大類,其中實物可轉變為圖像,口述可轉變為文字[1]。故而廣義上講史料即可概括為文字和圖像兩大部分。關于圖與史的關系,我國古代史學家多有精辟論述。唐人張彥遠在《論畫》中說:“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指出圖像具有可以更清晰、直觀展現事物面貌的特征,故應得到充分重視。陳繼儒在《三才圖繪》中稱:“古之學者,左有圖而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認為圖像與文字,是兩把治學之匙,二者不可偏廢。鄭樵在《通志》對于圖像和文字的辯證關系有著精彩論述: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憲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廢者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執左契。后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寘之行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2]。
也即是說圖像與文字不僅同樣重要,且相輔相成,是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在治學之中需要充分重視。正是基于這一考量,中國古代史學書寫中圖像與文字一起得到運用,有“左圖右史”的說法。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經》被認為是一本述圖之作,即先有圖,而又以文字對一幅幅圖進行說明,只是這些圖是地圖,還是光怪陸離的圖畫,則仍有爭議,而山海經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則一直以來認為被低估了[3]。漢唐時期又流行起了“圖經”“圖記”“圖志”類文獻,以更清晰呈現各區域的歷史地理面貌。較早的有《巴郡圖經》《廣陵郡圖經》《冀州圖經》《齊州圖經》《洛陽圖》《湘州圖副記》《江圖》《幽州圖經》《隋西域圖》《并州總管內諸州圖》等。到了隋大業年間,普詔天下諸郡調查地方地理情況,繪制地圖并配以說明以上于尚書,使這類圖文結合的圖經類文獻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其中包括《周地圖記》(109卷)、《隋諸州圖經集》(100卷)、《諸州圖經集》(100卷)、《隋區宇圖志》(129卷)等大部頭文獻[4]。此后的唐、五代、北宋時期,地方府州定期編修與造送圖經仍是定制。但是相對于文字文獻,圖像文獻的保存和翻刻、流傳均面臨更為巨大的困難,故這些圖經文獻中的圖能夠流傳下的并不多,經常是“經存而圖亡”,這也就更加凸顯出了圖像文獻的寶貴。
在近年的研究中,圖像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開始逐漸受到學界推崇。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指出,圖像作為歷史證據,在心態史、日常生活史、物質文化史、身體史的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5]。特別在近現代史的研究中,圖像的重要性尤其明顯,大量的畫像、雕塑、照片、電影、電視等圖像資料,是研究近現代史所不能忽視的史料。曹意強教授曾指出:“百年之后,人們通過如此的圖像實錄在理解21世紀初的歷史,其震撼力必定是文字記載難以比擬的[6]。”在古代史的研究中,圖像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古代繪畫作品、古地圖、雕刻等材料是我們研究古代史的重要史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趨向于通過照片、畫像、地圖等圖像文本進行歷史書寫,以增加學術作品的可讀性。可以說以圖入史、以圖證史、以圖佐史的圖像史學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經得到普遍認可。緊扣學科前沿方向,展現學界研究最新成果,引導學生熟悉和掌握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高校歷史教學的一個重要要求。因此,高校歷史教學也應當更為重視圖像史學在教學中的應用。
二、圖像在歷史教學中的應用
圖像內涵豐富,包括各種圖形和影像。古舊地圖是圖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有著悠久的地圖編繪史,《管子》中專列“地圖篇”,對地圖在軍事作戰中的關鍵作用、地圖應包含的內容進行了論述,可知在當時地圖的編繪已經達到一定高度。現存最早的實物地圖——天水放馬灘地圖已經有了3類7種注記內容和6類10種注記符號[7]。年代為西漢時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包括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等多類型地圖,東漢墓葬中也出土了寧城圖、繁陽縣城圖兩幅壁畫地圖,可知漢代地圖的形式已經較為豐富。西晉時裴秀完成了目前可知最早的一部歷史地圖集《禹貢地域圖》,并指出地圖應有的六種基本要素,即“制圖六體”:分率(比例尺)、準望(方位)、道里(距離)、高下(高程)、方邪(坡度)、迂直(實地高低與圖上距離換算),說明制圖的理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度。兩宋時期編繪了不少全國性地圖,其中有部分保存至今,包括《唐十道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禹跡圖》《九域守令圖》《地理圖》《輿地圖》等。明代流傳下來的古舊地圖更加浩如煙海,除了有《楊子器跋地圖》《古今形勝之圖》《廣輿圖》《歷代地理志圖》等全國性的地圖外,大量方志文獻所附的疆域圖、城池圖為我們了解明代地理面貌提供了重要參考。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達中國,在傳教的同時也傳播歐洲在地理大發現中獲取的世界地理新知識,并與一些中國文人一起繪制了一批地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坤輿萬國全圖》,對中國的地理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8。西方測繪技術的傳入,為中國地圖編繪從“計里畫方”圖、山水畫圖等傳統方式繪制的輿圖,向近代實測地圖邁進奠定了基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帝令西方傳教士分赴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廓,以西方地圖測量法進行實地測量,并令清廷派出干員協助辦理,地方官則給予充分配合,供應一切需要,至五十八年(1719年)完成了《皇輿全覽圖》的編繪,這是中國第一部經過現代方法實地測量和繪制而成的實測地圖。乾隆年間又對哈密以西地區進行了實測,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訂正補充,形成了乾隆《內府輿圖》。這兩部全國實測地圖對了解當時中國的地理面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近代以來,十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等大比例尺實測地圖逐漸豐富起來,使我們能夠更細致了解當時的歷史地理面貌。相較其他圖像類文獻,古舊地圖所包含的歷史信息更為豐富,因而其在圖像史學中也占據著重要地位,在歷史教學中理應受到充分重視。
圖畫是圖像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紙畫、絹畫、帛畫、畫像磚、壁畫、銅鏡畫、陶瓷畫等類別,其描繪內容包括仙佛鬼神、人物傳寫、宮室庭院、山水林石、花鳥蟲魚、果蔬藥草、小景雜畫等,具有直觀、形象的特點。其中不少內容直接反映了歷史情景,如漢代畫像磚所反映的漢代生活場景,“苗蠻圖”能夠反映清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服飾裝束和生活面貌。另一類圖畫雖然不是反映真實的歷史,但亦可視為“文化的歷史”,如仙佛鬼神類圖像,對了解古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宗教觀亦有較大參考。圖畫在歷史教學中應用廣泛,特別是宗教史、藝術史、生活史等專題中尤為重要。
自攝影技術發明后,老照片成為傳播歷史的一個重要載體。圖畫會有夸張、不實的成分,照片則能夠較為真實記錄歷史的真相。近年來,老照片成為歷史呈現的一個重要載體。1996年底由山東畫報出版社策劃的《老照片》叢書推出以后,就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歡迎,曾經創下單個專輯超過30萬冊的銷售量,也得到了史學界的密切關注。在近年出版的一些重要歷史著作中,老照片也得到充分采用,可以更清晰表達歷史情景。在歷史教學中,老照片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深化對歷史的認知,補充一些文獻所不能表現的歷史場景。
三、歷史教學中的圖像運用應關注的問題
首先,需要對圖像所反映的歷史真實性進行考辯。圖像反映的歷史不僅有真實的歷史,也有夸張、虛構的歷史,甚至某些場景還會與歷史事實相反,在教學中要尤為注意。例如信息量較大且相對真實的歷史地圖,也與歷史真實有所差距。傳統方式繪制的寫意地圖、“計里畫方”圖的科學性、規范性都略顯不足,存在地理要素選擇主觀、地名相對位置不準、河流走向不準、湖泊標注隨意等問題。近代實測地圖雖然準確性超過傳統輿圖,但由于當時相對落后的測繪技術,以及投入測繪的人力物力不足,與現代衛星定位測繪的地圖仍有較大差距,依然存在不少錯誤,在教學中也要留意。照片雖然最能反映歷史真實,但因其只能反映一個歷史的片段,反映的是碎片化的歷史,若不加以細致考量,則會以偏概全,如僅以一張清末富家人的晚餐照片,就說當時生活條件好,顯然是不真實的。且照片也存在不少造假的行為,如曾經轟動的“周老虎事件”,最后就證明其照片是偽造的。圖畫的真實性就更需要仔細考究了,若隨意使用,不僅不能達到深化教學的目的,還可能會傳播錯誤的歷史,以至于誤人子弟。
其次,需要對圖像所反映的歷史進行深入挖掘。圖像之于歷史研究有幾種方式,一是以圖入史,二是以圖證史,三是以圖傳史。在歷史教學中,前兩種方式也都可以得到充分采用。王也揚在對“老照片”熱潮的評論中就指出,雖然老照片歷史價值很大,但在許多關于老照片的出版物中編纂者多文學人士,歷史闡釋不足,不免缺憾[9]。在歷史教學中,圖像的運用不僅僅是簡單作為史論的佐料,更應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歷史內涵,引導學生通過圖像更加深入認知歷史、分析歷史,這樣才能有助于教學的深入。
第三,注意圖像選擇的貼切性。圖像的運用是為了達到教學目的,故對它的選擇要進行仔細考量,以貼近教學目標為要,如果照片不切題,不僅不能講清知識點,還會誤導學生。同時,圖像的選擇要根據教學對象的特點進行適當調整,這樣不僅可以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還能促進學生進一步深入思考,若選擇不當則有可能引起學生的厭惡和反感。
第四,注意圖像與文字之間的合理配比。無論圖像或文字的運用,其目的都是為了完成教學任務,將知識點準確傳遞,并讓學生掌握一定的自主研究技能,培養思辨能力。如果教學過程中圖像資料運用過多過雜,會導致知識點泛化、碎片化,反而不利于學生能力的培養。因此選取上不僅數量要精,與文字的合理配比也是必須要考量的因素。
基金項目: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項目“清代黔北地區行政區劃研究與歷史地圖編繪”
參考文獻:
[1]藍勇.中國古代圖像史料運用的實踐與理論建構[J]人文雜志,2017(4)
[2]鄭樵.通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5:1825
[3]王丹林.《山海經》是最早的“圖經”和“山志”[J]安徽史學,2019(4)
[4]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982-988
[5]彼得·伯克.圖像證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
[6]孟建.圖像時代:視覺文化傳播的理論詮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57
[7]雍際春.天水放馬灘地圖注記及其內容初探[J]中國歷史地圖論叢,1998(1)
[8]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王也揚.“老照片”引出的史學話題——關于歷史學理論的斷想[J]史學理論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