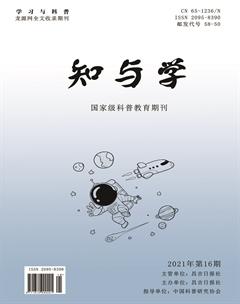略論先秦時期詩教的發生與發展
程諾
摘要: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從先秦時期詩樂舞一體的詩歌開始,這一點貫穿著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始終。詩教不能簡單地從字面意義上理解為通過詩歌進行教育,它有著更豐富的內涵。
關鍵詞:詩教;先秦;樂教;禮樂
1.從樂教中產生
詩歌的初始形態是祭祀儀式中的一種表演形式,因其歌樂舞一體的綜合形態可以斷定:此時的詩是一種“聲詩”。在那個時期,舞、樂的重要性是超過詩的,那么其教化功能自然是以“聲教”或者說以“樂教”為主。這些詩歌在內容上以歌功頌德和記錄本部族的重大歷史事件為主。在遠古時代巫術盛行和圖騰崇拜的社會背景下,樂教因此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作用。且根據考古發掘的實物推斷,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龍山文化時期禮制已經成熟,可以想見樂教在產生之初就與禮制一起,發揮著溝通人神,統一思想,強化秩序,整合社會的重要作用。
詩教自誕生之初就一直從屬于樂教,是樂教的一個分支。直到秦漢以降,音樂的教化功能逐漸消失,詩歌得以獨立出來才成為教化的主體,可以說詩教就是從樂教這一母體中脫胎出來的。
2.以《詩》教為主體
“詩教”一詞最早見于《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孔子于此處詳細地分析了“六藝”之教的優缺點以及其所能達到的教育效果,其中《詩》教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能達到“溫柔敦厚而不愚”之教化效果。但詩教與《詩》教并不完全相同,因為“詩”并不等于《詩》。《詩經》中的詩篇并非創作于同一時期,這些產生于不同時期的作品展現了詩歌由詩樂舞一體的綜合形態向純文學形態轉化的過程。《尚書·堯典》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時詩、樂的功能已經出現了分化,詩的獨立功能開始顯現。陳世驤先生指出,在《詩經》文本中,直接使用過“詩”字的篇目共有三篇,分別是《崧高》《卷阿》《巷伯》,通過分析,陳先生認為“作者自己在末后加重說他這一個篇章是‘詩’,特為明示或暗示著一種自覺的意識,標出詩之為語言的特有品質,雖然照早已流行著的風尚,這些篇章照例是歌唱的,但此時覺到了詩的要素在其語言性。有和歌唱的音樂性分開來說的可能與必要。”[1]陳先生的觀點恰與《尚書·堯典》中所提及的詩樂分化的現象相互印證。可見在先秦時期,詩歌雖然仍是詩樂舞的綜合藝術形式,但其中已經孕育著相互分離的趨勢。
《詩經》最初的編纂目的與后世的《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等詩集不同,其編纂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從文學角度上做文本的記錄和保存,《詩經》的形成更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其中的雅、頌部分更是周代禮樂文化興盛的表現,是周代禮樂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周代社會具有極高的地位和影響,統治者將其作為禮樂教化的范本,所以禮樂教育又稱為“詩教”,最終形成了以《詩》教為主體的一整套禮樂教育系統。
3.最終演進為言教
周代高度發達的禮樂文化孕育出了成熟的禮樂教育。此時的詩歌雖然仍是詩樂舞為一體的綜合藝術,但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詩樂舞各自的發展以及某些政治原因,詩樂舞的分離自西周時期開始逐漸展現,詩教開始脫離音樂呈現出以語言為主的教化特點。
根據《禮記·保傅》的記載,周代的教育更加細化,根據教學內容的不同分為五類,由不同的官員負責:“周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水東為東序,水西為瞽宗。”其中成均是學樂的專門場所,由大司樂主持。《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載了周代音樂教育的具體內容,其中包含樂德、樂語、樂舞三個部分。樂語的具體內容又分為“興、道、諷、誦、言、語”六部分,類似于六種語言文字技巧。由此可以推測,詩與樂在傳授過程中或已出現了分開教授的情況。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大環境加速了詩、樂的分離,此時的音樂的主要職責是娛人,只有極少一部分音樂還保留著教化的作用。詩成為了禮樂教化的主力軍。促成這一切的直接動因或是春秋戰國時期頻繁的外交活動。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此處的“誦”可理解為《周禮》中記載的“樂語”之一,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可見“誦”包含著“背誦”和“吟詠”兩個意思。而“專對”一詞可解釋為“擅自應對”或“獨立應對”。春秋時期各個國家之間的外交往來要遵守朝聘制度,《春秋公羊傳·莊公十九年》中記載:“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儀禮·聘禮》中講:“辭無常,孫而說。”鄭玄注曰:“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劉寶楠先生認為,使者是因為接受過良好的《詩》教,所以其外交辭令可以達到“孫而說”的水平。基于當時以《詩》作為外交辭令的歷史事實,外交使臣一定要精于《詩經》,并恰當地引用《詩經》中的語句來進行外交活動。故此時《詩》教的內容,主要是以學習《詩》中的語言技巧和創作手法為主。雖然當時詩樂結合使用的情況依然存在,但在外交活動中,《詩經》都是在脫離音樂的情況下使用的,外交使臣們引用與自己論點相符或對自己論證有利的部分詩句組織外交辭令,這種“斷章取義”的用詩方式在當時應用的十分廣泛,這與貴族教育中重視言辭的傾向是高度一致的。傅道彬認為“春秋時代經歷的從武化向文化、從世族到士族的轉型,一個重要傾向是人們普遍的文言意識和言語能力,一個注重詩書禮樂修養追求‘建言修辭’的士人集團走向歷史舞臺。”[2]士人的崛起為詩歌的獨立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在士人群體的推動下,詩歌以語言的形式開始承擔“言志”的功能,而音樂則逐漸朝著娛樂化和世俗化發展,樂教開始向著言教轉變。
參考文獻:
[1]陳世驤《中國詩之原始觀念試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2]傅道彬《詩可以觀——禮樂文化與周代詩學精神》,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 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