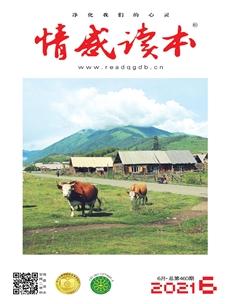“稀土之父”的浪漫愛情
不一
在她病情加重的那段時間,徐光憲幾乎片刻不離地守在她的身邊。但無論他如何不舍,她還是永遠地離開了。“老頭子,跟你過了一輩子,我很滿足,以后我不在了,你要好好活著。”這是她留給他的最后一句話。
舒婷曾在《致橡樹》中描述愛情的樣子:“不是誰攀緣了誰,不是誰歌頌了誰,不是誰滋養了誰,而是兩個高大獨立的個體,有著相同的信仰和姿態,像木棉和橡樹一樣,彼此獨立,相互致敬。”這句話用來形容徐光憲和高小霞的愛情,再合適不過。
徐光憲和高小霞,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或許只是兩個陌生的名字,但提到稀土,人們或多或少聽說過。
稀土是17種特殊元素的統稱,也被稱為“工業黃金”,小到智能手機,大到火箭、導彈等高新科技領域,稀土都是無可取代的存在。因為稀土的提取和分離技術要求極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雖然是稀土資源大國,卻因為萃取技術不過關,不得不低價出口稀土精礦,再以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價格購買稀土產品。
將中國從這種劣勢中拉出來,甚至影響了整個世界稀土格局的人,便是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的徐光憲。而他一生的摯愛,便是高小霞。
1940年,徐光憲和高小霞相識在交通大學,兩人是化學系的同班同學。廖一梅說:“這輩子,遇見愛,遇見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見了解。”他們的相識恰恰應了那句:精神上的門當戶對。他們擁有相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有時無須多言,一個眼神就懂了彼此的想法。
1946年,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將余生珍重地許諾給了彼此和國家。對于兩個在戰火中長大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有著相同的理想——科學救國。于是,第二年,他們都通過了赴美留學考試,只是因為經濟拮據,高小霞默默放棄了這次機會,直到兩年后才在朋友的幫助下赴美國學習。
其間,徐光憲僅用了一年時間就獲得了碩士學位,此后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并且被選為美國西格瑪克塞榮譽科學會會員。與此同時,半工半讀的高小霞也在學業上得到了導師的高度認可。當時不止一人提出要他們留在美國,畢竟這里的生活和前景會更好,而他們的選擇并不意外: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
1951年,正值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宣布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但徐光憲毅然選擇放棄美國優渥的工作而回國,高小霞也堅定地站在丈夫身邊,即使再過一年她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隨后,兩人以華僑探親的名義獲得簽證,輾轉回到中國,回到了那個最需要他們的地方。
回國后,兩人同時在北京大學任教。雖然生活條件和往日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不曾有一絲后悔,身邊是愛人,身后是國家,其他的都不足掛齒。
此后,徐光憲曾在科研上三次轉向,在四個方向上開展研究:從量子化學到配位化學,再到核燃料化學,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學,可以說,祖國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1954年,他與唐敖慶、盧嘉錫等人在北京主辦質結構講習班,為全國高校培養了一批理論化學方面的教師,他編寫的全國第一本物質結構教材,影響了幾代化學工作者;1957年,由于國防和學科建設的雙重需要,他開始從事核燃料萃取化學研究;1972年,又轉向稀土分離和萃取方面的研究。
針對當時中國在稀土市場上極不平等的地位,徐光憲傾盡了全部心血,帶領學生翻閱國外最新書籍,最終大膽決定放棄國際上流行的離子交換法和分級結晶法,改用萃取法來完成分離。這種在當時被很多人不認可的方法,卻使得稀土純度達到了創世界紀錄的99.99%。這一創新之舉直接推動中國稀土分離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也實現了中國從稀土資源大國向高純稀土生產大國的飛躍。
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曾經說過:能讓中國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幫人在拼命。徐光憲當之無愧是其中一位,而高小霞也身在其中。
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她一直從事分析化學的教學、科研工作,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200余篇。改革開放后,她就選擇了稀土極譜分析作為研究方向。徐光憲將稀土包含的17種元素分離出來,她則將剩下的部分制成“稀土微肥”,兩人一次次的合作,在科研上不斷迎來新的突破。
明明自己被稱為“中國稀土之父”,然而在徐光憲心里,妻子才是稀土研究方面真正的大家。原本嚴肅的科學,因為他們的愛情,似乎也染上了一絲浪漫的色彩。
成就接踵而來。1980年,兩人同時當選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學部委員;次年,又同時被批準為全國首批博士研究生導師;1988年,兩人同時當選中科院院士……一路走來,他們不僅是伴侶,更是朋友、親人,是彼此最不可取代的存在。她不止一次地說:“我這輩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他成為夫妻,并且一起生活這么多年。”而他對他的愛也是如此。
他常常為一個問題連續研究好幾天,但只要看到她工作到晚上11點還不休息,便一定要提出“黃牌警告”。而且不管走到哪里,兩人總是習慣地牽著手——牽了手就是一輩子,一不小心就白了頭。
高小霞晚年因為骨折坐上了輪椅,徐光憲便每天推著她繞著北大的未名湖慢慢走,說著只有彼此聽得懂的笑話,竟是比年輕時候更加親密。
1994年,徐光憲和高小霞榮獲了首屆“中華藍寶石婚佳侶獎”,并在《綜藝大觀》上度過了他們的藍寶石婚。在節目上,已是古稀之年的高小霞臉上卻帶著幾分羞怯,回首往事,她笑著說:“能夠跟他在一塊兒,我很幸福。”1998年,在接受采訪時,徐光憲說:“希望我們可以過一個金剛石婚。”只是這個心愿最終沒有實現,那個時候高小霞已經被診斷出癌癥。
在她病情加重的那段時間,徐光憲幾乎片刻不離地守在她的身邊。但無論他如何不舍,她還是永遠地離開了。“老頭子,跟你過了一輩子,我很滿足,以后我不在了,你要好好活著。”這是她留給他的最后一句話。
“我一生中,最滿意的是和小霞相濡以沫度過的52年;我最遺憾的是沒有照顧好她,使她先我而去。”在高小霞的追悼會上,這個經歷過無數風雨的男人坐在妻子的遺像邊,忍不住淚流滿面。
妻子去世后不久,徐光憲的頭發就全白了。思念如馬,自別,未停蹄。此后,每年清明節,他都會到墓園里,和長眠在此地的妻子聊家常,告訴她自己的研究成果,絮絮叨叨大大小小的事情:“小霞,你走了15年了,我們家里現在還好,我身體也還好,還有,你盼望成立的分析化學所也成立了。”
2005年,徐光憲獲得“何梁何利科技成就獎”,他將全部獎金都用來設立“霞光獎學金”,用來資助和獎勵貧困學生。“霞光”,是徐光憲的私心,取自兩個人的名字,為國,也為她。他知道那一定也是她的期望。
有人問什么是最好的愛情,徐光憲和高小霞給出了一個動人的答案——不可忘國憂,不可負卿卿,一心一意一事,一生一世一人。
余沈陽摘自《百家講壇·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