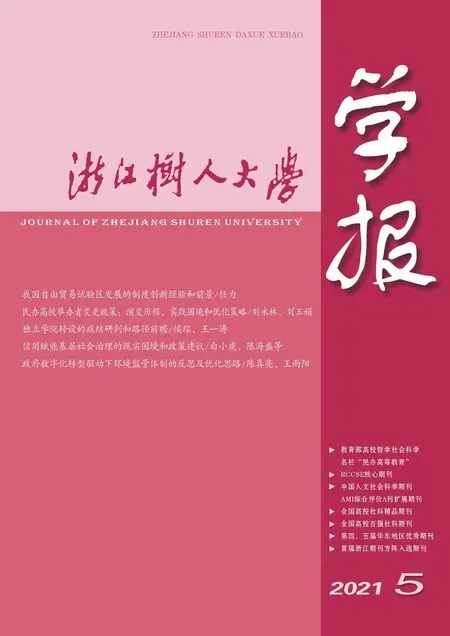我國基礎設施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溢出效應的檢驗
——基于1998—2019年時間序列數據
程永文
(合肥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才是平穩的增長來源,資本或勞動力增長可以短期帶動增長,但不具有持續性。內生增長模型說明了資本增長的外部性,特別是技術落后的國家,資本投入的大幅增長,不僅表現為資本要素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因資本的外部性,技術進步尤為明顯。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增長過程就是“追趕經濟體”的典型表現,特別是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融入全球制造業供應鏈,更是加速增長。2002—2009年,我國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平均達22.08%(1)數據來自2003—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經整理而得。,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2010年、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大幅下降,這也說明大幅投資是不可持續的。隨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雖有所恢復,但逐年下降。
1998—2007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穩步上行,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拖累,TFP增長率有所下降,整體表現大幅波動。特別是在2016年、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較低,甚至出現負增長,TFP增長率大幅回升。在經濟增長方面,1998—2017年勞動力增長、資本增長和TFP增長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給出了有意義的結論(2)數據來自1999—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經整理而得。。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0—2007年,資本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平均為41.4%,且很平穩。1998年、1999年為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政府制定了相應的財政擴張政策,資本拉動貢獻超過50%。為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政府再次推出財政擴張政策。2008—2016年資本平均拉動增長78.9%,增長效果顯著。2017年降到43%,處于相對均衡位置。
2008—2016年,資本發揮了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作用。若經濟增長有下滑趨勢,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放松都有利于促進投資增長,維持經濟仍以較高速度運行。然而,大幅投資維持增長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可能不利,首先刺激投資,信貸隨之大幅增加,國內宏觀杠桿率從2008年的113.7%,升至2019年第一季度的204.9%,10年間穩步增長了109%(3)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整理而得。。其次,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投放,是否對TFP具有“正向效應”,如果是“負向效應”,還不如降低基礎設施投資,讓TFP承擔更多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這不僅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還會降低宏觀杠桿增長的速度,甚至抑制宏觀杠桿的增長,既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免除“去杠桿”的難度。從2017年的數據看,固定資產增長率為-0.063%,但TFP的增長率為5.68%(4)數據來自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經整理而得。,TFP承擔起主要的經濟拉動作用,因此了解基礎設施投資與TFP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本研究擬通過1998—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驗證基礎設施投資對TFP是否具有“外部經濟性”(External Economy)。如果基礎設施投資存在外部經濟性,則基礎設施投資會提高TFP,兩者應呈正向關系,反之,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統計意義上的關系或反向關系,即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對TFP具有阻礙作用,表現為“外部不經濟性”。
一、文獻回顧
Arrow等(1970)最早將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引入新古典模型(5)Arrow K J,Lind R C,Uncertainty and the Evaluations of Public Investment Decis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No.3,pp.364-378.,Barro(1990)將政府支出作為內生增長模型的影響因素,如同“資本外部性”,對技術效率增長具有正的影響(6)Barro R J,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eous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No.5,pp.103-125.。Aschauer(1989)利用美國1945—1985年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公共設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現公共設施的產出彈性高達0.39(7)Aschauer D A,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No.2,pp.177-200.。Munnell(1990)(8)Munnell A H,Why has Productivity Growth Declined?Productivity and Public Investment,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1990,No.1,pp.3-22.、Finn(1993)(9)Finn M G,Is All Government Capital Productive?FRB Richmond Economic Quarterly,1993,No.4,pp.53-80.、Moomaw等(1995)(10)Moomaw R L,Mullen J K,Williams M,The Interregional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Capital,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5,No.3,pp.830-845.的測算結果分別為0.10、0.16和0.11。Stephan(2001)(11)Stephan A,Regional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Productivity:A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France,WZB Discussion Paper,2001.對德國大城市20世紀80年代的數據,Everaert等(2004)(12)Everaert G,Heylen F,Public Capital and Long-term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in Belgium,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4,No.1,pp.95-112.對比利時1953—1996年面板數據估算的結果分別為 0.082和 0.29。可以看出,基礎設施的產出彈性總體上處于0.08~0.30之間。
Devarajan等(1993)利用1970—1990 年69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資本、交通和通訊、保健和教育等支出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為負或不顯著,而經常性支出能促進經濟增長(13)Devarajan S,Swaroop V,Zou H F,What do Governments Buy?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Working Paper,1993,pp.1-36.。Landau(1986)(14)Landau D,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n Empirical Study for 1960-1980,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6,No.1,pp.35-75.和Haque等(2008)(15)Haque M E,Kneller R,Public Investment and Growth:The Role of Corruption,Centre for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08.集中反映 “負向效應”結論,Barro(1991)(16)Barro R J,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No.2,pp.407-443.、Devarajan等(1993)、Holtz-Eakin(1994)(17)Holtz-Eakin D,Public Sector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vity Puzzl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4,No.1,pp.12-21.、Evans(1998)(18)Evans P,State-society Syner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8,No.3,p.292.、Dessus等(2000)(19)Dessus S,Herrera R,Public Capital and Growth Revisited:A Panel Data Assess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0,No.2,pp.407-418.集中反映“沒有顯著效應”結論。
Berndt等(1991)采用瑞典1960—1988年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證明增加公共投資可以產生龐大的外部性,能夠顯著刺激私人部門生產(20)Berndt E R,Hansson B,Measu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in Sweden,NBER Working Paper,1991.。Everaert等(2001)(21)Everaert G,Heylen F,Public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Growth:Evidence for Belgium,1953-1996,Economic Modelling,2001,No.1,pp.97-116.、Hulten等(2006)(22)Hulten C R,Bennathan E,Srinivasan S,Infrastructure,Externaliti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Study of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6,No.2,pp.291-308.、Bronzini等(2009)(23)Bronzini R,Piselli P,Determinants of Long-run Regional Productivity with Geographical Spillovers:The Role of R&D,Human Capital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9,No.2,pp.187-199.采用不同的方法檢驗基礎設施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得到基礎設施對區域全要素生產率有積極影響的一致結論。
在國內,郭慶旺等(2006)(24)郭慶旺、賈俊雪:《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年第3期,第36-41頁。、武普照等(2007)(25)武普照、王耀輝:《公共投資的經濟增長作用分析》,《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第69-72頁。發現,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吳楠等(2017)認為,經濟性公共投資在 1%水平上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效應,其彈性系數為 0.219,而社會性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不顯著(26)吳楠、楊飛虎:《基于省級面板門限模型的公共投資經濟增長效應探析》,《價格月刊》2017年第8期,第78-83頁。。李獻國等(2017)基礎設施投資引入經濟增長模型,研究表明,基礎設施投資存在最優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呈倒U型關系(27)李獻國、董楊:《基礎設施投資規模與經濟增長——基于1993—2014年東、中、西部省級面板數據分析》,《宏觀經濟研究》2017年第8期,第86-93頁。。郭慶旺等(1999)(28)郭慶旺、趙志耘:《論我國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財貿經濟》1999年第6期,第31-35頁。、劉溶滄等(2001)(29)劉溶滄、馬拴友:《赤字、國債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兼評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有擠出效應》,《經濟研究》2001年第2期,第13-19頁。認為,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田杰棠(2002)指出,財政擴張已經產生一定程度的“擠出效應”(30)田杰棠:《近年來財政擴張擠出效應的實證分析》,《財貿研究》2002年第3期,第80-82頁。。莊子銀等(2003)認為,隨著地方財權的加強,地方公共投資效率在提高,對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正效應(31)莊子銀、鄒薇:《公共支出能否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的經驗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第4-12頁。。張勇等(2011)認為,公共投資不是拉動而是擠出了私人投資(32)張勇、古明明:《公共投資能否帶動私人投資:對中國公共投資政策的再評價》,《世界經濟》2011年第2期,第119-134頁。。王麒麟等(2011)發現,政府生產性支出未能促進經濟增長(33)王麒麟、賴小瓊:《政府生產性支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產出效應還是增長效應?》,《廣東商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第4-11頁。。張學良(2012)發現,我國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且正向溢出效應顯著(34)張學良:《中國交通基礎設施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嗎——兼論交通基礎設施的空間溢出效應》,《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第60-77頁。。張光南等(2013)認為,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通過降低經濟生產成本擠入了私人投資(35)張光南、宋冉:《中國交通對“中國制造”的要素投入影響研究》,《經濟研究》2013年第7期,第63-75頁。。楊飛虎等(2013)認為,我國公共投資的效率呈下降態勢,對產出、就業的促進作用不足(36)楊飛虎、周全林:《我國公共投資經濟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議》,《當代財經》2013年第11期,第18-26頁。。帥雯君等(2013)發現,財政支出對私人投資的作用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交替呈現擠出和擠入效應(37)帥雯君、董秀良、胡淳:《我國財政支出擠入擠出效應的動態時間路徑分析——基于MS-VECM的實證檢驗》,《財經研究》2013年第9期,第19-34頁。。楊智峰等(2013)發現,公共投資擠入了居民消費(38)楊智峰、陳霜華、吳化斌:《擠入還是擠出:中國公共投資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第60-68頁。。
王耀輝(2011)將公共投資分為公共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研發資本投資,樣本空間為1978—2008年,回歸系數就為各個組成部分的變化率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的影響。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和公共人力資本投資都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影響,但公共研發資本投資(財政科技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并不顯著(39)王耀輝:《中國公共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中國城市經濟》2011年第8期,第300-301頁。。張海星(2004)發現,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及研發投資可以有效提高TFP(40)張海星:《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中國數據的計量檢驗》,《財貿經濟》2004年第11期,第43-49頁。。李曉嘉(2012)認為,公共投資總體上提升了 TFP,不同性質的公共投資項目對 TFP 的影響不同,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41)李曉嘉:《政府公共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實證分析——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動態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第22-26頁。。曾淑婉(2013)認為,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提高了 TFP,并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42)曾淑婉:《財政支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基于中國省際數據的靜態與動態空間計量分析》,《財經理論與實踐》2013年第1期,第72-76頁。。
鐘世川等(2017)基于多要素的 CES 生產函數,將TFP增長率分解為中性技術進步效率變化效應、非公共資本增強型技術進步效率變化效應、勞動—非公共資本之間的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公共資本—非公共資本之間的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并利用1990—2014年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要素替代彈性顯著大于0且小于1;勞動的生產效率是提高的,而公共資本與非公共資本的生產效率是下降的;技術進步偏向資本,并且偏向非公共資本的程度大于公共資本,這是導致中國TFP增長減緩的主要原因(43)鐘世川、毛艷華:《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再測算與分解研究——基于多要素技術進步偏向的視角》,《經濟評論》2017年第1期,第3-14頁。。尹向飛等(2019)認為,從整個系統效率來看,2007年之前,TFP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這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2007年以后呈現低幅增長變化趨勢。絕大多數的年份技術進步為正,而技術效率改進為負(44)尹向飛、歐陽峣:《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再估計及不同經濟增長模式下的可持續性比較》,《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第72-91頁。。郗恩崇等(2013)研究表明,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印證了交通基礎設施投資阻礙了我國TFP的提升。同時,交通基礎設施的滯后項卻具有溢出效應:GMM估計方法得到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一階滯后項的回歸系數為正。回歸結果顯示,勞動力和國際貿易總額會阻礙TFP的提升(45)郗恩崇、徐智鵬、張丹:《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全要素生產率效應研究》,《統計與決策》2013年第23期,第137-140頁。。張光忠(2020)從政府身價的角度考察公共支出的審計效率,認為國內公共投資的審計功能未充分發揮,導致公共投資效率下降(46)張光忠:《政府審計促進公共投資效率的路徑研究》,《經營與管理》2020年第6期,第130-137頁。。
羅良文等(2016)利用2004—2013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DEA-Malmquist 指數法測算各省份TFP及其構成,并借助動態面板模型,從基礎設施投資角度分析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對TFP的實際貢獻度。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有效促進TFP的提高,且在促進TFP提高的途徑方面存在差異性。具體來說,基礎設施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對自主研發產生擠出效應,弱化了自主研發對TFP的積極作用;而對技術引進存在一定的促進作用,能夠增強技術引進對TFP的正向效應(47)羅良文、潘雅茹、陳崢:《基礎設施投資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基于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的視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第30-37頁。。賈俊雪(2017)構建一個異質性企業家模型,以中國現實數據為基礎,考察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TFP的影響機理。研究表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 TFP 具有明顯的“倒 U 型”影響。企業家面臨的信貸約束越嚴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 TFP 的影響越大,對存貸利差的影響則較弱。減少勞動摩擦可增強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 TFP 效應,較大的有效基礎設施服務、企業間差異性和公共消費性支出也具有類似影響,利用消費稅融資可更好地發揮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 TFP 的促進作用(48)賈俊雪:《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異質企業家模型的理論分析》,《經濟研究》2017年第2期,第4-19頁。。
謝里等(2011)選取 2000—2008年我國29個省級數據構建面板數據分析模型,實證公共投資對TFP的影響。結果表明,相對于政府的研發經費投資和交通基礎設施投資而言,政府對教育、能源、通訊和環保的公共投資更能顯著地促進我國TFP整體水平的提高(49)謝里、曹清峰、隋楊:《公共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省際數據的經驗研究》,《財經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4期,第99-103頁。。李成等(2015)采用DEA-Malmquist指數對TFP增長率進行了分解,以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公共投資的代理變量,檢驗了公共投資對TFP增長率及其分解的影響。結果表明,公共投資對TFP增長具有負向影響,且無顯著的區域差異;公共投資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僅體現在東部,而西部公共投資對純技術效率的負向影響最小;東、中、西部公共投資對規模效率均無顯著影響。因此,應從總量上減少公共投資,為穩定經濟進行的投資應該向西部地區傾斜,并著力改善東部地區具有技術進步作用的公共投資(50)李成、田懋、劉生福:《公共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空間面板分析》,《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第13-22頁。。劉生龍等(2010)考察了我國三類主要基礎設施對TFP的影響,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促進了TFP,而能源基礎設施對TFP的影響并不顯著(51)劉生龍、胡鞍鋼:《基礎設施的外部性在中國的檢驗:1988—2007》,《經濟研究》2010年第3期,第4-15頁。。文東偉(2019)認為,我國大多數制造業行業資本配置不足、勞動配置過度,且制造業整體的資源錯配程度在下降,但國有資本惡化了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了TFP(52)文東偉:《資源錯配、全要素生產率與中國制造業的增長潛力》,《經濟學(季刊)》2019年第2期,第617-638頁。。
由于以上國內文獻直接假設計量方程或經濟模型變量間的函數關系不明確,本研究先推導總產出增長率與各生產要素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間的函數關系,以此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以檢驗基礎設施投資對其他生產要素是否具有正的外部性。本研究的檢驗方法具有創新性,模型的可靠性更高。
二、模型與數據處理
根據包含有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在內的生產函數,推導出總產出增長與TFP增長率、公共投資增長率、私人投資增長率和勞動增長率之間的函數關系,再依據年度數據,即可發現計量關系。
(一)計量模型
公共資本投資是否有效率,是否有正的經濟外部性,是針對是否需要控制當前公共投資規模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本研究先建立包括公共投資在內的生產函數,推導出公共投資對產出增長影響的增長方程,然后建立計量模型。
設生產函數為:
Q(t)=A(t)F[KP(t),KG(t),L(t)]
(1)
其中,Q(t)是產量,A(t)是全要素生產率(TFP),KP(t)為私人固定資產投資,KG(t)為公共固定資產投資,L(t)為勞動投入。
對式(1)全微分則有:
dQ(t)=dA(t)F[KP(t),KG(t),L(t)]+A(t)dF[KP(t),KG(t),L(t)]
等式兩邊同除以Q(t),則有:

簡寫為:
或寫為:

(2)

要素彈性不能直接通過宏觀數據計算,但可以將彈性轉換成要素收入比例,表示為:
(3)
其中,αKP(t)、αKG(t)和αL(t)分別為私人資本要素收入比例、公共資本要素收入比例和勞動收入比例。如果公關資本存在“經濟外部性”,則有:
Q(t)=A(KG(t),t)F[Kp(t),KG(t),L(t)]
(4)
對式(4)全微分則有:
dQ(t)=dA(KG(t),t)F[KP(t),KG(t),L(t)]+A(t)dF[KP(t),KG(t),L(t)]=AKGdKGF[KP(t),KG(t),L(t)]+AtdtF[KP(t),KG(t),L(t)]+A(KG(t),t)FKPdKP+A(KG(t),t)FKGdKG+A(KG(t),t)FLdL
其中,AKG為A(KG(t),t)關于KG(t)的偏導數,At為A(KG(t),t)關于t的偏導數。
上式兩邊同除以Q(t),可簡寫為增長方程:
(5)

因測算TFP數據限制,擬使用索羅剩余法,即假設生產函數為:
Q(t)=A(t)F(K(t),L(t))
則有:
(6)
或寫為:
(7)

(8)

(二)數據處理
根據以上計量模型,需要公共資本年度數據、私人資本年度數據、GDP年度數據和勞動力年度數據等。根據世界銀行的界定,本研究將基礎設施分為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基礎設施投資對TFP的影響,且主要針對經濟基礎設施對TFP的影響,上述提到的公共資本主要指經濟基礎設施。金戈(2016)已對我國以及各省的經濟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和非基礎設施的資本存量做了相對合理的估算(53)金戈:《中國基礎設施與非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及其產出彈性估算》,《經濟研究》2016年第5期,第41-56頁。,因此1997—2011年的數據,本研究引用了金戈的數據,2012—2017年的數據是根據金戈的估算方法,原始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所有名義數據都平減至實際數據,GDP實際數據按照零售物價指數平減得到,資本存量按照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平減。表1是本文整理后的數據,數據皆是以1980年價格為基準計算的。

表1 測度生產函數相關數據
測度國內年度TFP增長率,擬使用式(7),涉及如何測算勞動力和資本在收入中的占比。生產函數只考慮資本和勞動兩個生產要素,則收入也只有資本要素收入和勞動要素收入。年度統計年鑒將GDP分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因此,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應屬于資本所得,生產稅凈額應屬于勞動和資本共同所得,因營業盈余還需扣除企業所得稅,所以資本所得應為: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企業所得稅。勞動要素收入比例和資本要素收入比例即為:勞動報酬/(勞動報酬+資本所得)、資本所得/(勞動報酬+資本所得)。表2為計算TFP所整理的數據。

表2 測度全要素生產率相關數據/%
依據式(8)得到回歸方程:
(0.042) (0.243) (0.151)


表3 回歸方程計量結果
(三)計量結果分析
從文獻研究來看,國內公共資本的效率低于私有資本,且公共資本年投資相對于私有資本的比例多數年份高于30%(見圖1)。賈俊雪(2017)認為,企業家的投資效率受限于信貸約束,公共投資對企業家的信貸約束有兩個方面影響,正向影響體現在公共投資增加,對企業家財富積累有正向影響,但公共投資增加的資金不論來源于稅收的增加或是資本市場,都會擠壓企業家的信貸,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54)賈俊雪:《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異質企業家模型的理論分析》,《經濟研究》2017年第2期,第4-19頁。。兩種相反的影響因素,如果前一種因素大于后一種因素,則公共投資增加會提高企業家的投資效率,相反,后一種因素,則因為公共投資擠出私人投資,私人投資不足,會降低企業家的投資效率。

圖1 國內公共資本年投資相對于私有資本的比例/%
這種微觀影響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公共投資增加、TFP反而下降的現象,重要的影響渠道可能有三個方面:第一,公共投資的長期增加和高速增長,使得政府的宏觀稅負長期居高不下,影響企業的資本積累和降低私有資本的投資;第二,同樣的資本,在高公共投資下,公共投資效率低于私有投資效率;第三,高公共投資的融資,使我國資本市場更傾向于公共資本的融資,使私有信貸約束更為嚴重,進一步降低投資效率。
三、政策建議
鑒于以上模型和計量結果,結合已有研究給出的微觀解釋,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政策調整,目標是提升TFP對經濟的拉動,雖然公共投資減少會降低公共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但TFP對經濟拉動會更高,因此不會大幅影響經濟增長,而且會使資本要素錯配現象得以緩解,經濟結構調整可以順利進行。我國的宏觀杠桿率和宏觀稅負會下降并保持穩定,經濟增長可持續且更加健康發展。
(一)政府部門僅批準帶來較高經濟效益的公共基礎設施
加大對公共設施投資的嚴格審批,與以往公共投資規模相比逐漸降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以提高公共投資效率。公共投資已明顯出現“擠出效應”,從數據分析結果看,公共投資占比過高,TFP下降,宏觀負債迅速上升,宏觀經濟風險上升,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降低公共投資,使TFP增長率上升,既能使經濟增長不致失速,又能降低宏觀負債率。
(二)宏觀上控制公共投資項目的資本市場融資
在降低公共投資規模的前提下,GDP增長率并不會降低,財政稅收并未減少,資本市場融資會自動下降,甚至會有財政盈余。否則,公共投資規模過大,擠出效應明顯,GDP增長率下降,稅收降低,公共支出規模大,公共債務增加,要求宏觀稅負增加,居民消費增長率必然下降。
(三)公共投資相對于私有投資比例應降低到30%以下
相對歷史數據和其他國家相關數據,公共投資降到30%以下,公共資本的邊際收益自然上升,能帶來正的經濟外部性。這為控制公共投資計劃的比例提供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限制。如果公共投資持續超過這個比例,宏觀經濟風險會進一步加大,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經濟風險的爆發將會嚴重傷害經濟發展。
(四)未來逐漸降低并穩定宏觀稅負水平,提高居民可消費水平
在穩態下,按照巴羅的理論,宏觀稅負比率與公共支出比例相等。降低當前過高的公共支出,才能使宏觀經濟穩定增長。目前金融部門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顯性化”和“去杠桿”措施已走出了重要一步,但降杠桿并不明顯,重要原因是沒有控制公共投資規模。因此,有必要降低公共投資比例,降低宏觀稅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