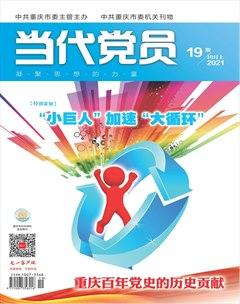紅巖家書:信念寫就家書 家書傳續精神
王娟 張菓



編者按:由厲華、鄭勁松、鄭小林編著,重慶出版集團出版的《紅巖家書》,是重慶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該書收錄了車耀先、藍蒂裕等20位紅巖英烈的家書,并以家書為切入點,講述紅巖英烈的革命事跡。通過家書對紅巖英烈的精神人格進行解讀,充分展現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執著追求、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彰顯了他們的崇高理想、高尚人格與家國情懷。本刊從本期起推出“紅巖家書”專題第一輯,以饗讀者。
車耀先(1894—1946),四川大邑人。他17歲入川軍當兵,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川西特委軍委委員,后在四川成都從事革命活動,引導許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抗戰期間,他創辦《大聲周刊》進行抗日宣傳,成為成都抗日救亡運動領導人。1940年,車耀先在國民黨制造的“搶米事件”中被捕,先后被囚禁于貴州息烽監獄和軍統重慶集中營。1946年8月18日,車耀先犧牲于重慶歌樂山松林坡,時年52歲。
車耀先:以“謙”“儉”“勞”為立身之本
“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余之不足;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全之國民。則余愿已足矣。夫復何恨哉?!”這是車耀先從自己的人生經歷中得出的人生感悟與肺腑之言,也是他對車崇英、車毅英、車時英、車伯英、車仲英5個子女定下的道德要求和人格規矩。短短200余字的家書,字里行間洋溢著最可貴的家國情懷和一個革命者對子女的殷殷囑托。
這是車耀先的人生價值取向。為人處世不可有傲氣,保持低調謙虛,生活上低標準,事業上高標準,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不傲、不貪、不懶……這是作為父親的車耀先對子女的期望:唯有健全的人格,才能去擔當道義。
車耀先就是這樣“誨人不倦”,總是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被捕后,車耀先忠誠自己的政治選擇,把監獄當作一個特殊戰場,借獄中圖書管理員的“工作”繼續傳播進步思想。
在沒有確切刑期的關押中,車耀先拒絕寫悔過書、拒絕參加國民黨的工作,他早已將個人生死與自由置之度外。
“回憶父親是痛苦的,也是自豪的。因為我們有一位滿懷革命理想和愛國豪情,無私無畏、堅貞不屈的好爸爸。他引導我們筑牢對革命的信仰,并給予我們無窮無盡的力量。”車耀先的子女如是說。
茍悅彬(1919—1949),云南綏江人。1935年到四川成都,先后入濟川中學、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讀書。1940年至1942年初先后在重慶、云南昆明當技術員、中學教師。1942年底考入國民黨陸軍機械化學校,1945年6月隨該校到重慶,后進入重慶二十一兵工廠當技術員。194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3月,他將《挺進報》傳給進步群眾閱讀,被特務發現,于同年4月15日被捕,被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監獄,1949年11月27日犧牲,時年30歲。
茍悅彬:我絕對不會有一句口供
這封信是茍悅彬在1949年3月,托一位出獄難友帶出去給黨內同志的。信言簡意賅,想來寫得匆忙。信中他談起受刑云淡風輕,那是不想讓家人擔心。紙雖短,情卻長!對弟弟妹妹的關心,對兒子的殷切希望,躍然紙上。
茍悅彬在信中說:“我生活得很好,請轉家人放心……”事實是這樣嗎?當然不是。茍悅彬在獄中遭受酷刑七次,面對酷刑,他泰然自若。他不想讓大家擔心,不想讓大家難過。他深知,勝利與成功從來都是革命者用鮮血浸染的、用犧牲奠基的。
“入獄后受了七次刑,沒有問出什么就算了。”這看似輕輕松松的一句話,今天讀來,卻有著沉甸甸的分量,令人肅然起敬!
七次酷刑,特務都沒能從茍悅彬身上得到任何訊息,他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誓言:我絕對不會有一句口供!
特務們始終想不明白,在數次酷刑面前,是什么力量支撐著這個文弱的書生?
特務們當然不明白,但我們可以從他的日記和社會調查中找到答案。他那封短短的家書的最后一句是希望兒子“繼承爸爸的意志”,這是眾多紅巖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對后代血與淚的囑托和殷切希望。
韓子重(1922—1949),重慶長壽人。1937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太南日報》戰地記者。1947年返國民黨四川省軍管區任少校參謀,建立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利用軍官身份,開展“軍運”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出賣,韓子重被關押進重慶渣滓洞監獄。1949年11月27日,韓子重在“11·27”大屠殺中犧牲,時年27歲。
韓子重:革命的道路是艱辛的
韓子重的兩封家書,情真意切,一方面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對家人的牽掛,另一方面真實地再現了時局的混亂和獄中慘無人道的生活。
“以天下人為念”,這在革命烈士的身上表現得最為充分。韓子重希望父母明白,像自己這樣因為革命而被捕坐牢的何止千萬,意思是在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治亂分合”時局中,總得有人去呼之、鼓之!殺身成仁、流血犧牲在所難免,沒有什么可說的。
從家書中不難看出,盡管身陷囹圄,生還希望渺茫,但韓子重最擔憂的不是個人生死,而是國家存亡和其他良善公民的生命。他告訴父親:“大勢所趨,大人尚可向有關當局作有效之私人建議,以搶救許多良善公民(于)死神手也。”
獄中的韓子重一直牽掛著他的戀人,又覺得自己拖累了她,因此請求父母“愿善待之,祈在可能范圍內,予以適當工作機會,兒身受也”。韓子重在給她的信中寫道:“革命的道路是艱辛的,坐牢流血是常事情,勿為我悲……”
韓子重犧牲在新中國已成立而重慶尚未解放之際。對父母,他沒能盡孝;對戀人,他沒能相伴到老;對生活,他沒能更多享受優越家庭本該有的幸福,但他實現了把自己“獻給國家、民族、社會”的愿望,用生命踐行了對信仰的追求。
英烈的價值,在于啟迪后人。韓子重的家書和他的這些閃爍著思想光芒的文字,就是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何柏梁(1917—1949),重慶人。1937年在重慶參加學生聯合會,組織鄉村救亡宣傳團,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奉命入復旦大學經濟系從事“學運”工作。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經組織安排,由他集資在重慶開辦安生公司并擔任經理,籌集黨的活動經費和擔任聯絡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出賣被捕,關押于重慶渣滓洞監獄。1949年11月27日,何柏梁在“11·27”大屠殺中犧牲,時年32歲。
何柏梁:以萬忍的耐心候黎明
何柏梁的第一封信寫于1949年11月11日,通過獄內看守、獄醫帶出,真實再現了解放戰爭走向全面勝利時的獄中形勢,以及革命烈士在獄中所受到的血與火的考驗和渴望得到消息的急切心情。
“何柏梁被捕后,他妻子曾詠曦送衣服去也被捕,他父親到處托人營救,還花好幾根金條才把曾詠曦保釋出(她懷孕要生小孩),但還是沒能把何柏梁救出。”幸存難友劉德彬回憶說,“每次他家中送來的食品,不管是罐頭或皮蛋以及其他,他都會分給獄中有病的難友吃,有時留少許來均分給同寢室的朋友,而有時竟一點也不留給自己……特別要提的是,柏梁同志和另外幾個朋友盡到最大努力,讓我們在獄中能知道外面的消息,能多了解一點外面的情況。”
在江竹筠等人被押出殺害后,何柏梁在其第七號信中表示不希望家人再通過各種活動營救他:“如再有條件出去,那太無價值了……”這里所談的“再有條件”,無非就是變節投降、跪地求饒,而在這出賣靈魂的前提下,生命又有什么意義呢?那個時候,國民黨特務雖然對失敗無可奈何,但仍不放棄動搖革命者,特別是利用革命者想“活著出去”的心態,企圖讓他們發表聲明、“悔過自新”,希望通過輿論打擊共產黨。對此,被關押在渣滓洞的“政治犯”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絕不茍且偷生。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愿把牢底坐穿”的那種無上的使命使他們有一種絕對的自豪感。當然,他們絕不放棄對活下來的等待,“要以萬忍的耐心候黎明”。這是在生死問題和革命信仰上,何柏梁告訴家人的自己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