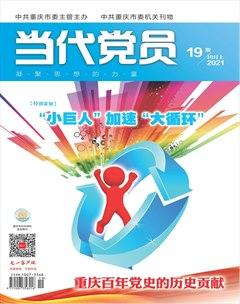一本書,一道疤
徐成文
那個七月,在擠掉了眾多競爭者后,我拿到了夢寐以求的師范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我喜悅地高擎著那蓋有鮮紅公章的紙張,望著鄉村小道,目光所及,皆是鄉鄰的微笑。
而后,一切為進城讀書準備著。
開學報到那天,天還沒露出魚肚白,我和父親依著火把的光亮,在崎嶇的山路上緩慢而行。父親扛著木匠新打制的木箱——里面塞滿了我的各種日常必需用品;我則提著網兜——其間散著一些衣褲及幾本與學習關系不大的小說。到了街上,父親敲開一家店鋪,他以買一盒低價的香煙為由,向店老板打聽客車的情況。得知還有一個小時客車才經過,那些哼唱了四十多年的鄉村流行曲便從父親的嘴里飄揚出來,但他壓低了嗓門,知道這里不是他隨意抒情的鄉下,還有很多人在酣睡呢。
客車如我家那條在田間耕耘了十多年的老水牛,緩慢地到達了城里的汽車站。
“學校接待處”的紙牌吸引著我們前去。得知我是新生,負責接待的高年級同學把我和父親以及攜帶的東西一一送上寬大的貨車車廂。東西放于車廂最前端,我們坐在木箱上,等待貨車的啟動。學校其實在鄉下,因為被譽為“下川東革命的搖籃”,自然遠離了城里的喧囂,躲進了幽靜偏僻的鄉村一隅。貨車在城鄉間穿越了近半個小時,原本安靜的車廂內,陡然有些躁動,抱怨聲開始蔓延。“你是來讀書的,要安安心心讀書,別沒事往城里跑!”父親叮囑我。
前面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貨車來了個大顛簸,我的手不自覺地松開網兜,順勢扶著車廂的欄桿,這時網兜里的一本書掉到了公路上。
“你的書掉了!”父親眼尖,我默默點頭。父親猛地直起身子,用力敲打著駕駛室的頂棚——他想讓師傅停車,撿起我的那本書。或許是敲擊聲太小,又或是師傅聽力不佳,貨車碾過那段坑洼,加速朝學校奔去。父親只得高呼“停一下!停一下!”縱使父親喊破了喉嚨,貨車依然沒有停止前行的跡象。“算了吧,一本書,不關緊要的。”我阻止父親。那是一本好友送給我的畢業禮物——一本與青春愛情有關的小說。“讀書人,怎么能隨意落下書呢!”父親駁得我緘默無言。
“你守好東西在學校等我,我下車去撿書!”父親見貨車即將爬行一段陡坡,車速定會放緩,決定下車撿書。我再三勸說父親,安全要緊。父親沒有工夫與我辯駁,他見縫插腳,移步到貨車的尾部,趁著貨車換擋的空隙,跳到了公路上。雖然車速減緩,但因為慣性,父親依然摔了個趔趄。貨車“吱嘎”一聲,停了。滿臉絡腮胡須的司機跳下車,對著父親一頓教訓,然后讓父親趕快上車。
父親把那本書遞給我,我才瞧見封面上的血跡。原來,父親在剛才下車時,右手背被車欄上的一顆螺絲釘刮了一條口子。父親用左手使勁地攥緊右手背,抑制更多的鮮血浸出。我提議叫師傅停車,讓父親找個最近的診所包扎一下,父親阻止了,他說不能耽誤同學們到校。我立馬從網兜里掏出粗糙的衛生紙,快速地擦拭父親手背上的鮮血。
學校到了,我建議父親到醫務室去處理一下傷口,我一人守著東西,但他卻一意孤行,總說自己的傷口并無大礙。把我安排好,父親要趁早返回城里的車站,坐早晨那輛客車回家。父親的右手背已經不再流血,只是那條傷口讓我悲從心生。正值農忙時節,父親當天必須趕回家,他還邀請了鄉鄰們第二天來幫忙收割稻谷。
我去報到注冊,父親到寢室為我鋪床。時間緊迫,父親把我安頓好就坐上了那輛返回城里接新生的貨車。臨走時,我再次勸說父親回家后不要忙著干活,先找個醫生好好弄些藥,等傷口痊愈后再干農活也不遲。父親沒有言語,他瘦弱的身軀很快模糊在我的視野里。
第一次遠離父母,國慶節三天假期我毅然選擇回家。到家時分,母親正圍著豬圈給豬喂食。
“爸爸呢?他的傷口好了嗎?”
“唉,好端端的一只手,現在留著一道疤痕。”母親說,父親不愿意去診所拿藥,又趁天晴去收割田里的稻谷,結果導致傷口感染。
“回來了,讀書還習慣吧?”父親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臉的喜氣。我沒有回答,立即抓過父親的右手,一探究竟——一條“肉蟲”凸現在父親的右手背上,父親原本粗糙的手背越發難看了。淚水不爭氣地浸滿我的眼眶,父親卻拍拍我的肩膀:“咱農民沒那么嬌氣,一道傷疤,一個標記,一個回味啊!”父親樂呵呵,我卻苦悶悶。
而今,那道傷疤跟隨父親離世已消失多年,唯有那本叫《窗外》的小說,悠閑地躺在我的書屋。
一本書,一道疤,我想父親了。
(作者系中學高級教師,重慶市萬州區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