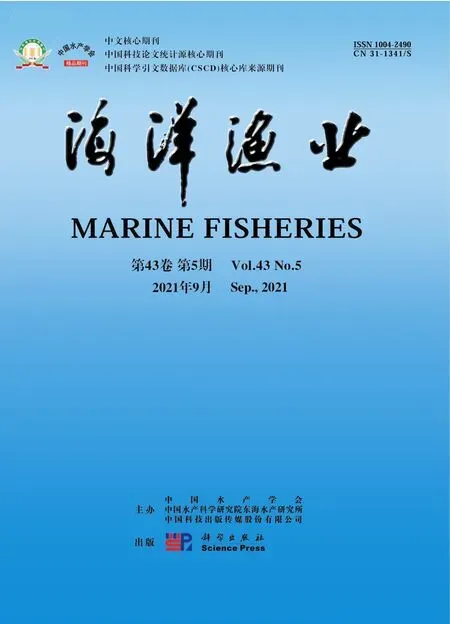以拉氏擬柱胞藻和浮絲藻為主的藍藻水華對中華絨螯蟹腸道和鰓及其養殖環境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
馬清揚,王 元,李傳步,范培莉,周俊芳,房文紅
(1.上海海洋大學,國家水生動物病原庫,上海201306;2.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農業農村部東海漁業資源開發利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90)
中華絨螯蟹(Eriocheirsinensis)又名河蟹,是我國重要的淡水養殖經濟蟹類[1],2018年全國養殖產量達75.7萬t[2]。中華絨螯蟹養殖區域主要集中在長江、黃河和遼河流域[3-4],隨著養殖規模擴大和放養密度增大,飼料大量投喂導致糞便和殘餌蓄積,使得養殖水體極易暴發藍藻(Cyanobacteria)水華[5],不僅會破壞養殖水的生態系統[6-7],有些藻類還會釋放次級代謝產物,對水生動物產生毒害作用,影響水生動物的生存[8]。同人類及其他哺乳動物一樣,水生動物的腸道中存在著數量龐大且結構復雜的微生物群體,這些微小生物會對宿主的生長發育、營養代謝和免疫應答等各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9-10]。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利用16S高通量測序[11]、克隆文庫和實時熒光定量PCR[12]、高通量測序[15]等技術對不同生存條件[12]、不同地理位置和性別[19]等條件下多種蟹腸道和生存環境[15]中的菌群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在不同生存條件下蟹體內的微生物是有差異的[11-15]。本研究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可以克服大多數微生物不可培育的技術難題,全面地解析微生物菌群結構信息[16]。通過研究在暴發以拉氏擬柱胞藻(Cylindrospermopsis raciborskii)和浮絲藻(Planktothrixsp.)為主的藍藻水華池塘中的中華絨螯蟹鰓與腸道及其養殖環境中池水、水草和底泥的菌群結構,以期為評價藍藻水華對中華絨螯蟹微生態健康的影響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品采集
2018年9月對上海崇明東灘某一水產養殖專業合作社發生藍藻水華的中華絨螯蟹池塘進行采樣,同時采集相鄰的未發生藍藻水華池塘的樣本作為對照。藍藻池和對照池池塘面積均為10 000 m2,池水水深1.0~1.4 m,蟹種、水源、飼料和養殖管理技術等均一致。藍藻池池水水溫(25.8±0.1)℃、溶解氧(4.05±0.22)mg·L-1、總氮(1.96±0.13)mg·L-1、總磷(0.45±0.03)mg·L-1、亞硝基氮(NO-2-N)(0.011±0.003)mg·L-1、pH 8.8,對照池池水水溫(25.9±0.1)℃、溶解氧(4.12±0.31)mg·L-1、總氮(1.72±0.15)mg·L-1、總磷(0.43±0.03)mg·L-1、亞硝基氮(0.007±0.003)mg·L-1、pH 8.7。采集藍藻水華池和對照池的池水、伊樂藻(Elodeanuttallii)、底泥和中華絨螯蟹的鰓和腸道。每種樣品4個重復(中華絨螯蟹的腸道和鰓取自4只雄蟹和4只母蟹),水樣為上、中、下3層水混合。將采集的池水、底泥、伊樂藻和中華絨螯蟹保存于4~8℃低溫樣品箱,帶回實驗室處理。
1.2 樣品前處理
1.2.1 浮游植物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樣品處理
采集的池水在現場采用魯哥氏溶液(魯哥氏溶液為1∶2比例的碘和碘化鉀水溶液)固定,1 L水樣添加15 mL魯哥氏溶液;靜置沉淀,以虹吸法吸去上清液,濃縮成50 mL后,再加1 mL甲醛溶液。
1.2.2 微生物多樣性分析的樣品處理
稱取底泥2.00 g、剪碎的伊樂藻2.00 g分別置于5 mL無菌EP管中;取100 mL水樣,使用抽濾裝置(0.22μm水系濾膜,紫外消毒15 min)過濾水樣,將濾膜放入5 mL無菌EP管中,將所有樣品保存于-80℃冰箱備用。
取酒精棉球擦拭中華絨螯蟹體表,打開頭胸甲取兩側的第3片鰓于無菌EP管中;取出腸道,去除腸道內容物,放入無菌EP管中,保存于-80℃冰箱備用。
1.3 浮游植物定性和定量分析
浮游植物種類鑒定主要參照《中國淡水生物圖譜》[17]和《淡水微型生物》[18];定量計數時,取搖勻樣品0.1 mL,置血球計數板內全片計數,每個水樣計數2片取其平均值,若2片計數結果之差大于15%,則取第3片計數,取3片的平均值。
1.4 微生物多樣性分析
1.4.1 基因組DNA提取、PCR擴增及測序
池水、底泥、伊樂藻、中華絨螯蟹腸道和鰓分別采用PowerWater?DNA提取試劑盒(MoBio,美國)、土壤DNA提取試劑盒(MP Biomedicals,美國)、植物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TIANGEN,中國)、DNA提取試劑盒(Omega,美國)。DNA提取后用1%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DNA樣品質量。將檢測合格后的樣品交送上海美吉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采用Illumina PE300測序平臺進行細菌V3+V4區高通量測序。
1.4.2 數據分析
根據PE reads之間的overlap關系將成對的reads進行拼接。與此同時,對reads的質量和拼接效果進行質量控制。采用RDP classifier貝葉斯算法對OTU進行分類學分析,并在合適的分類水平進行分析,通常情況下,細菌數據庫匹配采用Silva數據庫。
對注釋過的信息進行Alpha多樣性分析、物種組成分析、NMDS分析(將樣本中包含的物種信息以點的形式反映在多維空間上)和樣本層級聚類分析(使用UPGMA算法構建樹狀結構,可呈現不同樣本的差異)等,具體方法參照王元等[19]以及肖漢玉等[20]研究。
2 結果與分析
2.1 藍藻水華池塘和對照池浮游植物種類與生物量
表1 為藍藻池與對照池浮游植物種類組成、豐度和生物量。藍藻池浮游植物有21種,其總豐度為(9.18±0.94)×108個·L-1,生物量為(103.944±11.367)mg·L-1,而對照池浮游植物僅有12種,豐度為(1.22±0.60)×106個·L-1,生物量僅為(0.545±0.056)mg·L-1。藍藻水華池塘的浮游植物生物量是正常池的190倍。藍藻水華池塘以藍藻門的浮絲藻和拉氏擬柱胞藻為優勢種,其生物量分別為55.879 mg·L-1和39.544 mg·L-1,兩者生物量之和占總生物量的91.8%。對照池塘的優勢藻為隱藻門的卵形隱藻(Cryptomonasovata)和嚙蝕隱藻(Cryptomonaserosa),其生物量分別為0.273 mg·L-1和0.126 mg·L-1。
2.2 高通量測序結果
2.2.1 Alpha多樣性分析
根據barcode和引物提取有效的序列,進行去雜和修建,得到Trimmed序列。對其進行統計分析發現,一共得到3 396 275個序列,落在401~500 bp長度上的序列有3 393 885條(99.9%),表明測序片段大小正常。經過物種注釋與分類,樣品中的微生物涉及到52個門、106個綱、205個目、373個科、674個屬、1 163個種、2 302個OTU(相似性大于97%的序列歸為一個OTU)(表2)。

表2 Alpha多樣性分析Tab.2 Alpha diversity analysis
結合Shannon指數和Simpson分析微生物多樣性。環境樣品微生物多樣性由高到低分別為底泥、池水和伊樂藻。池水和底泥中的微生物多樣性對照池高于藍藻池,水草的微生物多樣性藍藻池較對照池低。腸道和鰓的微生物多樣性低于池水和底泥,腸道的微生物多樣性高于鰓。
結合Ace和Chao指數分析物種豐富度。腸道和鰓的群落豐富度總體上低于環境樣品(底泥、池水和伊樂藻)。底泥微生物最豐富,其次是伊樂藻和池水。水草和池水的群落豐富度藍藻池高于對應的對照池中的樣本,而底泥的群落豐富度藍藻池低于對照池。
2.2.2 菌群結構分析
2.2.2.1 門水平的優勢菌群分布特征
如圖1所示,基于門水平下的菌群分類,藍藻池和對照池的池水、底泥、伊樂藻中的細菌物種組成差異較大,分別呈現了不同的優勢菌群分布特征。但相同的是,都從中發現了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的生物。并且,未發生藍藻水華的對照池的樣本中也檢測到了一定量的藍細菌門生物。藍藻池水中優勢菌群為藍細菌門(Cyanobacteria)、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變形菌門和疣微菌門(Verrucomicrobia),相對豐度分別為38.29%、27.38%、12.98%和7.05%;對照池水的優勢菌群為變形菌門、放線菌門和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相對豐度分別為52.17%、21.88%和13.24%。底泥的優勢菌群一致,藍藻池和對照池均為變形菌門、綠彎菌門(Chloroflexi)以及擬桿菌門,只是在相對豐度上有少量差別。水草中微生物多樣性很低,絕大部分為藍細菌門,藍藻池藍細菌門相對豐度在90%以上;對照池在80%以上;除藍細菌門的生物,水草中其余菌群為變形桿菌門,藍藻池中還含有疣微菌門的菌群。

圖1 門水平上的細菌種群結構與豐度(n=4)Fig.1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at phylum level(n=4)
藍藻池和對照池中華絨螯蟹鰓中均以放線菌門、擬桿菌門和變形菌門為優勢菌,但在物種相對豐度上存在差異;中華絨螯蟹腸道均以擬桿菌門、柔膜菌門(Tenericutes)、變形菌門、厚壁菌門(Firmicutes)為優勢菌。在中華絨螯蟹腸道樣本中,藍藻池中優勢物種同對照池相比,變形桿菌門生物的相對豐度增多,相應的柔膜菌門生物的含量減少,厚壁菌門的生物替代擬桿菌門的微生物定植中華絨螯蟹的腸道中。另外,藍藻池蟹鰓和腸道的樣品中都出現了一定豐度的Saccharibacteria門的生物。
2.2.2.2 屬水平的優勢菌群分布特征
基于屬水平(圖2)分析各樣品的優勢菌群分布特征,結果顯示,池水、伊樂藻和底泥中的細菌種類均很豐富,尤其是底泥。

圖2 屬水平上的細菌種群結構與豐度(n=4)Fig.2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at genus level(n=4)
藍藻池和對照池池水中優勢菌群結構相差較大,藍藻池池水的優勢菌群為浮絲藻屬(Planktothrix)、CL500-29_marine_group屬和hgcI_clade屬,相對豐度分別為34.52%、11.28%和7.05%;對照池水中的優勢菌群為不動桿菌屬(Acinetobacter)、Candidatus_Aquiluna屬和hgcI_clade屬,相對豐度分別為15.59%、14.67%和2.30%。池塘底泥細菌種類豐富,藍藻池底泥優勢菌群結構與對照池的差別體現在相對豐度上。對照池和藍藻池的底泥中優勢屬為norank_f_Anaerolineaceae屬和norank_f_Xanthomonadales_Incertae_Sedis屬。對照池和藍藻池中伊樂藻的優勢菌群為norank_c_Cyanobacteria屬,藍藻池中該菌屬的相對豐度高達92.42%。
對照池蟹腸道中優勢物種為Candidatus_Bacilloplasma屬、Candidatus_Hepatoplasma屬和Prolixiibacter屬,相對豐度分別為17.38%、16.60%和12.95%。藍藻池中華絨螯蟹腸道中優勢物種為Prolixiibacter屬,相對豐度為28.59%,大 約 是 對 照 池 的2倍。其 次 是Candidatus_Bacilloplasma屬 和norank_f_Erysipelotrichaceae屬,相對豐度分別為17.84%、9.86%。在中華絨螯蟹腸道中還發現了一定豐度的氣單胞菌(Aeromonas)和弧菌(Vibrio)。
對照池中華絨螯蟹鰓中優勢物種為Ilumatobacter屬,相對豐度為49.89%,其在藍藻池含量更高,為61.90%;而后是norank_o_Sphingobacteriales屬和Albimonas屬,相對豐度分別為22.90%和12.75%,藍藻池中norank_o_Sphingobacteriales屬和Albimonas屬的相對豐度相應都低了5%,分別為17.99%和7.82%。
2.2.3 NMDS分析
圖3 是藍藻池和對照池中池水、底泥、伊樂藻以及人工養殖的中華絨螯蟹的腸道和鰓樣品細菌群落多樣性的NMDS分析。NMDS分析是根據樣本中包含的物種信息,以點的形式反映在多維空間上,不同樣本間的差異程度是通過點與點間的距離體現的。結果顯示,環境樣品(池水、底泥和伊樂藻)中,兩個池塘中底泥樣品間的距離最短,即菌落組成最相近,其次是伊樂藻,而池塘水樣相差最大。藍藻池和對照池的同一類環境樣品未見重合,而兩個池塘中養殖中華絨螯蟹的腸道和鰓樣品有交集,其中腸道樣品重合程度較鰓樣品高,這表明中華絨螯蟹腸道的菌群結構較為穩定。另外,對照池和藍藻池中鰓樣品距離各自生活的池水更近,菌群組成更接近。

圖3 不同樣品中細菌群落多樣性的NMDS分析Fig.3 NMDS analysi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
2.2.4 樣本層級聚類分析
如圖4所示,運用UPGMA對樣本層級聚類分析。不同種類樣品大致可以各自聚成一個分支。環境樣品,例如伊樂藻、底泥和對照池池水,依據采樣環境和樣品種類呈現不同的分組。其中,藍藻池中池水跟伊樂藻比較相近,可能是由于藍藻池的水中富含大量藍藻門的生物。對照池池水則和中華絨螯蟹的鰓樣品的物種組成距離更近,甚至對照池的部分鰓樣品(G4_CON和G6_CON)與對照池池水在同一簇內。池塘底泥與中華絨螯蟹鰓也在同一簇內,但處在不同分支下。不同池塘的腸道樣品和鰓樣品各自未呈現很好的聚類,對照池的分支內會出現一些藍藻池的樣品。其中腸道樣品與環境樣品不在一個簇內,自成一個分支。而池塘底泥的分支與中華絨螯蟹鰓的分支在一個簇內,部分池水樣品與鰓樣品被劃到一個分支內。

圖4 各樣本的層級聚類分析Fig.4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of samples
3 討論
本次實驗中引起藍藻水華的是以藍藻門拉氏擬柱胞藻和浮絲藻為主的藻類,兩者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91.8%。藍藻池藍藻門的浮絲藻生物量最高,其次是拉氏擬柱胞藻,大約是浮絲藻的0.7倍。這與常孟陽等[21]報道的藍藻暴發優勢種為微囊藻的結果不同,可能是由于采樣地點不同導致的結果差異。同微囊藻一樣,拉氏擬柱胞藻也具備產生多種毒素的能力,并且該藻有較寬的溫度適應能力,在11℃的低溫和35~39℃的高溫下,均長勢良好[23-25]。有報道稱擬柱胞藻已在中國廣東、云南、湖北、福建及臺灣等多個省份被發現[26-28]。在未來,擬柱胞藻可能會成為藍藻水華的重要來源。
藍藻水華對池塘微生物結構產生了一定影響。綜合門水平和屬水平注釋的物種信息分析,藍藻暴發極大地改變了水環境的微生物結構,特別在屬水平上,這種差異尤其明顯。并且在所有藍藻組的環境樣品中都檢測到了一定量的藍細菌門物種,且含量都比對照組的樣品高。這印證了藍藻水華會改變養殖池塘微生物組成這一論點。
相較于環境樣品,藍藻水華對養殖的中華絨螯蟹體內微生物的影響較小。其對中華絨螯蟹腸道中的微生物菌群有一定的影響,但基本不改變結構,只是改變各物種的占比。在金貝[31]的報道中,陽澄西湖的中華絨螯蟹腸道優勢菌群為柔膜菌門、變形菌門、擬桿菌門、CK-IC4-I9和厚壁菌門,與本研究結果相似的是中華絨螯蟹腸道中的優勢物種都出現了柔膜菌門、變形菌門和擬桿菌門。根據LI等[12]的研究,中華絨螯蟹中腸道優勢菌群主要是變形菌門、擬桿菌門、放線菌門和疣微菌門。在狄盼盼等[32]的研究中,中華絨螯蟹腸道優勢菌群為變形菌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等。基于門水平的物種注釋分析,本研究中中華絨螯蟹腸道優勢菌群特征與上述兩文研究結果大致相似,不同之處可能是由于采樣地點、時間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導致。在馬文元等[34]研究中,中華絨螯蟹腸道優勢細菌共計6種,屬于4個菌屬,分別為檸檬酸桿菌屬(Citrobacter)、假單胞菌屬(Pseudomonas)、氣單胞菌屬和摩根菌屬(Morganella),本文結果與其不同,其原因可能是上述文章的中華絨螯蟹被投喂了蝦青素,且運用的是傳統分離培養的方法,而本文采用高通量測序的方法研究中華絨螯蟹腸道優勢細菌組成。
另外,在中華絨螯蟹腸道中還發現了一定量的氣單胞菌和Tyzzerella3,這和馮光志[33]在小龍蝦腸道中發現的結果相似。此次實驗在中華絨螯蟹的腸道中發現了一定量的弧菌和氣單胞菌,但鰓中卻幾乎沒有。
中華絨螯蟹鰓中的微生物結構與環境微生物有緊密的聯系。本實驗得到的中華絨螯蟹鰓中的優勢物種為放線菌門、擬桿菌門和變形桿菌門,其中放線桿菌門和擬桿菌門也是藍藻池和對照池中池水和底泥樣品中的優勢物種。本實驗和馬文元等[34]研究的中華絨螯蟹鰓中優勢物種為變形菌門和厚壁菌門的結果不同,可能是因為其用傳統的分離培養方法進行研究,而本文中中華絨螯蟹鰓中的優勢物種也是其生存池水中的優勢物種。
水生生物經歷孵化后,在不同的發育階段,外界的微生物會經歷一段演替和適應的過程,部分或全部定植在生物體內[29-30]。所以不同的外界微生物會影響水生物體內的微生物結構。綜上所述,環境的不同會改變中華絨螯蟹腸道和鰓的微生物結構。
結合NMDS結果看,中華絨螯蟹腸道的菌群組成較為穩定,鰓中的微生物結構與生活的池水的關系更近。相比于腸道,鰓中菌群結構差異更大,層級聚類分析結果也從側面反映了這一點。中華絨螯蟹的鰓會接觸外界環境,大量的水流入鰓室,入水孔周圍列生著的許多剛毛雖然會阻擋一些外來物,顎足也會清理污雜物,但不能阻止微生物在鰓中定植[34]。中華絨螯蟹攝食過程中攝入了水,水中的細菌進入腸道定植下來,同時其部分的消化功能要依靠腸道微生物來完成,中華絨螯蟹腸道內有自身的微生物群落[34-36],對于外來微生物的入侵可能有一定的防御力,入侵后體內的微生物群落可能形成了緩沖,所以環境中微生物對腸道的影響相較于對鰓的影響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