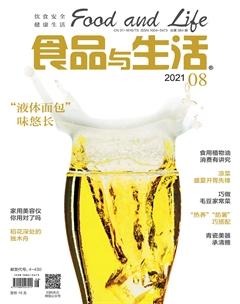青田散記
何菲
從上海到浙江青田,高鐵單程耗時3個多小時。列車在浙江東南部霧靄氤氳的山嵐間飛馳時,我暗自琢磨這座大山里的縣城吸引我的理由。“中國四大名石”之一的青田石只是引子,飛地感與滄海遺珠,是我對青田的私感受。
紅色革命老區,渾然天成的洋味,華僑、田魚、咖啡、群山、梯田、甌江、斷崖直瀉、萬仞飛瀑、梵音裊裊、永嘉學派、劉伯溫……構成了青田的魔幻。青田不靠海,是地道的山區。境內所見皆山,千米以上的大山有200多座,“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和“大山里的小歐洲”的縣城觀感,足以滿足仙俠劇和穿越劇的構成。
沒去過青田的人很難想象這座山城的復雜氣息。以我之前的偏見,以為青田的洋味當屬山寨土味效仿,卻不想那已經有了300年的積淀,這使得它成為江南的一處秘境。青田的神奇,也使得它成為中國房價第一縣、中國人均存款第一縣、外匯第一縣,實現了這座東南之磽壤的最強逆襲。
早在唐宋時期,青田就隸屬浙江麗水市管轄。麗水古稱“處州”,在江南當屬山高水遠,卻是浙閩的咽喉要道。因山勢險峻,土壤貧瘠,自然災害頻發,曾經的青田可說是窮鄉僻壤,處于中心文化的邊緣地帶。
好在一泓甌江水穿城而過,順甌江往東南60千米可達商業繁華的溫州。這條中國東海獨流入海的河流是浙江第二大江,自西向東流經麗水、溫州,從溫州流入東海。窮則思變,甌江提供給硬錚強韌的青田人向外探索的可能。
溫州就是青田人的出海口和啟航港。也因此,盡管隸屬麗水,但從地緣、語言、文化認同上,青田人的自我身份認知更趨同于“鹿城”溫州。而發源于溫州的永嘉學派有著事功思想,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青田人劉伯溫是永嘉學派的直接繼承者,這也成為青田人商業思維的理論依據。
青田石雕是青田人外出討生活的依傍之物,形成他們第一次出國潮契機。他們簡陋的行囊里背負著巧奪天工的青田石雕,沿甌江順流而下至溫州,路就盤活了,寧波、上海、天津、日本、歐洲皆有他們的履痕。他們中有些遠行至東北邊陲滿洲里出境,越過西伯利亞茫茫森林原野,進入俄羅斯,再輾轉歐洲各國;走水路亦是山迢路遠,險象環生,許多人有去無回。青田人的膽量與勇氣可見一斑。經年的跨國貿易往來,開拓了青田人的視野,有了海的開闊與澎湃,也形成了早期浙商的縮影。
家家有華僑,人人是僑眷,建縣于唐代的小城青田已有300多年的華僑史。現戶籍人口約57萬,卻有著33萬華僑,分布在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80%集中在歐洲,是著名的僑鄉。旅歐數十載的友人說他在西歐吃過的中餐館中80%以上是青田人開的。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說,“這些青田人辛辛苦苦,積攢下一點錢,想方設法要帶回青田老家,這些人誓死都不忘故國。”乘風破浪,生如夏花,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對家鄉的熱愛與反哺,使得他們將積累的財富和經驗跨越時差與洋流,以各種方式帶回故土,以更國際化的眼光與習慣改變這座曾經閉塞貧困的山城,使得青田一天天脫胎換骨,形成一張亦歐洲、亦江南的動態拼圖,高鐵的開通也讓青田有了更大的朋友圈。
徜徉于青田縣城,歐陸風情建筑隨處可見。臨江路的青田外灘酒吧、咖啡館、西餐廳星羅棋布,青田“外灘3號”同樣典雅恢弘。在橫跨甌江的網紅人行橋上眺望兩岸夜景,也曾有不知今夕何夕的喟嘆。青田人購物,習慣于去中國僑鄉進口商品城,那里有著純正的意大利咖啡、西班牙火腿、德國啤酒、法國香水、日韓彩妝……青田也可能是中國菜場中唯一能用歐元結算買菜的縣城。不久前我與《舌尖上的中國》制片人聊到青田時,她脫口而出:“青田的法餐真的好!”
咖啡是青田的標識。起初我不以為然,我生活的上海是目前世界上咖啡館最多的城市,有著7000多家咖啡館,是紐約的3倍。上海人均年消費咖啡約20杯。相比于上海人喝咖啡或多或少的氛圍感,青田的咖啡更隨性,全然活在自己的范式里。在大山里的農家菜館,登場和收尾的不是茶,而是咖啡。農民下地耕種前,提神的是咖啡,學子放學后,解渴的是咖啡,老街麻將館里兼營咖啡。在政府機關,為訪客提供的飲品是盛在一次性紙杯里的意式濃縮咖啡,純正程度可圈可點。青田的咖啡館溫馨而家常,15元一杯意大利濃縮的平價,使其完全融入日常餐飲范疇。對青田人來說,何以解憂,唯有咖啡。
青田有近300家咖啡館,人均年消費50杯,甚至有24小時營業的咖啡館。咖啡是青田人的剛需,而非道具。你會從青田人的生活方式中感覺到他們對僑居記憶的某種懷念和習慣延續,這也使他的居民形成豁達高闊的心智:你開你的法拉利豪車,我飲我15元的咖啡,一樣地道好味,因為這里是青田。
距離縣城40多千米外的方山鄉龍現村,是青田華僑的發源地之一。村民吳乾奎以經營茶葉為主,兼帶部分青田石雕銷往歐美,這些故土風物屢屢在歐美獲獎。吳乾奎是青田華僑的先驅,在海外奔波了22個春秋,衣錦還鄉后的他在龍現村建造了吳氏舊宅“延陵舊家”,外形歐美,內部則是中式傳統風格,旨在告訴后人:外表可以是西方的,但心永遠是中國的。
群山環繞、梯田錯落、稻魚共生、東西合璧、農旅融合的龍現村現有800多村民,曾經和現在仍旅居海外的華僑有700余人,僑居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被譽為“聯合國村”。他們回家過個年,仿佛在餐桌上就聚齊了小半個聯合國,僑鄉氛圍濃郁。龍現村亦是聯合國世界農業文化遺產——稻魚共生系統保護實施地。魚稻套種已有700多年歷史,被農業部命名為“中國田魚村”。梯田、田魚、華僑、石雕,使得龍現村形成了獨一無二的風格: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田魚村龍現小學是2021牛年央視春晚“一年又一年”中浙江唯一的取景地。在龍現小學旁,我又吃了一頓田魚,就著咖啡。說實話,依然不很適口。在青田我幾乎每頓都吃田魚。這種形似紅鯉魚的淡水魚氣質優雅,外形俊美,口味卻非我所喜。但這種魚的食用意義倒在其次,它幾乎滲透到了青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國人的生活,與其說是物質生活,不如說是情感生活。青田人漂洋過海,背井離鄉,他們的行囊里除了青田石,一定裝著田魚干。他們與田魚共生共榮。田魚之于他們,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是33萬青田海外僑民的共同感知體和鄉愁圖騰。看到了田魚,仿佛看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