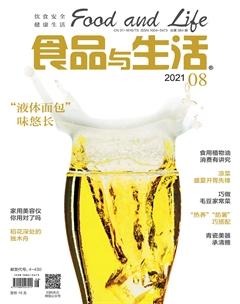轉過身,就是那碗冷面
蔣頤
2021年的夏天,上海毫無掙扎地入了伏。今年的熱很特殊,雖然熱得不動聲色,但是常常讓人大汗淋漓。空氣的味道、天空的顏色,都令我恍惚地覺得,我回到了1990年。
彼時是我最后一個暑假,我即將開始工作了。在工作之前,我照例過著一成不變的暑假。而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騎著父親淘汰給我的28寸“鳳凰”牌自行車,在傍晚穿梭于弄堂之間。不為什么,也不知道為了什么,就是喜歡。
我喜歡看老人在家門口閑聊間準備著晚上的吃食;我喜歡看小孩子坐在浴盆里,在水斗邊象征性地洗著澡,實則是在玩水的嬉鬧;我喜歡去后弄堂偷偷地欣賞我心中的“女神”洗頭發……我最喜歡那時的一切,夕陽淺淺地照在屋檐,地上有濕濕的、為了降溫的水,也可以騎著車在形式各異、顏色不同的萬國旗下穿過,那是上海的夏天傍晚。到現在有時在夏天做夢,還是會夢到那時的情景。真好!
那時父母很忙,我最愛的奶奶也去世很久了。想和她一起吃飯,卻再沒有機會了。
和奶奶一起過夏天時,最喜歡的吃食就是上海的冷面。
不僅是面條的溫度帶來的清涼,還有去吃冷面前對于冷空氣的向往。冷面店里總是很涼快,風扇轉得非常賣力,雞蛋黃的面條靜靜地躺在那里,油亮地昂著頭,似乎在宣告她是上海傳統降溫食品的代表。
在最近比較受人關注的描寫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小說《繁花》里,也有不少上海市井夏天的味道。畢竟是講人的小說,寫到上海吃食的片段并不多。要么以后我寫一下類似的,感情內容可能寫不出很多,吃的倒是可以“倒出”很多的。
上海冷面是上海人心里最沒有等級的食物了,因為吃冷面必是夏天的規定流程。無非是在澆頭上做些文章,用句我經常說的話“有錢的吃好點,沒錢的吃簡單點,實在不行隔著玻璃窗看看也是蠻好的”。
冷面雖然在家里也能做,調味也簡單,但成品總是不盡如人意。
首先是對于面條的選擇。上海冷面用的面條是上海獨有的小寬面,比蘭州拉面的“韭葉”還要窄,約3毫米寬、1毫米厚。家里做不好的原因就是少了“蒸”這個重要步驟。面條需要先取出,拆散、蒸熟,再下水煮,這樣做出來的面條不散、不爛、不漲、有彈性。現在據說上海冷面的天花板是“四如春”,號稱“風扇冷面”,我有點奇怪:如果不用風扇冷卻用什么?所以第二個步驟就是水里撈出的面條必須迅速地拌上熟油(熟菜油),用四根甚至更多的筷子挑開面條,提起來在風扇的作用下迅速地冷卻。面條就會愈發有彈性,呈現出更漂亮的黃色,而松松彈彈恰好是上海冷面的特點。
其次就是拌面的汁水。與現時北京流行的二八醬不同,上海冷面使用的是純花生醬,極細的那種,香港人多稱之為“幼滑花生醬”。在家里做往往不得要領,非常容易澥。飲食店里一般會多次加入滾燙的開水,剛開始時,醬料的狀態會比原來的更加黏稠,繼續加入,持續攪拌,至呈現類似法國菜醬汁的濃稠度即可。
再次是醬油。單純地使用醬油來拌面肯定是行不通的,各家有各家的做法,有用雞湯調制的,也有幾種醬油合在一起的,總之不會是純醬油。
最后是醋。一定得是上海本地的米醋,鎮江香醋味道過重,而山西醋酸度太高,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終歸還是上海的醋合適。
上海冷面的澆頭在我記憶中的品種倒是不多,多是淡味的食材,冷面吃的就是醬汁拌面的口感、味道,如果澆頭味道重了,反而會搶了滋味。最簡單的澆頭方為絕配,比如銀芽雞絲,再次一級的也是要青椒銀芽來拌。現在的澆頭是照單將湯面澆頭一股腦兒的都加上,說實話真的不是很適合。
大抵上,我去吃的很多食物都會是和情感掛鉤的食物,想吃冷面的心情和冷面店的環境都是我懷念奶奶時想到的一部分。吃了會想,想了就會去吃,與其說是吃飽,不如說純粹就是為了懷念。我總是表面理性,骨子里感性,我覺得人的感情就是這樣,不是輕易就可以放開的。從小奶奶對我的影響巨大,從穿衣、吃飯到做人、做事,我想大家也會有這樣的親人或者愛人存在吧!
時至今日,我還是會在有機會的時候騎著我的“小電驢”,在傍晚的時候穿梭于弄堂之間,仿佛回到即將工作的那一年。轉眼已經30年了,真快!“女神”也已經是大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