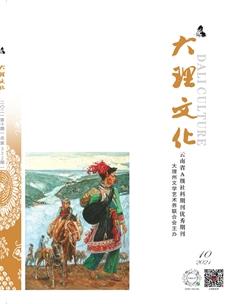你不能假設生活
錢會芬
丈夫的單位今天下午聚餐。獨自吃過晚飯,我洗了個澡,在陽臺上邊玩手機邊晾頭發。就在我準備起身離開陽臺的時候,一個女人進入了我的視線。
此時太陽距離西山頂很近,就像一個遲暮的人,散發著缺乏溫度的光。
那個女人就在這昏黃的天光中遲疑地朝著這個小區走來。不是本地人,我一看就知道,她沒有在一個小縣城常年居住,對一切了然于胸的那種篤定和從容,也沒有鄉下人那種惶惑甚至緊張。她并不急于趕路,而是邊走邊四下觀望,仿佛是在辨別方位。
我正在衛生間梳頭,就聽到一陣敲門聲。就在拉開門那一瞬間,我怔住了,門外站著的竟然是剛才看到的那個女人。
“我就覺得你應該在家。”她說,那口氣仿佛是一個和我一起生活多年,熟悉我生活規律的人。
“你是誰?”我問,“你找誰?”
“哎呀!你還是這樣性急,讓我先進去。”她不滿地抱怨道。
她側身就進了屋,說:“先給我倒杯水,我可是真的渴了。”
我把水遞給她時,她已經斜躺在沙發上了。喝完水,她長呼了一口氣,說:“我去洗一把臉吧,真是風塵仆仆啊!”她站在客廳環視了一圈,就朝衛生間走去。
她是誰?看面容似曾相識,可是我真不認識她。
從衛生間出來,她又深深地斜躺在沙發上,還拉過一個抱枕墊在身后,扭了幾下身子,似乎找到了最舒服的姿勢。
“你可能暫時不認識我,你就叫我隱得了,先聽聽我的故事吧。”我并沒聽清她說的是ying,還是yin,不過為了方便,我就叫她隱吧。
那年我21歲,沒有談男朋友。隱說,因為我不想一輩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我渴望我的世界更遼闊一些。還有就是我希望我愛的人,他要能夠為我打開生命的另一扇窗。于是我決定出去轉轉,我想我未來的愛人應該在很遠的地方,我興許能找到他。
我去了一個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叫梅思麗沙漠。我不清楚為什么聽上去像個女人的名字。出發之前我了解過,這片沙漠面積三萬多平方公里,是一個世界聞名的大沙漠的尾巴那部分,因為面積不大,環境相比也不是十分惡劣,所以常有世界各地的驢友到這里體驗徒步穿越沙漠的感覺。我到達那里的時候,剛好有四名中國人結伴準備行動,三男一女。雖然他們在我來之前就已組成了隊伍,但我發現他們彼此并不熟悉,而且對了解隊友也沒表現出什么興趣。以前看到一個新銳作家說過這樣的話:愛好旅行的人都是無情的人,因為他們知道結束了這一段行程就各自天涯,很快又要去結識新的人開始下一段旅程,久而久之,在他們心中,一切都只是匆匆過客。看來這話不無道理。我加入了他們。我們一行五人是在一個黃昏進入梅思麗沙漠的,當地人告訴我們,晚上走會涼爽一些,這對我們有利。剛進沙漠時還很燥熱,隨著太陽落下夜晚到來,寂靜和黑夜就降臨了。
我邊走邊東張西望,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沙漠,總想找到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東西。當我發現天空中那么大的星星,我驚呼起來:“看,天上結滿了柿子!”可是我的驚呼并沒有獲得回應,隊友們都在悶聲不響地低頭走路,只有一個黑皮膚的男人皺著眉頭瞥了我一眼,就像我的話令他不快似的。好在一個長頭發的姑娘一手扶著那個男人的胳膊,一邊回頭對我說:“節省體力。”我把她稱作蘇吧。蘇說了那四個字后再沒聲響,直到后來分頭行動時。我原以為我們可以在行進過程中分享一些新發現,彼此交流一些想法,可是這些人只是想著向前走,橫穿沙漠,到達對面的目的地。
我忽然覺得隱的故事似乎跟我有某種聯系。我坐到隱的身邊,她所講的絲絲縷縷的背后,一定隱藏著跟我有關的更多秘密。
隱抬起眼睛,仿佛她的目光穿透了眼前的墻壁,穿越了小區林立的高樓,穿越了外面世界的千山萬水,回到了那片沙漠。
她接著講,第二天中午,隨著太陽逐漸升高,氣溫迅速回升到38攝氏度,這對于我們是一個艱難的體驗。我們決定休息一下,等太陽最曬的那段時間過去再行動。沙漠里一片寂靜,舉目四望就是一個個橘紅色的高高低低的沙丘,這些沙丘沉默著一直排列到天的盡頭。帳篷里很快傳來鼾聲。我坐在帳篷外一個角落里,我可不想就這樣去睡覺。前一晚在夜色中,周圍一片漆黑,都沒能看清沙漠的樣子。我極目遠望,眼前仿佛是一片無邊無際的大海,沙丘不過是海面翻卷起的波浪,對!這是海的另一種存在方式。正當我這樣想著時,感覺有人在我身邊坐了下來。就是那個黑皮膚的男人,我就叫他喬吧。喬坐下后,瞇起眼睛看向遠處。
“發現什么新鮮玩意了?”喬說。
“沒有。”我回答。
“那有什么好看的!不睡覺?”喬說著就準備起身。
“我發現這其實是一片海。”說實話,那時我心里還是渴望有人和我說說話的。
喬果真又坐了下來。
“海!你說這是海!這個說法倒不錯!”
“也許這是另一種樣子的海。”
喬扭頭看我,我發現這個皮膚黝黑的男人長著一雙比他的皮膚還要黑的眼睛。當他的目光落在我臉上時,深深地皺了一下眉,仿佛我的表情讓他不快似的。
“走吧,夠了。”喬一邊說著一邊鉆進了帳篷。
我們在前面六天走了將近七十公里,第八天,我們來到了一片洼地。這里矗立著一些石墻,說是墻,只是有一些大致墻的樣子,在這一片洼地里,就像是一個敞開著的肚皮里的一段一段腐爛的腸子。這里應該是一個什么古老建筑的遺跡。腸子在洼地里制造出幾小塊陰涼,讓我們得以坐下來喘一口氣。當我們坐下時,發現墻角處竟然長著幾蓬小草,而且還開出了幾朵小黃花。蘇和喬并肩坐在一起,我看到蘇和另外兩個男人如獲至寶地把小草連根拔起,拍拍土就送進嘴里大嚼起來。進沙漠這么些天,除了啃壓縮餅干就是喝水,任何一種別的味道,對舌頭來說都是一種享受。喬看了看小草,把身子往蘇的那邊挪了一下。在這一望無際的砂礫地上,這些小生命多么讓人憐愛。我趴下去聞了聞,金黃色的小花里竟然還有一股涼絲絲的清苦的氣息。喬轉頭望向我,眉頭又皺了起來。就在我要直起身的時候,突然瞥見草叢中有一塊青綠色的東西,拿起來一看,竟然是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和雞蛋一般大,形狀也像雞蛋一樣一端尖,一端圓,只不過是扁的,差不多有一個手指頭厚。我把石頭拿在手里翻來覆去地看,它不像沙漠里的石頭,沙漠里的石頭質地不太硬,而且都是黃色或者黑色的。這塊石頭質地緊密,放在手里掂一掂,大約有80克左右的樣子,它通體青綠色,卻在中間部分隱約有一道彎曲的、稍顯白色的紋路,就像一片長滿青草的土地上流淌著一條小溪。我把石頭給他們看,喬說:“這是什么?上帝的眼淚!”是的,它太像一滴水,或者說太像一滴眼淚了。
酷熱的天氣,加上每天只吃壓縮餅干和水,缺乏維生素,我們嘴角都起了泡,又疼又癢,心情更加焦躁。那顆石頭一直被我帶在身上。上帝的眼淚!說真的,我很喜歡喬為它取的這個名字。正午熱得無法入睡,當我看到“上帝的眼淚”,仿佛看到一片生機盎然的草地,那些充滿生命力蓬勃生長的草,讓我覺得整個世界那樣遼闊自由,內心深處涌起一種難以言說的感動,我很快就會平心靜氣地睡去。疲憊不堪的時候,我看著那條“小溪”,就會想起我小時村子前面那一條清澈的小河,身上就覺得有了力氣。這顆石頭就像和我有某種淵源,它仿佛能和我內心最隱秘的依賴和渴望相通。
“石頭!青綠色的石頭?”我的自言自語打斷了隱。我一邊喃喃著,一邊努力回憶,就像要從一大堆灰土里扒出童年時的彩色玻璃球。它是否曾經出現在一個我遙遠的夢境中?
隱抬起頭滿眼期待地看向我,就像看一個就要從睡夢里醒來的人。她挪了一下,和我挨近了一些。她為什么這樣看我呢?
她接著說:進入沙漠越深,氣溫越高,空氣越干燥,到第12天下午,我們仿佛置身于一片火海中,最糟糕的是水快要喝完了,而我們在此時迷失了方向。不是迷路,沙漠里根本沒有路。我們躺在一個沙窩里,七嘴八舌,爭論不休。從見到他們那天起,我們從來沒有說過這么多話。蘇說,應該往3點方向走,她記得很清楚,前天經過的那個深紅色的沙包在9點方向。可是回頭去看,那個紅色沙包連影子都看不見。另外兩個男人則堅持往5點方向走,并讓我們相信他們的感覺,而感覺這玩意兒在很多時候不過是自我解嘲的代名詞。我像往常一樣把“上帝的眼淚”握在掌心,那時我真不知道該聽他們誰的。忽然我感到迎面吹來一陣輕風,像天上最輕盈的一縷云彩,輕輕地拂面而過,空氣里似乎有一絲清涼。
“往12點方向走。”我說。
他們都扭頭看我。
“先往12點方向走,前面有水,我們把水儲存夠了再說。”
“你犯迷糊了吧?這四下里一片火海,不可能有水!”蘇說。另外兩個男人則不置可否地沉默。
“剛才從12點方向吹來一陣風,風里有水的氣息,你們沒聞到?”
“犯傻吧?哪里有風?這里怎么可能有水?”一個男人說。
“相信我,前面一定有水。”我一再堅持。
“別聽她胡說八道!如果找不到水,耗費了體力不說,連現在這點水都喝完了,我們就只有等死!”蘇和另外兩個男人說。
就在我們不知道該怎么辦時,一直不吭聲的喬說:“這樣吧,我們分成兩組,我和她(喬指了指我)往12點方向去找水。”喬指了指那兩個男人,“你們倆和蘇一組,但是方向要一致。”蘇想了想說她愿意和那兩個男人一起往5點方向走。
喬對那兩個男人說:“你們一路上要照顧好蘇。”
喬說:“記住,到后天,無論情況怎樣,我們還來這里匯合。”
他們三人走時,喬讓他們帶走了全部的水。蘇臨走時看我一眼,又看喬一眼,她的眼神告訴我,希望和喬一起走的是她。我真不知道她在這十多天里是怎么喜歡上喬的,也許是從她扶著喬的胳膊扭頭告訴我“節省體力”時就開始了吧。
我和喬走了一天,第二天黃昏,又渴又累的我們終于發現了一個小水塘。它在兩堵隆起的狹長的沙丘中間,大約有一百多平方米的水面。當我和喬踉踉蹌蹌地奔過去時,我依稀看到水面閃了一下眼睛。我們喝飽水,把所有能裝水的東西都裝滿了。離開水塘之前,我把“上帝的眼淚”清洗了一下,它身上沾了我多少汗水呀!我和喬急忙往回趕。可是當我們回到沙窩時,并沒有看見蘇他們。沙漠里很少有標志物,有時你往前走幾天,眼前的景物和你剛開始時見到的毫無二致,稍不小心就容易迷失方向。怕和他們錯過,我們只好在沙窩里等。待了兩天后,我們決定往5點方向去找他們。我曾問過喬為什么選擇和我一起,喬說:“在那一瞬間我覺得我應該相信你。”我多次打量那顆石頭,我納悶為什么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突然就吹來一縷涼風,也許這是上帝冥冥之中在拯救我吧!
講到這里,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乎累了。她把期望的目光投向我。我突然覺得手心發涼,就像握著一塊石頭,低頭看,手里卻什么也沒有。
隱接著說,我們一直走,不知在沙漠里度過了多少個白天和黑夜。我們一直沒看到蘇和另外那兩個男人,或許他們已經走出了沙漠,或許他們又走錯了方向,也或許他們已經倒下了。誰知道呢!在這滿世界的沙丘里,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有時甚至沒有意識。到后來,我們甚至把蘇他們給忘了,我們唯一的渴望就是什么時候一抬眼,赫然看見沙漠的邊緣。但是這樣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我甚至懷疑我們根本沒有往前走,而只是在原地兜圈子,眼前的一切都是昨天看到的,除了沙丘還是沙丘,除了死寂還是死寂,那時我想,要殺死一個人,根本不需要用刀或槍,只要把他留在沙漠里。水也快喝完了,干糧也所剩不多,我以為我會永遠留在沙漠里了。喬把水省著給我喝,一天只敢啃手指大一塊餅干。有很多次,我渾身僵直地躺在松軟的沙子上,真想閉上眼睛不再醒來。當我看到“上帝的眼淚”,我想,我不能就這樣死,我一定要活著走出去,我要去尋找那個地方,在那里,草兒恣意生長,小溪自由流淌。在那里,我所有失去的生命力都會重新回到我的身體里,我的生命會重新煥發光芒。想到這些,我就掙扎著站起來,在喬的攙扶下繼續向前走。有幾次我神志不清,哭嚎著要跳進村前的那條小河里洗一個涼水澡,可是那條小河總是我走近一步它就后退一步,我永遠也到不了河邊。每當這時,喬就把“上帝的眼淚”放在我的胸口上,我會慢慢地平靜下來,在他懷里沉沉睡去。
“上帝的眼淚”,它像是我靈魂的棲身之所。
終于在一個晚上,當筋疲力盡的喬攙扶著我爬上一個沙丘時,我們看到遠處移動的燈光,那是車燈,距離我們大約500米左右,說明我們快要走出梅思麗沙漠了。意識到這一點時,我的心撲通撲通狂跳起來,或許是身體長時間處于虛弱狀態,心臟受不了這突然到來的驚喜,我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覺。
當我恢復意識時,我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床上,眼前是白色的墻,我蓋著白色的被子,右手上掛著吊瓶。喬坐在床邊,他也在掛吊瓶,睡著的他雙眉舒展。我的呻吟驚醒了喬,他看到我,眉頭又皺了起來,“你終于醒了!這是診所。”他一邊說一邊伸過沒掛吊瓶的那只手來握住我的手。
“‘上帝的眼淚在哪?”我問。
“扔了。”喬說。
“扔了,扔哪里了?你怎么能把它扔了?”我提高了嗓門。
喬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不扔,我怎么能把你背到公路邊,500多米的路程。”
我沒說話,靜靜地看著他的眼睛,他又皺起眉頭,低聲說:“扔了就扔了,那就是一顆不值錢的石頭。”
我突然明白,眼前這個給過我很多溫情的男人,冷靜、睿智,令我心動,盡管我和他經歷過萬般艱難,經歷過生與死,但能讓他放在心上的,也僅僅是我這一副軀殼罷了,至于我靈魂深處的渴望,他可以像對一顆石頭那樣棄之不顧。他不知道,有些人,他們靈魂的依憑恰恰是一些不值錢的東西。
我問喬:“如果那是一顆比我值錢的鉆石,那么,此時埋在黃沙中的該是我吧?”
喬生氣地說:“沒有如果!生活是不能假設的。”
當我有力氣走出房間的那天,我離開了這個喜歡皺眉的男人,沒有給他留下只言片語。
隱講完這些,嘆了一口氣。
我突然覺得內心有一種深深的失落,仿佛一些我一直不愿意直面的東西突然赤裸裸地擺在我的眼前。我神經質地拉起另一只手,一陣熟悉的溫熱在身體里浸潤開來,是的,在很多時候,我唯有兩手相握,讓他們互相安慰。一低頭,才發現那一只竟然是隱的手。
隱喝了幾口水,平復了一下情緒,接著講:
我走遍了梅思麗沙漠周邊的村莊,四處打聽蘇和另外那兩個男人的消息,可是什么消息也沒得到,也許他們已經永遠地留在了梅思麗沙漠,也或許他們已經回到了原來的生活。
24歲那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姜。他大學畢業6年,搞海洋生物研究,在一個海濱城市有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據說他的父母是搞房地產開發的。我對他的家庭背景不感興趣,也從不過問。由于工作關系,他經常出海,也因為工作關系,他和附近漁村里的漁民混得很熟。和姜熟悉之后,有一次他便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出海。在這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個邊遠閉塞的小縣城,對于海,只是在文字中接觸過,在電視上看過。因此,我一口答應。
我們是坐一個漁民的船出海的,是一艘鋼質的近海機動漁船。啟程時,天還沒完全亮,東邊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抹狹長的亮白色,漁民告訴我們,那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漁船在黑黝黝的海面上滑行,此時的海就像一匹無邊際的黑色絲綢,四周也是一片暗黑,如果不是發動機的聲音提醒我,我真以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幽靈之地。我和姜坐在船頭,看向遠處那一抹亮白色。早春的風很大,吹得衣襟刷刷響,寒冷并沒有減少空氣中的腥味,我努力忍受著一陣陣惡心的感覺,姜扶我坐下,拿出一瓶風油精,滴一點在我的太陽穴上,邊按邊揉說:“就知道你會暈船,事先準備的,別緊張,我第一次坐船也這樣,以后就習慣了。”不知是風油精的作用還是姜的話安慰了我,我真的很快就覺得舒服多了。
東邊天空的那一抹亮白色漸漸變成亮橙色,太陽就要升出海面了。姜指著那些橘色的云朵,激動得像一個孩子。
“快看,那里有一匹馬。哎,看這邊,那朵云像不像奧特曼?”
我問他:“你每次出海都這樣?”
姜垂下眼睛有些羞澀地說:“平時這個時候我就坐在船頭,一邊喝酒一邊看云彩。”接著,姜說:“在海上看云彩和在別處看不一樣,你看四周,沒有山或樹木,就這樣遼闊無邊,看著這些云彩,不知它們將飄向何處,你會想到生命中的很多不確定,很多可能性,這樣想著,你會覺得自己已經離開了物化的世界,你已經接納和包容了一切,和天與海融為一體。雖然你最終還是要回這個世界,但是,當你經歷過這種體驗后,你會發現生命原來可以這樣遼闊、自由!不過,你不會懂這些。”姜說著這話的時候,望向遠方的雙眼既迷離又憂傷。那時,我很想對姜說:“不!我知道,這就是我一直渴望和尋找的。”
“生命的自由與遼闊!”我重復著這句話,又一次打斷了隱。多么熟悉的話,好像一個相處多年的朋友,不知什么原因就疏遠了,忘記了,現在又突然隱約記起。
隱看著我,她似乎在等我繼續說點什么,但我腦海里一片迷霧,感覺有一些東西,曾經很珍貴,但是現在想要抓住,它們卻若隱若現。
隱只好接著說,這個男人,他像一本書,為我的靈魂打開了一扇窗,又像一座燈塔,讓我透過迷霧,看到了光亮。內心深處有一道溫泉噴涌而出,我不禁熱淚盈眶。
“太陽出來了,快看!”姜推了我一下。
喔!一輪橘紅色的太陽就像掙脫了羈絆,一躍而出,那么新鮮,就像剛從樹上摘下的一個碩大的金桔,海面上金光閃閃,就像有一萬條金魚在游動,整條船沐浴在朝陽的光芒中。姜情不自禁地抓起我的手用力舉起來,仿佛要這樣來迎接嶄新的一天。在金色的陽光中,我和姜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隱停了好一陣才又接著講,似乎快要沒力氣了似的往我肩頭靠了靠。我突然覺得我和她是那么熟悉,仿佛她是從我身體的某個地方分離出去的一部分,我跟隨她故事里的喜悅而喜悅,悲傷而悲傷。
姜在客廳里擺了一個很大的魚缸,養了兩條紅金魚。姜很喜歡它們,每天都給它們喂食,有時他會對著魚缸吹口哨。他說,魚能通人性。周末無論多忙,姜都要清洗魚缸,不讓魚缸里有魚食殘渣。從海上回來之后,我和姜就住到了一起。姜很喜歡每天下班回來吃我做的飯,晚上摟著我入睡。姜不止一次說:“你就是上天給我的禮物。”姜給我許多零花錢。姜的父母很有錢,姜不需要依靠工資生活。而我打算慢慢熟悉這個城市后就找份工作,我不屑讓任何男人養活我,包括姜。而姜卻不以為然,他說:“工作會讓你勞累,我不喜歡那樣的你!放心吧,你不工作我們也能過得很好。”姜在那次之后就沒有帶我出過海,他說那些時候海風太大,怕我受不了暈船,他每次出海回來都會給我帶回一個形狀古怪的貝殼,或者一個小巧的海螺。而我還是盼望著春天過完后能和他一起出海。那天,我百無聊賴地在客廳里轉來轉去。姜出海6天了,說要一個星期才回來。這時我看到魚缸里那兩條金魚貼著缸壁游來游去,嘴巴一張一合,像是餓了,我就抓了幾顆魚食扔進去,兩條魚吃完魚食,仍然不停地張合著嘴,好像還沒吃飽,我又喂了幾顆。過了一會兒,只見兩條魚肚子脹得鼓鼓的,肚皮向上浮了起來。這時我才想起姜說過,喂魚食一天最多不能超過4粒,否則魚會被脹死。這下怎么辦?姜回來我該怎么對他怎么說呢?我心里忐忑不安。第7天下午,姜回來了,他習慣性地看向魚缸,魚缸里空空如也。我強作鎮靜地向他解釋,姜還沒聽我說完,就爆發了,他一只手叉著腰,一只手把魚缸拍得當當響,說:“我走時是怎么告訴你的?你沒有好好記著嗎?連這么點事都做不好,你一天在家,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我突然發覺在姜的眼里,我還不如他養的金魚。那晚我早早上了床,姜上床后,像往常一樣摟住我,不停向我道歉,說他連續在海上漂了一個星期,非常疲倦,沒有控制住情緒,讓我原諒他。他從背后溫存地抱住我,吻著我的耳朵說:“我愛你,我也不喜歡和你生氣,我希望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快樂的。”他熱烘烘的男人的氣息繚繞在我的頸間,唇間,我原諒了他。
夏天到來時,我決定出去工作。姜知道后,軟磨硬泡地勸我放棄這個想法。他說,我們現在生活得挺好,我不需要去工作。他說,他喜歡每天下班回到干凈整潔的家里吃我做的飯。他還說,他就喜歡我現在這個樣子。而我依然堅持我的想法,我絕不依靠誰來養活,我要有自己獨立的生活,我要在工作中感受外面廣闊的世界。姜終于大發雷霆。他說,我就喜歡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不安分,既然他能讓我衣食無憂,我就該在家相夫教子,獨立、思想只屬于男人,對于女人來說有屁用,照顧好丈夫和孩子才是女人的本分!
天啊!這是那個在晨曦中和我談生命的自由和遼闊的男人嗎?我現在才明白,他不過是把我當做一個能順遂他心意的傾聽者而已,我從沒有走進過他的內心,他也從沒有接納我。那天清早在船頭,他不是說我不懂這些嗎?當時我竟沒理解他說這句話的意思。在他看來,我永遠也不會懂這些,女人只是缸里的魚,籠中的鳥。他需要的只是我這具作為他社會意義上的女人的軀體,他需要的是我能像他養的寵物一樣順從他,這和喬,又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呢?
我問姜:“如果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就有工作,是否你就不會和我走到今天?”
姜說:“沒有如果,生活不需要假設!”
第二天,我離開了姜的家。臨走時,我給姜留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對不起,魚缸太小!
隱喘了一口氣,用她的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就在那一瞬間,我的腦海里劃過一道閃電,我終于抓住它們了,我想起來了……
我問隱:“你是誰?你到底是誰?”
隱說:“難道你還沒看出來。我是二十多年前離開你的,那時你還那么年輕,滿腦子那么多美好的夢,但你卻不敢跨出一步去尋找,我為你著急,為你惋惜,于是我就替你去了。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可是,原諒我,我沒能替你找到!離開姜后這些年,我碰到過很多男人,可正是他們讓我的希望一點點消失,后來我漸漸覺得,也許喬和姜是對的。
生活就像一條逼窄的隧道,不問出處,不問方向,只要跟著前面的人走,你會獲得安全感,即使偶爾碰到一條岔道,又有幾個人有勇氣邁出一步,走向不可預知呢?既然絕大多數女人都是這樣生活,我為什么不呢?現在,我累了,我回來了。這些年,你過得好嗎?”
“隱!”我干涸的眼里已經流不出眼淚,我緊緊地握著她的手說:“謝謝你!”
我接著說:“我不知道現在自己過得好還是不好,但那又有什么意義呢?”
天色已晚,這時我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是丈夫回來了,就在丈夫進門的瞬間,隱用盡全身力氣和我融為一體。
“剛才你在和誰說話呢?”丈夫問。
沒等我回答,丈夫又說:“怎么不開電視?聽說這兩天正在放一個電視劇,收視率極高,快打開看看。”
我說:“有什么好看的,那是別人的生活。”
丈夫奇怪地看我:“別人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
沉默了一會,我說:“如果剛才我是在和另一個我說話,你相信嗎?”
“沒有如果,人不可能有另一個自己。生活中沒有假設。”丈夫說。
編輯手記:
《進城的大樹》是一篇頗具現實生活氣息的小說,小說里的生活可能就真實地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作者用“進城的大樹”來比喻農村進城來照顧孫輩的老人,生活習慣的不同,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觀念的不同,必然使得這“進城的大樹”雖然有豐富的營養和管護,卻在移植的過程中枝丫、根脈被斬斷,難以吸收足夠的陽光和營養。小說里的婆婆素珍就是這樣,她不習慣城里的生活,和兒子兒媳生活習性的不同導致她離家出走回農村。這可能是現在很多人面臨的現實生活,城鄉的異質性必然導致“進城的大樹”需要更多的理解以及時間的適應,作者用生動形象的比喻和集中爆發的沖突矛盾探討了城鄉不同、習慣不同的兩代人該如何相處的現實問題。
《你不能假設生活》這是一個女人對生活的假設,一個女人與另一個自己的對話,那個敲門而進的“隱”,向“我”述說了兩個故事,在梅思麗沙漠里和喬的故事,在小縣城里和姜的故事,兩個故事都是現實生活的隱喻,一個故事隱喻著靈魂的棲息和被拋棄,“上帝的眼淚”所象征的靈魂終是被拋棄在沙漠里。另一個故事隱喻著生命的自由與遼闊,魚缸象征著生活的牢籠和愛的牢籠,而尋求生命的自由和遼闊必將沖破牢籠。其實,兩個故事都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和假設,那個不速之客“隱”就是另一個“我”,她替我出去尋找和體驗,她替我去過假設的想象的生活,但是生活本身是不能假設的,無論是隱喻的靈魂,還是自由的生命,很多生活的想象都是不能假設的,這便是生命的真實狀態和生活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