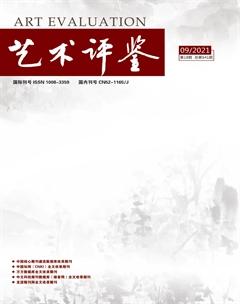從《窮人樂》看大眾的“戲曲自覺”
殷慧娟 張錦程
摘要:1944年,阜平縣高街村村民自編自演的《窮人樂》在晉察冀邊區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農村劇運得益于此,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立足當下,審視《窮人樂》所帶來的經驗,仍值得我們關注。
關鍵詞:《窮人樂》? 群眾? 戲曲意識
中圖分類號:J8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18-0168-03
“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門前唱大戲”。每當念及這首童謠,都會使人想起兒時“看大戲”的情景:俊俏的扮相,鏗鏘的唱腔,炫目的情節,令人印象深刻。
自古以來,戲曲在大江南北廣為傳播,蔚然成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阜平縣的高街村,無論斗爭形式何等嚴酷,無論生活多么貧窮,村民們都會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戲曲的創作、表演與觀賞活動之中。以他們編演的《窮人樂》為代表,在宣傳抗日主張、鼓舞民眾士氣方面發揮了“高臺教化”作用,同時也促進了邊區戲劇運動的開展。時過境遷,當年村民們在演戲、看戲的藝術實踐所表現出的濃厚的愛戲集體意識,有許多歷史經驗值得總結。因為,它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依然有著積極的啟迪之義。
一、高街村劇團與《窮人樂》
資料表明,高街村(今屬河北省)作為抗日工作先進村,有著良好的政治基礎,村干部的抗日覺悟較高。在他們的組織下,抗日救亡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其中,他們遵從村民喜愛戲曲的民風傳統,及時開展了以抗日宣傳為目的的村民戲曲運動。其實,早在1936年該村村民就自發組建了業余劇團,人員當中有半數以上是村干部,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能夠將演劇與識字結合起來,在村民中影響很大。時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晉察冀邊區成立之后,他們在邊區政府的組織下,對劇團的各項業務工作進行了新的提升,結合抗日的斗爭現實,自行創作、表演了《減租減息》一劇。1938年,村劇團又對鄰村的表演劇目予以移植改編,演出受到好評。受此鼓舞,高街村劇團的演劇活動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堅持編演活報劇和歌表演,演自己編的農民戲,將生活與演劇相結合,用新形式表達農民的喜怒哀樂。
在高街村的演藝史上,最值得驕傲的是,劇團在邊區“抗敵劇社”汪洋、張非等專業人士幫助下,自編自演了《窮人樂》一劇。該劇反映了勞動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翻身的經歷。它擷取了從“抗戰”到“大生產”兩個重要的現實情節,藝術地再現了高街在共產黨的帶領下發生的新變化。該劇從創作到表演,均由村民承擔。1944年在晉察冀邊區“第二屆群英會”上演出,好評如潮。
回顧該劇創作,最初的排演過程中由于多數村民——演員缺乏演戲經驗,常會“笑場”,表演缺乏表情,似乎在“做游戲”。因此,張非等人運用戲劇表演的“體驗說”予以誘導,啟發他們從“不要忘記生活”中學會如何真實地將自己的勞動與生活模仿出來。逐漸地,村民們“入戲”了,例如將勞作中的動作真切而藝術化地再現出來,得益此番訓練,為村民們演戲奠定了基礎。
《窮人樂》一劇演出,做到了“真人演真事”,但創作并非一帆風順。起初資料匱乏,張非等人決定將抗戰之前村民受喇嘛剝削的生活作背景,重點放在合作社的“樂”上。可村民認為并未將他們賣兒賣女、逃荒要飯的悲慘生活表現出來。他們說“沒有陰天,就沒有晴天”雖然村民幾次提出修改意見,但都并未被采納。直到1943年在北岳區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被批評“群眾的立場不夠堅定”,經抗敵劇社耐心幫助,村劇團幾易其稿,《窮人樂》終于面目一新,令村民觀后為之一“樂”。該劇融合了話劇、舞蹈、歌唱、快板等形式,演出提高了村民的審美能力,對當地表演人才培養起到了示范作用。總之,由于《窮人樂》將本村民眾受壓迫與翻身解放的情節酣暢地展現出來,村民看戲時更多地將自己融入其中,“看著看著就哭了,哭著哭著就樂了”。村民此番“如是說”,正是其成功的要素,經驗耐人尋味。
《窮人樂》的創作使我們看到,只有以群眾為中心,努力貼近他們的生活,才能真正走進群眾內心,產生群眾喜愛的戲劇。事實上,高街村的抗戰生活由村民搬上舞臺,融于藝術,真切體現了“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哲理。
回顧《窮人樂》的成功,一方面體現了村民可以接受戲劇藝術訓練,村民——觀眾——演員的“角色”轉換,學會了如何創作劇本、如何演戲、如何進行舞臺表演等各項技能,使村劇團成為鄉民的文娛組織,承擔起了鄉村社會政治動員的任務。在藝術上,村民通過熟悉的方言“自己演自己”“本土化”的故事情節更易被鄉親們喜愛。演戲成為群眾表達生活、情感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專業劇團也為自己吸取了新鮮血液,專業人才的后續隊伍不斷擴大。此時的村民,不僅是戲劇的觀眾,也是政策宣傳的對象;村民看戲不僅是一種娛樂,更是一項政治活動。群眾通過戲劇表演了解中共的方針政策,使戲劇轉化成為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
鑒此,1944年12月《晉察冀日報》發表了《沿著<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評論:稱贊該劇“真實反映了高街村群眾從苦難到快樂的翻身過程……它是邊區勞動人民光榮斗爭史的真實反映,是我們執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成就,特別是我們從《窮人樂》中找到了一個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新方向”。為此,中共晉察冀分局做出向高街村劇團學習的《決定》,此舉推動了邊區文藝運動的發展,各村紛紛響應,村劇團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廣大民眾以自己身邊的生活為題材,努力挖掘生活中的典型人事,選擇喜聞樂見的劇種和表演方式,使之成為戲劇表演活動中的主體創造者。
《窮人樂》作為晉察冀邊區演劇活動的一面旗幟,從演員的真實、劇本的真實、再到語言的鄉土氣息,都體現出高街村劇團獨有的特征。高街村劇團在鄉村文藝活動中的引領作用,尤其它用演劇形式武裝群眾思想的經驗,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二、晉察冀邊區的農村戲劇運動
晉察冀邊區的戲劇運動在農村如火如荼地開展著,在此期間,數以千計的村劇團蜂擁而起,農民一躍成為戲劇運動的主體,農村劇運也成為邊區文化建設的一道亮麗風景。村劇團幾乎遍布于晉察冀邊區的各個角落,為當時處于戰爭年代的群眾提供了精神食糧。時過境遷,農村劇運在歷史進程中留存的經驗,是現今文化建設事業發展中不可磨滅的財富。
晉察冀邊區農村戲劇運動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得益于黨的正確領導。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晉察冀邊區敵后根據地的文化建設。在聶榮臻的領導下,晉察冀邊區戲劇逐漸成為群眾文化生活中最活躍的一部分。其中,1939年組織開展的邊區戲劇運動座談會,為戲劇運動在邊區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邊區政府積極響應,并制定相關舉措使戲劇運動得以快速的發展。演劇事業需有經費為保障,邊區政府便多方籌措資金予以支持。同時,各地領導機構在為村劇團提供物質保障的基礎上,將農民的演劇活動認定為正式工作,并給予一定的工資補助。在政府有力的引導下,各村村民積極參與到劇運之中。除此之外,政府組織開辦鄉藝培訓班,培養村民的戲劇才能,為戲劇運動不斷輸送新鮮血液,僅在1940年舉辦的兩期鄉藝培訓班,就有600余人參與。群眾一步步地由觀眾轉換為演員身份,成為戲劇運動的主體。
戲劇運動的形式多樣,街頭劇、活報劇、歌舞劇等均有涉獵。其中,以《窮人樂》為代表的綜合性藝術形式在戲劇運動發展中所占比重較大。不同劇種的演出,滿足了不同群眾的需求,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這些村民自編自演的翻身戲,先是娛樂大眾,使其活躍于群眾中,其次才是教化作用,在歡聲笑語中傳遞著黨的方針政策。各村劇團通過政府部門組織的文藝匯演加強業務提升,促進各村相互借鑒交流。1940年邊區首屆藝術節的成功舉辦,各村劇團接受了政府檢閱。
邊區戲劇運動的開展,除了黨與政府的支持外,也離不開專業劇團的幫助。專業的文藝工作者有著高超的技藝與藝術聲望,譬如抗敵劇社在1942年,臨危受命演出曹禺的《日出》,從劇本、服裝、再到演出,短短三天內完成,向冀中黨委部門展現出了文藝工作者精湛的技藝。文藝工作者在提升自身技術的同時,積極扶持各鄉村劇團,涉及到劇本創作、導演、表演等各方面內容。對于從未接觸過表演的村民而言,劇團成員從“如何入戲、如何表現”等方面進行引導。如西北戰團戲劇組成員在1940年,唐縣、完縣、繁峙縣開辦了三期的“鄉村藝術干部培訓班”,培養了數百名的文藝青年骨干。之后,各文藝骨干回到各村再對村民進行培訓,形成了一種循環,源源不斷的戲劇人才涌現在晉察冀邊區。
三、建設與時俱進的“村劇團”
村劇團與戲劇運動在抗戰時期得以興盛,不單是因為它配合了宣傳抗日主張,更因戲劇源于生活,深受群眾喜愛之故。
如今,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形成于民族解放戰爭年代的“村劇團”及其經驗,是否還有其本質屬性與當代價值,它在新農村建設中又該如何發展。筆者以為,“村劇團”雖處時代不同,但其本質尚未改變。建設村劇團的目的,不僅在于“樂與政通”的功能論,對滿足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傳承傳統文化也有著重要意義。
但是,目前“村劇團”在許多農村的發展式微,形勢不容樂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戲曲受重視的程度衰減,戲曲人才流失較重;另一方面是農村劇團組織與領導的缺失。所以,我們是否可以借鑒內蒙古“烏蘭牧騎”的經驗,以此方式建設現代的“村劇團”。
“烏蘭牧騎”是我們熟悉的現代之詞,即“紅色文化工作隊”。其特點是牧民自己組織小型文藝宣傳隊,通過就地取材、自編自演等形式表現農牧民喜愛的歌舞節目。該組織自1957年問世以來,常年活躍于當地牧區,為群眾送去歡樂。立足當下,建設新時代的村劇團,“烏蘭牧騎”的經驗值得我們關注,其顯要處,在于長期駐扎村屯,且鄉風民情濃厚。
常駐本村的“烏蘭牧騎”,對于培養村民的審美情趣、陶冶情操、教育思想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本村群眾而言,常駐劇團以周邊的人或事編寫劇本,配以當地劇種,選取本村能演、會演的村民演劇,將《窮人樂》“真人演真事”的模式搬上舞臺。其次,每個村若有劇團,可便于村民現場觀看,逢年過節,可在村中搭臺演出,村民聚集在村口觀看演出的場景,似一種濃郁的鄉愁。
再言之,若村劇團常駐在每個村莊,對于戲曲人才的培養不失為一種新方式。因為村劇團從劇本的選擇、編排至最終演出,均需由劇團人員親自完成。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編劇人員、演出人員、舞美人員都會在劇團的實踐中不斷更替,有助于各種戲劇人才的培養。
簡言之,現代村劇團的建設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對傳遞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是一種易于農民群眾所理解、接受的形式,通過唱、念、做、打對其進行高臺教化之意;另一當面,對當地村民而言,是一種審美能力的提升。村劇團常年“駐村”演戲,時間久之,耳濡目染,可陶冶村民情操,提高見識。此外,鄰村間交換舉辦“文藝匯演”。以匯演形式,組織各村劇團參與,一則激發村劇團的演出熱情,促使村劇團更好的創作;二則各村之間相互“競爭”,可從對手身上學到更多技藝,所謂“取長補短”。
如今,加強鄉村劇團與戲曲藝術建設,不僅能帶來審美愉悅,更是傳播思想、團結群眾,以娛樂作為鄉村建設的社會導向,是引導中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發展的需要。簡言之,建立現代村劇團,不僅是對傳統戲曲、民間音樂的保護,更重要在于村劇團作為藝術傳遞的主體,從劇本選擇、制作、演出都由村民自己完成,可促進各類專業性人才的發展。借助村劇團,村中年邁的老人也能更迅捷、直暢地了解黨的新政策,明晰社會發展的新面貌。
梳理高街村劇團與《窮人樂》的創作,為現代村劇團建設增添了些許經驗。村劇團的建設,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被忽視。2018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傳承發展提升農村優秀傳統文化……支持農村地區優秀戲曲曲藝……等傳承發展”。可見,發展農村戲曲藝術,村劇團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建設村劇團并使之成為文化建設的有力支撐是切實可行的。
參考文獻:
[1]張非,汪洋.《窮人樂》的創作及演出.張非.偏套集[M].三樂堂編印,2008:27.
[2]韓朝建.鄉村劇團與社會動員-以1944年河北阜平縣高街村《窮人樂》的編演為中心[J].民俗研究,2018(03):129-139.
[3]劉雙雪.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窮人樂》的創作及影響[J].北方音樂,2018(11).
[4]黃娟.傳統戲曲與新時代農村文化建設——以晉北道情的發展現狀為例[J].晉陽學刊,2019(04):142-143.
[5]周維東.被“真人真事”改寫的歷史—論解放區文藝運動中的“真人真事”創作[J].中山大學學報,2014(02):65-73.
[6]王林芳.《窮人樂》:群眾文藝運動發展的新方向[J].黨史博彩,2020(08):6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