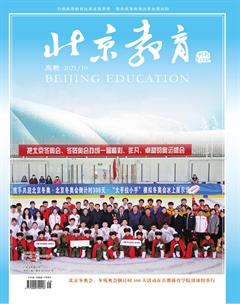打造國際交往中心:大學國際化發展的高階階段
吳偉 樊曉杰 鄭心怡 陳艾華
摘 要:國際化正逐步走進大學功能體系的核心,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教育中樞”就充分證明了這一趨勢。不少地區借助若干世界一流大學才得以匯聚全球范圍內的創新資源,而世界一流大學也需要基于全球視界才能取得卓越的學術地位。在國際化的高階階段,大學將展現出作為知識交流中心、智力匯聚中心、創新輻射中心的樞紐角色,成為“國際交往中心”。我國高水平大學應把建構國際交往中心嵌入大學發展全局,實現“走出去”與“引進來”戰略相結合,實現與所在區域的深度協同。
關鍵詞:國際交往中心;高等教育國際化;教育中樞;知識交流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暫時阻遏了跨境活動,但高等教育全球化仍是大勢所趨,以人才、知識、技術等為核心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已經成為大學發展的核心議題。科爾(Clark Kerr,1990年)指出,國際化是時代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高等教育應在立足民族化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國際化進程。[1]近年來,國內大學高度重視推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從規劃制定、機構設立、人員往來、平臺搭建等多個方面發力,“推進國際交流合作”也被列為“雙一流”建設的五大改革任務之一。同時,國內外頂尖大學也紛紛加快了辦學的全球布局。泰晤士全球大學排名前50大學中的大多數都制定有國際化相關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文本。[2]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13所大學在2021年高校國際化能力建設研討會中明確提出新的國際發展戰略,擴展全球布局的規劃。例如:清華大學將“十四五”規劃編制與全球戰略2030遠景規劃相結合,著力提高學校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聲譽;北京大學制定了國際發展推進途徑,構建全球互聯體系。[3]可見,國際化理念已在國家政策、院校戰略兩個層面得到貫徹,成為推動中國大學走向世界舞臺的巨大力量。
國際交往中心概念的提出
隨著國際交往的日漸頻繁和深入,大學的“界面”地位突顯出來,正成為國內外人才、知識、信息等的交匯、流轉樞紐和國家、區域創新競爭力的重要依托。大學國際化水平的階段演進,既源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在驅動力,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的客觀結果。大學國際化從初期增進文化理解的“偶發型—工具性”階段,發展為經濟驅動的“共識型—機制性”階段,并進一步演進為全面國際化的“綜合型—國際交往中心”階段。[4]在國際化的高階階段,大學主動承擔強化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的角色和功能,并帶來其所在區域國際化程度的極大提升。
從歷史的角度看,大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國際化特性,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真正新穎的是國際化在當代大學中所產生影響的深度和廣度”。[5]可以說,從最早的大學一直到中世紀大學,國際交往是以文化傳承為主“偶發興趣”的結果。[6]現代大學制度的形成和現代科技知識的傳承,推動大學國際化進入新階段。這種知識的普遍性延宕至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入的19世紀中葉以后,以探索真理和發現知識為核心動力。[7]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日益緊密,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知識交流的便捷化,圍繞技術、人才而開展的大規模國際交流與合作在大學發展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學通過人員國際交往、信息交流、國際技術援助和合作,吸收、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和辦學模式,從而達到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推動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的目的。這一階段,高等教育國際化成為國際交流的重要工具。[8]
進入21世紀,以大學排名為代表的學術評價話語體系日漸興盛,使得基于國際可比較指標的國際化表現日漸成為許多大學努力的目標,甚至不少大學排名的核心指標就是大學在國際化維度上的表現。外在因素驅動著大學管理主義導向下的辦學國際標準追逐,推動大學國際化進入了以國際學術合作為主的“共識型”階段。眾多世界一流大學以全球為視界,追求卓越的學術地位,如在國際化進程中,頂尖大學集聚域內外人才、智力、設施、平臺等各類創新資源,為更大物理或行政區域的國際交往提供交流空間、交流平臺和交流資源。[9]
大學與地區發展相互推進的過程又推動了所在地區的人才聚集和經濟發展。換句話說,世界一流大學像磁鐵一樣,吸引著相隔萬里的人以及人的智慧,如擁有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硅谷以及擁有麻省理工學院的波士頓地區,都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10]與此同時,大學的積極行動使其敏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并在其間獲得更多有形無形的資源支持,充分融合政策、科技、人才、資本、金融等創新要素,進而搭建以自身為核心的海內外政產學研創新生態圈。
大學國際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
國際交往中心往往被認為是國際化大都市的重要功能之一,意在強調其作為鏈接全球的角色定位。這種城市一般表現為國際性機構眾多、國際交流活動頻繁、國際化服務設施完善等特征。事實上,大學自身塑造的國際交往中心角色也正是伴隨著國際化大都市國際交往中心功能不斷凸顯而產生的。
20世紀80年代,伴隨跨境教育的產生而出現了“教育中樞”(Education Hub)概念,這可以說是大學國際交往中心的典型表現。高等教育國際化領域著名學者簡·奈特(Jane Knight,2011年)將教育中樞定義為一項有計劃地建立集教育資源和各類國際參與者于一體的龐大集群體系,而這一集群體系戰略性地參與跨境教育、培訓、知識生產和創新活動。[11]教育中樞強調以政府主導,境內外教育資源與所在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耦合,以解決亟待破解的地區發展實際問題。它的出現提高了該地在區域內外的聲譽、競爭力和政治地位。根據政策出發點和動機不同,教育中樞可劃分為:學生中樞、人才中樞、知識/創新中樞。[12]在“國際交往中心”階段,大學扮演推動自身發展乃至所在區域的國際交流與融合的重要樞紐,成為國際間知識傳播、人才流動、資源交互的重要載體。借鑒上述教育中樞概念,本文從三個維度來認識大學國際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
1.知識交流中心
大學自身作為知識密集型組織,其自身特性會塑造出獨特的大學知識生產方式,發揮推動知識的國際傳播、交流與共享的重要作用。克拉克·克爾(2001年)把早期學習的國際化劃分為新知識流動、學者的流動、學生的流動、課程內容的流動四個方面。[13]與傳統大學國際化相比,國際交往中心階段的大學將會更注重促進隱性知識方面的交流:人才培養上,既通過引進國際通用的教材、開展學分互換的學習交流項目以及構建國際化的課程體系,讓學生掌握國際前沿的顯性知識,也通過開展高水平人才聯合培養、建立全球實習實踐基地、設立分校等方式,讓學生獲得真實的學習體驗,培養學生國際化視野;科研合作上,通過搭建雙邊或多邊的聯合實驗室、聯合研究院等科研平臺來促進知識的協同共享,進而產出具有高影響力的國際合作成果,攻克國際性難題;人才交流上,既支持師生參加重要國際學術會議,也邀請其他高校專家學者開展講座,促進知識傳播等。
紐約大學已構建起龐大的全球教育體系,它在全球6個洲14個主要城市建立了11個海外學習中心和紐約、阿布扎比、上海三個有學位授予資格的校園。紐約大學的全球教育體系確保學生在同一個體系中自由流動,為學生提供數量龐大的課程進行選修,課程體系全球對接,師資水平、科研資源與學生服務系統全球統一。[14]與紐約大學推動學生在各分校交流學習的模式不同,哥倫比亞大學橫跨5大洲建立了8個全球中心,不僅與全球中心所在國家、地區和社區建立更有意義、更加深遠的聯系,而且還推動了其自身教育產業的發展。全球中心教育模式因地制宜,如哥倫比亞伊斯坦布爾全球中心重視與當地其他機構的合作,向當地輸送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人才和想法;哥倫比亞全球圣地亞哥中心開設有學分的課程,致力于促進教師在當地開展研究。[15]
整體來看,國際交往中心階段的大學將通過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壯大國際師資隊伍、開設全球課程、主導或參與國際大項目、吸引國際一流大學到本國開設異地校區或聯合辦學、開設國際雙學位、構建國際認證學分互認機制、牽頭發起成立國際組織、承辦國際活動、引進高層次和頂尖人才等,將國際化落到在本地實施合作項目、搭建平臺載體等知識交流的實質層面。而從強調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到推行優質國際教育,其實質是從單向吸收到雙向互動的轉變。
2.智力匯聚中心
大學往往通過投入資金、搭建舞臺、依托學科優勢等多種方式匯聚全球智力資源。阿特巴赫(2010年)認為,大學發展一直受到國際趨勢的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扮演一個更大的國際學術機構、學者和研究的共同體。[16]與傳統大學國際化相比,國際交往中心的大學更注重高端學術人員的雙向互動:人才培養上,積極推動“生源國際化”,通過擴大國際學生招生規模、設立獎助學金補貼、制定優惠政策、改善辦學環境等措施來吸引國際學生,不僅提供職業培訓課程給與國家優先發展產業相關的國際勞動力,而且鼓勵國際學生和勞動者在完成學業或培訓后留在東道國就業;科研合作上,既通過各種靈活方式著力引進一批活躍在國際學術前沿、滿足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一流學者、科學家和創新團隊來進行聯合攻關,也鼓勵教師組織或參與對區域性和全球性重大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為解決全球性難題貢獻力量的同時提升學校科研實力、國際競爭力和聲譽;人才交流上,既鼓勵教師前往國際名校訪學和進修,也注重吸引國際一流專家學者來訪問交流、開展合作研究和擔任學術領導。
悉尼大學通過“戰略性招聘工程”(Strategic Recruitment Project),一方面,向全球重金招攬世界一流科研領軍人才和具有潛力的優秀青年人才;另一方面,破除世界一流人才引進壁壘,建立更加靈活的家庭友好型職業發展制度和研究平臺,日益發展成為匯聚國際頂級學術力量的重要依托。此外,悉尼大學聯合墨爾本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昆士蘭大學等其他澳洲高校聯合成立澳大利亞高校技術種子投資公司(Uniseed)天使基金,為早期創業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與澳洲國立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悉尼科技大學等其他高校一起創立Cicada 孵化器,助力科研成果轉化。
國內一流高校也不斷探索和打造國際智力匯聚平臺。浙江大學利用國際聯合學院這塊“試驗田”,加快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道路。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與多個國際合作伙伴共建若干個聯合學院,首創“一對多”的機構性合作辦學模式。以自身的主流優勢學科,如生物醫學、電氣工程、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土木工程等專業,與英國愛丁堡大學、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帝國理工學院等頂尖院校開展深層次科研合作,實現工學、生物醫學、生物醫學工程(BME)交叉等研究板塊初步形成,協同推進長三角區域產業在科研、醫療、教育等領域一體化合作。
在國際交往中心建構中,除教育本身的國際合作外,潛藏在國際科學研究和學術合作更多領域的雙向融合更加重要。海外的“引進來”和本校學生的“走出去”,表征智力在國家間以大學為載體的深度交流。聯合培養、資源融合和產業合作都可以充分體現國際交往中心的智力匯聚功能。
3.創新輻射中心
國際化過程中,大學尤其是頂尖大學充分整合和集聚政府、域內外企業、科研院所、其他大學、非政府組織等多主體的學術資源,輻射國家和地區科技創新發展。與傳統大學國際化相比,國際交往中心階段的大學更注重其對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創新輻射效應:人才培養上,瞄準國家和區域戰略發展需求,與國際知名企業、一流科研機構開展聯合培養,旨在培養能夠應對創新需求的高水平智力人才;科研合作上,通過建設科技園區、創新孵化器等,與頂尖大學、企業和科研院所共同搭建創新平臺或共同開展國際合作項目,進而取得原創性發現和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突破,同時注重科研成果轉移轉化,擴大科技成果的輻射范圍,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知識源泉;人才交流上,既注重吸引與區域經濟發展迫切急需的國際上各領域、各行業的人才資源,也鼓勵師生加強與產業界、非政府組織、科研院所的互動,充分挖掘潛在智力引進對象。
在新加坡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的推動下,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為國內外前沿領域資源的樞紐,主動對接國際資源并發生“綜合化合反應”,進而推動創新活動的突破和迭代升級。面對20世紀末全球競爭、國家經濟發展的轉型和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形勢,新加坡國立大學在1997年提出明確定位為“全球化知識企業” (Global Knowledge Enterprise)的新目標。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開展技術攻關,借助跨國公司掌握研發的核心關鍵技術,再經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自主創新和集成創新。[17]
除主動對接區域產業需求外,主動服務于國家戰略是體現大學在這一階段的角色。《MIT本科教育全球教育機會》報告中,MIT本科教學教務主任丹尼爾·黑斯廷司(Daniel E.Hastings)提出MIT作為在美國大學以及世界科技前沿占據“鰲頭”地位的大學。[18]在2017年發布的《MIT全球戰略》(A Global Strategy for MIT)中指出,開展國際化工作并取得國際影響,對于麻省理工學院為國家和世界服務的使命至關重要,并強調了全球性戰略、以國家利益為重等國際合作八項核心原則。[19]
國際交往中心階段的大學可以充分發揮人才匯聚、突破創新的功能,特別是當下中外交往的阻隔和科技創新競爭的演變,使得大學作為民間組織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功能空間,主動推動國際國內的資源與需求緊密聯系和有效對接,支撐知識、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開展跨境流動,尤其在國際公共領域,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疫情防治的合作交流,可以逐步化解或打破競爭領域壁壘困境。
塑造國際交往中心的基本路徑
當前,人類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政治、經濟、文明版圖正在被重塑,錯綜復雜的跨國行為體被激活,城市已成為重要的次國家行為體,而大學也在扮演著“次國家”行為體的角色。在國際交往中心階段,大學有助于提升其自身及所在區域的國際形象、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本文立足大學國際交往中心的內涵,結合典型的區域教育中樞建設、部分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及部分頂尖大學國際化的成功經驗,提出大學建構國際交往中心的基本思路。
第一,將建構國際交往中心嵌入大學戰略發展的全局中。在這一戰略之下,大學應將服務國家/區域戰略需求作為國際化發展的核心理念,在扎根所在城市或區域發展的基礎上鏈接全球。大學主動瞄準對接國家/區域全球化戰略需求來制定國際化戰略,不僅可以獲得更多有形無形的資源支持,而且通過“借力打力”的方式幫助大學在技術、知識、人才、資本等創新資源的交互中塑造國際化中樞地位。同時,需要跳出“孤身作戰”思維,放眼國內外尋求有利資源,借助國內外一流大學、科研院所、政府、領軍型企業、國際組織等全球合作伙伴的力量,來推進國際交往中心和多重疊加平臺的構建。
第二,大學要注重“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在大學國際化的高階階段,隨著高等教育綜合實力的提升和國家對外開放格局的演進,亟待大學在鏈接全球資源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從本質上說,這種“引進來”不但是資源的引進來,更多還體現在話語體系的建構和主導權的獲取這種深層次上的“引進來”。在“走出去”辦學層面,實質上也是吸引全球創新資源的重要手段,甚至承載著文化、科技、經濟等方面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重大使命。
第三,大學要實現與所在區域的深度協同發展。大學要推動不同國別區域大學之間的互通有無、優勢互補,以國際化工作力量的協同、國際合作網絡的共享以及國際交流合作活動的共同實施,實現集約投入、效應放大的雙重目的。因此,大學要緊密對接所在區域的國際化戰略,將大學國際化融入區域國際化,并與所在城市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最大程度上發揮校地協同效應。這種廣泛深入的合作不應限于合作雙方自身發展需要,還應通過合作雙方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推進地區之間、合作組織與地區其他組織之間的合作交流,助力區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國際化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甚至正在走向大學發展框架的中心位置。尤其在當今全球化和網絡化的開放環境下,頂尖大學在有組織、有計劃地推進國際化過程中,不斷匯聚著各類學術資源,逐漸發展到國際交往中心階段,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人才培養孵化器、智力匯聚策源地、政產學研發動機的巨大作用。國際交往中心旨在強調大學作為國際合作與交流中的中立第三方,溝通各國、各界的知識、人才和話語,并進而在文化層面上推動相互理解與包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或許是在扁平化、泛在化時代,大學學術中心地位不斷受到挑戰情境下,大學不斷提升自身合法性的重要努力空間。
本文系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產學研協同創新對科研生產力演化的作用機制:基于浙江高校的分析”(課題編號:LY20G030027)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KERR C.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The 1990s[J].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990 (70): 5-17.
[2]韓雙淼,鐘周.一流大學的國際化戰略:一項戰略地圖分析[J]. 復旦教育論壇,2014(2):10-16.
[3]清華大學.高校國際化能力建設研討會在線舉行 [EB/OL]. (2021-01-04)[2021-08-20].https://news.tsinghua.edu.cn/info/1003/84352.htm.
[4]邱延峻.大學國際化的發展模式、演進歷程與歷史經驗[J].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1-7.
[5]MOK K H. Questing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Asia: Critical reflection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7, 11(3-4): 433-454.
[6][8]顧明遠. 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趨勢和經驗[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5):26-34.
[7]胡建華. 高等教育國際化與中國模式[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3):1-6.
[9]金雷.美國大學的國際化[N]. 光明日報,2017-12-20(15).
[10]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s international profile[EB/OL].[2021-09-07].https://www.ox.ac.uk/about/international-oxford/oxfords-international-profile?wssl=1, 2019-12-1.
[11]KNIGHT J. Education hubs: A fad, a brand, an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5(3): 221-240.
[12]KNIGHT J.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hub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ross border education[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 Springer, Dordrecht, 2014: 13-27.
[13]克拉克·克爾.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歷史—21世紀的問題[M]. 王承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5.
[14]上海紐約大學.紐約大學全球教育體系 [EB/OL]. (2019-12-18)[2021-08-20]. https://shanghai.nyu.edu/cn/page/niu-yue-da-xue-quan-qiu-jiao-yu-ti-xi.
[15] FASHMAN A. 哥倫比亞大學的全球中心戰略優先考慮參與,而不是紐約大學的單向知識交流[EB/OL]. (2019-12-20)[2021-08-20].https://www.columbiaspectator.com/news/2015/10/08/columbias-global-center-strategy-prioritizes-engagement-over-nyus-one-way-exchange/.
[16]菲利普·阿特巴赫,利斯·瑞絲伯格,勞拉·拉莫利. 全球高等教育趨勢—追蹤學術革命軌跡[M]. 姜有國,喻愷,張蕾,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0:142-160.
[17]卓澤林, 王志強. 構建全球化知識企業:新加坡國立大學創新創業策略研究及啟示[J]. 比較教育研究, 2016(1):14-21.
[18]許軍華, 邱延峻, 蒲波.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化戰略特征分析及其啟示[J]. 江蘇高教, 2014(2):70-73.
[19]LESTER R K. A Global Strategy for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B/OL].[2021-09-07].http://web.mit.edu/globalstrategy/.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