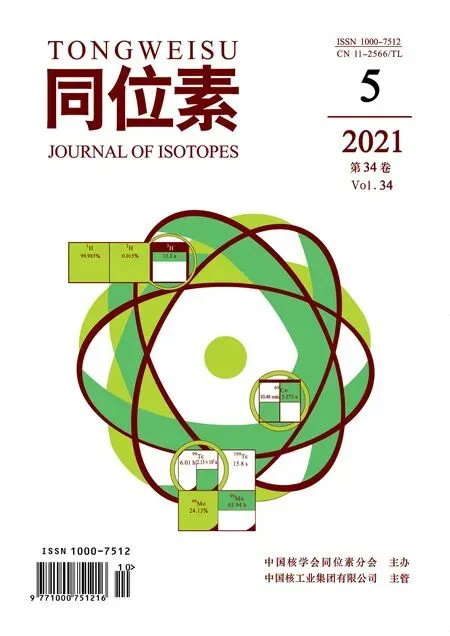Tau蛋白顯像劑的研究進展
于 倩,李鈺瑩,彭 程
(1.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 放射學與核醫學科,北京 100053;2.放射性藥物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北京師范大學 化學學院,北京 100875)
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作為一種進行性發展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是一種最常見的癡呆形式,約占癡呆疾病的60%~80%。其臨床癥狀主要表現為記憶和認知功能受損,日常生活能力持續減退并常伴有神經障礙,被認為是威脅老年人生命健康的主要“殺手”之一[1-2]。目前,AD的致病機理尚不明確,且無準確的診斷手段和有效的治愈方法。Tau蛋白異常磷酸化假說[3-4]在近年來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該假說認為Tau蛋白的異常磷酸化致使其生物功能受損,大量異常磷酸化的Tau蛋白在神經細胞內聚集纏繞,最終導致神經突觸損傷和神經元死亡。此外,實驗數據表明,相較于Aβ斑塊,高度磷酸化的Tau蛋白在腦內的聚集情況與AD的神經元退行和認知功能衰減具有更好的相關性[5]。因此,借助核醫學影像這種非侵入式的監測方法,實現腦中Tau蛋白含量的檢測,對AD早期診斷以及探究疾病的發展情況都具有重要的醫學價值。
正常生理條件下,Tau蛋白通過幾種不同的氨基酸修飾翻譯途徑調控蛋白質的功能。例如利用氨基酸的磷酸化修飾調整微管蛋白的穩定性和聚合性,進而調節和穩定細胞骨架。然而,當氨基酸序列在修飾表達的過程中出現高度磷酸化的異常現象時,Tau蛋白的生物學功能紊亂或喪失,導致Tau蛋白從微管蛋白上脫落,在細胞內發生堆積。大量高度磷酸化的Tau蛋白在神經元細胞內的堆積使得氨基酸序列發生β-折疊,這種錯誤的折疊方式導致蛋白自身聚集形成兩種不同的超微結構(雙螺旋細絲(paired helical filaments, PHFs)和直線型纖維絲(straight filaments, SFs)),最終形成不溶性的神經纖維纏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 NFTs)[6]。神經元細胞中微管結構的破壞,造成了軸突轉運受損和突觸丟失等細胞生物功能損傷,進而發展成AD這種神經退行性疾病。目前,已報道的Tau蛋白顯像劑同NFTs的結合方式大多是通過與β-折疊所形成的疏水空腔相互作用形成氫鍵[7]。值得注意的是,AD的另一個重要生物標記物Aβ斑塊也含有相似的β-折疊疏水結構。與Aβ斑塊不同, Tau蛋白主要存在于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和少突膠質細胞的內部[8-9],且蛋白濃度遠低于Aβ。
因此,相對于Aβ 類示蹤劑的開發,構建靶向于Tau蛋白的顯像劑應滿足更嚴苛的要求。首先,示蹤劑應當具有可靠的生物安全性;其次,相對分子質量必須足夠小(≤ 600 Da) 且脂溶性適中(logP=0.9~3),確保其能快速穿過血腦屏障和細胞膜,同細胞內的Tau蛋白結合;第三,示蹤劑應當對Tau蛋白具有高親和力和選擇性,在腦內的非靶結合低,非特異性結合少;最后,示蹤劑具有合適的藥代動力學性質和生物體內較好的穩定性。可以快速從正常的大腦中清除,且無放射性代謝產物重新進入腦內干擾顯像[10-12]。
1 Tau蛋白核醫學顯像劑的研究現狀
隨著核醫學顯像技術的發展,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single photo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顯像的技術手段能夠實現對疾病的早期檢測、“實時”監測和治療效果的評估。目前,已有多種靶向于Tau蛋白的分子探針被相繼報道,其中一些Tau-PET顯像劑已經進入臨床探索階段。此外,SPECT類的分子探針,由于其具有核素價格低廉、獲取方便、藥物制備過程簡單等優勢,近年來也受到廣泛關注,具有選擇性的Tau-SPECT探針被陸續發現。本文針對目前報道的PET/SPECT類Tau蛋白顯像劑進行歸納和總結,分析這些分子探針的化學結構和生物性質之間的關系,期望對Tau蛋白顯像劑的開發和臨床應用提供新的思路。
1.1 PET類分子顯像劑
從第一個Tau-PET顯像劑[18F]FDDNP[13-14]被報道至今,關于靶向于腦內Tau蛋白的PET類顯像劑的研發工作已開展二十多年。這些探針依據結構特點和發表時間先后被分為一代分子探針和二代分子探針。例如,以喹啉類衍生物、苯并咪唑-嘧啶衍生物和吡啶二烯-苯并噻唑類衍生物屬于一代分子探針,而吡咯-吡啶類衍生物則屬于二代分子探針。其中,部分生物性質優良且標記方法簡單高效的分子探針已進入臨床實驗階段(詳見表1)。

表1 進入臨床實驗階段的Tau-PET探針Table 1 Tau-PET tracers in clinical trials

續表1
1.1.1喹啉衍生物(THK系列) 日本東京大學的Yukitsuka Kudo團隊通過高通量的藥物篩選,發現喹啉類衍生物在體外神經病理學染色實驗中能清晰的標記出腦切片上的Tau蛋白,并且具有良好的選擇性。之后,為了進一步提高探針的選擇性,對喹啉衍生物的結構進行了進一步的化學修飾,報道了一系列苯基喹啉類衍生物(THK系列)用于AD患者腦內Tau蛋白的檢測。最早發表的化合物[18F]THK523[15]在人體PET的實驗結果表明,它能夠特異性結合AD患者腦中的Tau蛋白,然而較高的白質攝取為臨床醫生的圖像讀取和病情判斷增添了困難。此外,更多的研究數據表明,探針在腦內還存在其他的非靶攝取并且穩定性較差,無法滿足PET顯像的要求[16]。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利用同一個化合物做了多種不同Tau蛋白類型的親和力測定,結果表明體外人工聚合的Tau蛋白由于其自身的環境和氨基酸序列的影響,并不能完全模擬人體內的Tau蛋白沉積(NFTs),且親和力數據存在較大的差別(人工聚合Tau蛋白親和力為1.67 nmol/L,AD腦勻漿中的AD-PHF的親和力為86.50 nmol/L)。因此,體外的親和力測定結果只能作為篩選探針的參考指標,探針親和力和選擇性的評價仍需要更多元的評價手段還原更真實的蛋白環境。
該團隊再次優化化學結構,同時對位于喹啉環上6位的烷基和苯環側鏈的取代基進行修飾,得到了[18F]THK5105和[18F]THK5117[17]。高水溶性的氟丙醇側鏈的引入極大提高了探針對Tau蛋白的選擇性,同時N-甲氨基的引入也提高了探針對Tau的親和力和選擇性。人體PET顯像結果表明,這兩種探針均能有效區分AD患者與正常對照組,然而二者在腦內的清除速率過慢,使得探針的進一步臨床應用受阻[18-19]。
為了進一步提高探針在腦內的藥代動力學性質,用脂溶性更小的吡啶環替換THK5317中的苯環得到了THK5351[20]。又對氟丙醇側鏈進行手性碳原子的拆分,通過實驗發現,S構型的THK5351藥代動力學性質優良,腦白質的非特異性攝取低,顯像信噪比好,更有利于臨床診斷的應用[21]。
大量的臨床PET圖像顯示,THK系列探針都與腦內紋狀體中的單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 MAO)存在較高的非靶結合,尤其是單胺氧化酶B (MAO-B)。MAO-B在腦內的含量隨年齡增長而增多,而AD的診斷大多是針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因此該系列探針過高的非靶結合嚴重影響了AD診斷的準確率[22-23]。
1.1.22-苯基喹喔啉衍生物([18F]S-16) 2017年,北京師范大學崔孟超團隊報道了3對具有光學異構的18F標記的2-苯基喹喔啉衍生物[24]。該工作在之前該課題組報道的2-苯基喹喔啉骨架結構[25]的側鏈上引入具有手性羥基的氟丙醇側鏈,使探針在識別β-折疊的基礎上增加水溶性,從而提高探針對Tau蛋白的親和力和選擇性,改善體內藥代動力學性質。通過測定穩定的氟代化合物與3個特異性結合位點的競爭性配體([3H]THK523,[3H]T807和[3H]PIB)在AD人腦勻漿中的放射性競爭結合實驗,定量說明了探針的親和力,其中S-16表現出了對Tau蛋白的高親和力以及選擇性(Ki=10.3 nmol/L,選擇性=34.6倍)。AD人腦切片的放射自顯影結果表明,[18F]S-16可以特異性的與轉基因小鼠(rTg4510)和AD患者腦切片上的NFTs結合,并且得到了探針自身的體外熒光染色和AT8抗體的免疫熒光染色的結果確認。小鼠體內的藥代動力學研究表明,[18F]S-16在正常小鼠腦中穩定且無放射性的代謝產物干擾腦部放射性信號采集,能夠快速穿透BBB并且從正常小鼠腦內快速清除(brain2 min=(10.95±1.29)%ID/g, brain2 min/brain60 min=6.5),同時在小鼠體內不存在脫氟現象。經過前期系統的評價,[18F]S-16滿足作為Tau-PET顯像劑的需求。目前,[18F]S-16在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參與完成以“A/T/N”為研究綱領的核醫學顯像檢查,與[18F]FDG和[11C]PIB在同一條件下對患者進行PET-CT顯像,綜合診斷患者的病情。大量的采集圖像表明,[18F]S-16能夠與患者腦中的Tau蛋白特異性結合,并且同[18F]FDG和[11C]PIB的核醫學影像信息相對應,有效實現了Tau相關疾病患者與健康對照組的區分。同時,該探針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倫理委員會的批準,進入臨床I期探索實驗階段(ClinicalTrials.gov ID: NCT03620552)。
此外,該系列探針熒光量子產率高,對Tau蛋白的特異性和選擇性好,作為一種商業化熒光染料替代免疫熒光染色方法,用于體外高靈敏度Tau蛋白檢測。
1.1.3咔唑、苯并咪唑類多環衍生物(T系列、[18F]RO-948和[18F]PI-2620) Kolb團隊利用體外病理學染色或放射性自顯影的方法對800個化合物進行篩選,發現多環類的化合物咔唑、苯并咪唑衍生物對Tau蛋白具有較高的親和力和選擇性。其中,化合物[18F]T807[26]和[18F]T808[27]是兩個有潛力的Tau-PET顯像劑。體外飽和結合實驗說明,探針對AD人腦勻漿中的Tau蛋白有良好的親和力和選擇性。此外,探針的初始腦攝取值較高,藥代動力學性質良好,滿足PET顯像需求。但進一步的研究結果表明,[18F]T808在體內存在嚴重的脫氟現象,無法進行臨床探究[28-29]。而大量的臨床結果表明,[18F]T807能夠清晰的標記出AD患者腦內的神經纖維纏結,有效區分AD患者和正常對照組。因此,2020年5月28日,[18F]T807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準上市,成為了第一個可用于臨床診斷的Tau蛋白PET類顯像劑。
然而,臨床數據表明[18F]T807也存在較為嚴重的非靶結合,主要是同位于紋狀體內的MAO-B結合。此外,在脈絡叢和黑質區域有明顯的非特異性結合,可能是作用于脂褐素等[23, 30-31]。因此,Roche公司在T807的結構基礎上,報道了一系列多環類化合物作為有潛力的Tau-PET顯像劑。通過化學修飾將N原子引入到核心芳環結構中,降低分子脂溶性,從而提高探針對Tau蛋白的選擇性,減少非特異性結合。其中,[18F]RO-948表現出良好的生物學特性和藥代動力學性質。初步的臨床前實驗表明,探針可以迅速穿過靈長類動物的BBB (SUV=1.1~2.0),并從正常腦組織中快速代謝。在人體的PET顯像中,探針可以特異性地與AD患者腦中的Tau蛋白結合,能夠有效區分正常對照組和AD患者。此外,對圖像數據進行分析,未觀察到非靶結合。更多的臨床試驗仍在進行中,已有的臨床數據表明,[18F]RO-948非常有應用前景[32]。
類似地,[18F]PI-2620也是在T807的結構基礎上進行化學修飾。根據報道,該探針可以識別不同Tau相關疾病中對應的4R和3R結構,例如進行性核上麻痹(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中的4R結構和皮克病(Pick disease)中的3R結構。此外,臨床實驗數據顯示,[18F]PI-2620在腦內與單胺氧化酶不存在非靶結合。更詳細的臨床評價仍在進行中[33]。
1.1.4苯并噻唑類衍生物([11C]PBB3) 2013年,日本Makoto Higuchi團隊利用體外熒光染色實驗篩選發現化合物的骨架長度和分子脂溶性會影響探針對Tau蛋白的選擇性。他們報道了一系列具有反式丁二烯橋鍵的苯并噻唑類衍生物(phenyl/pyridinyl-butadienyl-benzothiazole/benzothiazolium)PBBs[34]。該類化合物較長的分子骨架結構能夠提高探針對Tau蛋白的親和力和選擇性,其中PBB3具有高親和力(Kd=2.55 nmol/L)和良好的選擇性(50倍)。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一樣,[11C]PBB3的放射性自顯影結果表明,探針與人腦切片上的Aβ斑塊和NFTs均有結合。PET顯像結果顯示,與[11C]PIB圖像不同,[11C]PBB3在AD患者腦部的海馬區有明顯的放射性聚集,且濃集程度與AD臨床癥狀嚴重程度有很好的相關性。然而,[11C]PBB3存在明顯的光致異構化現象,探針的標記過程要求嚴格避光,此外11C核素的物理半衰期短,限制了進一步的臨床應用[21]。
為了克服11C短半衰期的應用局限,將18F核素引入PBB3的分子結構上,報道了[18F]PBB3作為PET類Tau蛋白顯像劑的生物應用價值。目前,新旭醫藥與上海華山醫院展開合作項目,共同推進[18F]APN-1607([18F]PBB3)的臨床階段的探索。
1.1.5氮雜吲哚類衍生物([18F]MK6240) 2016年,Merck公司建立一套完整的體外篩選實驗方法,通過高通量的構效關系篩選,并優化化合物結構,最終得到高親和力和選擇性的Tau-PET探針[18F]MK6240[35]。人體的PET顯像結果表明,[18F]MK6240可以有效區分AD患者、輕度認知障礙患者和正常對照組。此外,腦內性質穩定,無放射性代謝物產生,體內藥代動力學性質良好,并且沒有觀察到包括Aβ和MAO-B在內的非靶區放射性信號濃集[36]。
1.1.61,5-萘啶胺衍生物([18F]JNJ311) Janssen藥物公司利用高通量篩選的方式,報道了全新的基于1,5-萘啶胺類衍生物作為高選擇性的Tau蛋白顯像劑[37]。通過構效關系分析,最終確定Tau蛋白親和力和選擇性最好的化合物結構上吡啶基氮的位置、取代基的位置以及氟原子的位置,篩選得到了探針[18F]JNJ311。隨后,進行了一系列小鼠、大鼠及恒河猴的臨床前評估[38]。實驗結果表明,[18F]JNJ311具有良好初始腦攝取和藥代動力學性質,并且體內代謝穩定,血漿中的放射性代謝產物無法再次穿透BBB干擾腦中放射性信號采集。此外,腦部的PET圖像表明探針無非靶結合。綜上,[18F]JNJ311完全滿足選擇性的Tau-PET探針的要求,是一種有潛力的PET類顯像劑。
1.2 SPECT類分子顯像劑
相較于Tau-PET顯像劑,SPECT類顯像劑研發相對滯后,研發時間較短,臨床應用方面仍需克服許多障礙。目前為止,報道的化合物類型非常有限,標記核素也主要集中于I-125這種物理半衰期較長的核素(表2)。

表2 幾種典型的Tau-SPECT探針Table 2 Several Tau-SPECT tracers
1.2.1苯并噻唑衍生物 大量研究結果表明,以苯并噻唑為骨架結構的分子探針對β-折疊有很好的識別作用,但AD患者腦中Aβ斑塊也具有和Tau蛋白相似的β-折疊。Nicolette S.Honson團隊通過體外熒光競爭結合實驗(同Th-S發生競爭性抑制熒光強度),從7萬多個分子結構中篩選出苯基二氮烯基苯并噻唑(phenyldiazenyl benzothiazole, PDB)類衍生物,該類衍生物對Tau蛋白具有較高的親和力和一定的選擇性[39]。
2011年,日本京都大學Hideo Saji團隊對PDB結構進行修飾,并進行I-125標記得到化合物[125I]2.1,以期望能夠作為一種Tau蛋白SPECT顯像劑用于AD的早期診斷[40]。體外放射性自顯影結果表明,[125I]2.1能夠特異性地與AD患者腦切片上的NFTs結合,且與Tau蛋白的免疫組化結果匹配,但同時Aβ的免疫組化結果也表明探針可以結合AD患者腦切片上的Aβ斑塊。之后,在正常小鼠體內生物分布實驗中,雖然探針[125I]2.1表現出了良好的初始腦攝取值(0.94% ID/g),但60 min時腦攝取值升高,說明其放射性代謝產物在正常腦中存在嚴重滯留或隨血液循環再次進入腦內,這對臨床應用非常不利,無法從影像學圖像上區分病患和正常對照組。
1.2.2苯并咪唑衍生物 由于PDB類衍生物脂溶性較高,其體內的藥代動力學性質不盡如人意。因此,Hideo Saji團隊又報道了一系列苯并咪唑類化合物,通過將苯并噻唑替換成苯并咪唑來降低化合物的脂溶性,同時,去掉重氮結構減少化合物的生物毒性,篩選得到了化合物[125I]SBIM-3[41]。盡管化合物的初始腦攝取值和腦部的藥代動力學性質都有了明顯改善,但探針對Tau蛋白的親和力和選擇性大大降低,阻礙了探針的進一步應用。
2015年,Hideo Saji團隊再次修飾了苯并咪唑的骨架結構,篩選得到了性質更為優良的探針[125I]2.2[42]。去掉分子結構中的N,N-二甲氨基部分,以提高分子探針對Aβ斑塊的選擇性。放射性自顯影結果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表明,[125I]2.2在顳葉有明顯的放射性沉積,與Tau蛋白在AD患者腦內的沉積情況相對應,然而在Aβ蛋白沉積的對應位置,也觀察到了大量的放射性信號。這一結果表明,盡管化學結構的修飾改善了探針的親和力,但較差的選擇性仍是該類探針急需解決的問題。[125I]2.2表現出了良好的藥代動力學性質(2 min腦攝取值為3.69%ID/g,60 min腦攝取值為0.06%ID/g)。此外,該系列化合物存在較嚴重的光異構化問題,這使得探針難以應用推廣。
1.2.3硫代乙內酰脲(thiohydantoin, TH)衍生物 2011年,Hideo Saji團隊對硫代乙內酰脲(thiohydantoin, TH)結構進行化學修飾,報道了[125I]TH2,該探針表現出對Tau蛋白較高的親和力(Ki=64 nmol/L)和一定的選擇性(7.3倍)[43]。并且神經病理學染色表明,該探針可以特異性結合AD患者腦切片上海馬部分的NFTs,體外放射性自顯影和免疫染色結果也進一步表明了其對組織切片上NFTs的親和力。但和PDB衍生物的問題相同,較高的分子脂溶性使得探針的藥代動力學性質不盡如人意。此外,探針的親和力和選擇性也需要進一步優化。
1.2.42-苯基喹喔啉衍生物 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崔孟超團隊報道了一系列99mTc標記的以亞氨基二乙酸二乙酯(diethyl iminodiacetate, IDA)為螯合配體的2-苯基喹喔啉類Tau蛋白分子探針用于AD的早期診斷[44]。其中探針[99mTc]2.3展現出與Tau蛋白的高親和力(Kd=(59.95±2.56) nmol/L),以及對Aβ聚集體的選擇性(20.3倍)。體外放射性自顯影結果進一步證明,探針能夠特異性與轉基因(Tau)小鼠和AD患者腦切片上的NFTs結合且對Aβ有很好的選擇性,該結果也得到了Gallyas-Braak染色的證實。在正常小鼠的體內生物分布研究表明,盡管[99mTc]2.3可以穿過BBB并且快速從非靶腦區清除,但是較低的初始進腦量使得探針不具有進一步生物應用的價值。綜上,喹喔啉衍生物的骨架結構使得分子探針對Tau蛋白具有良好的親和力和選擇性,但99mTc標記探針的穿透BBB能力和體內藥代動力學性質成為這一類SPECT顯像劑開發的重要瓶頸。99mTc標記配體類型的選擇以及相對分子質量大小的設計可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
2 總結與展望
2018年,美國老齡化研究所和阿爾茨海默病協會共同發布的以生物標志物A/T/N為研究框架的診斷指南,為AD的臨床診斷及病理學發展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45]。此時,[18F]T807作為首個進入臨床診斷的Tau蛋白顯像劑為AD的確診提供了重要參照。然而,臨床結果顯示明顯的非靶結合干擾了臨床醫生對于結果的準確判斷,因此開發高親和力和選擇性的Tau蛋白顯像劑成為了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在未來的5~10年,新型Tau蛋白顯像劑的研發及臨床實驗的開展尤為重要。
對于PET類Tau探針來說,發展時間相對較長,分子庫結構類型豐富,體內生物學性質良好,但仍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一代Tau探針臨床數據顯示,嚴重的非靶結合(如MAO, Aβ等)是臨床診斷應用的瓶頸,但能夠篩選出對Tau蛋白具有高親和力的分子結構,進一步的化學結構修飾也是突破應用瓶頸的方法。二代探針在提高親和力和選擇性的同時,有效降低了非靶結合,提高了顯像劑的藥代動力學性質和體內穩定性。但由于研發時間較短,許多臨床實驗數據不足,仍需要大量的橫向和縱向研究來進一步探究臨床診斷的可靠性。
此外,目前Tau-SPECT顯像劑的開發相對比較滯后,但是SPECT類核素制備簡單、方便且價格低廉。因此開發特異性好選擇性高的Tau蛋白顯像劑將成為熱點,同時SPECT類顯像劑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提高初始腦攝取值,改善分子藥代動力學性質等。
在新型Tau選擇性探針的開發過程中,化合物的篩選要綜合多種生物評價手段,注重數據結果的綜合考察。此外,Tau蛋白顯像劑的開發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體外的蛋白實驗并不能很好的模擬患者腦內的真實情況,且病理性的Tau蛋白在腦內的含量較低,這對探針的親和力和選擇性都有很高的要求。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Tau相關的疾病還包括很多種,由于病理狀態下Tau蛋白的表達表型不同,使這些疾病表現了不同的臨床癥狀。腦內的病理狀態Tau蛋白除了神經纖維纏結的形態外,還存在ghost tangles(GTs)和neuritic plaques(NPs)等形態特點[46]。這要求設計顯像劑時,還需考慮不同病理學狀態下Tau蛋白的類型(3R, 4R),Tau蛋白沉積形態(NFTs, NPs, GTs),細胞環境狀態(神經細胞,膠質細胞)等因素[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