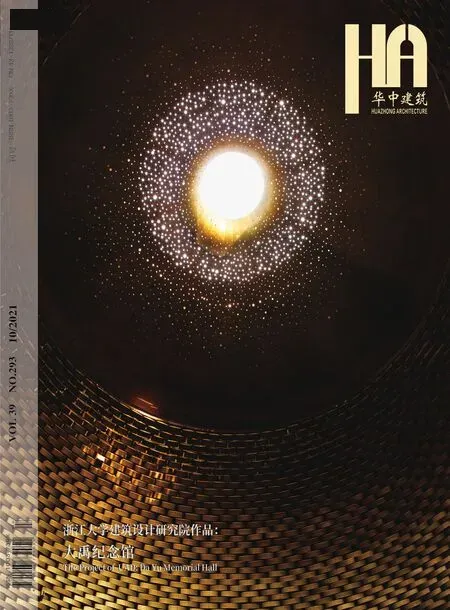世俗中的神圣:傳統民居中隱性空間探析
袁曉蝶 | Yuan Xiaodie
石若利 | Shi Ruoli
張 軍 | Zhang Jun
“隱性空間”最初是心理學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對視覺、聽覺、嗅覺等的空間體驗,是觀眾通過思維活動創造的一個全新的虛擬空間[1]。“隱性空間”研究的發展與環境行為學、知覺現象學、建筑現象學以及心理學中的意識研究是相輔相成的。本文的“隱性空間”是指在傳統民居建筑中普遍存在的、與信仰緊密相聯的空間,它隱于顯性的物質空間之后,是與神靈進行溝通的中介性空間,具體指與宗教信仰、原始信仰等相關并能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構建出來的情感性空間,如火塘、經堂等,往往與顯性的物質性空間共存,世俗與神圣共生。
1 研究背景
對中國知網中2000年—2020年以“傳統民居”或“民居建筑”為主題的核心期刊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從其關鍵詞的出現頻次統計中可知,“節能”、“能耗”、“節能改造”、“圍護結構”、“抗震性能”、“建筑節能”、“自然通風”“熱環境”等側重傳統民居顯性空間方面的關鍵詞出現頻次較高,而側重傳統民居隱性空間的關鍵詞較少且出現頻次較低,如“傳統文化”、“地域文化”、“文化”、“文化內涵”等。
在傳統民居的顯性空間研究方面,黃志甲從居住的舒適性出發研究總結出建筑內部空間的物理環境特征[2];徐一品則從熱工性能和耐候性能方面對民居進行了立面上的分析[3];吳迪針對特定地區的民居建筑能耗進行分析并確立了一整套技術流程[4];黃海靜針對傳統民居室內采光的問題進行量化分析,并提出了傳統民居光環境的優化策略[5];何泉結合傳統技術,對現代生土建筑設計和營造方法有所研究[6]。這些基于傳統視角的研究側重于物質環境與技術方面,對于民居建筑的社會文化環境關注不夠。
在傳統民居的隱性空間研究方面,羅晶探討了文化影響下傳統民居的形態變遷[7];周易知對江南傳統民居中“堂前”、“坐起”兩個空間的布局與文化內涵進行了研究[8];巨浪以人類學的視角探討了藏族民居建筑的空間布局和結構特征[9];張雪梅則以宗教學的角度對信仰影響下的中國西部鄉村聚落和社區形態進行研究[10]。蔣高宸教授分析總結了云南少數民族民居建筑的類型與空間特征并挖掘其文化內涵,對建筑發展歷史規律進行了科學性的認識[11];楊大禹、翟輝則對云南傳統民居的文化傳承和更新做了探討[12];楊宇亮、袁曉蝶則以信仰的維度對藏族聚落及民居空間進行分析[13-14]。目前,學界對傳統民居的社會文化方面有一定研究,但多是僅以宗教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進行探討,缺乏建筑學領域對于空間的分析。
綜上,對傳統民居的既有研究聚焦于建筑中顯性的物質空間,較少以信仰的角度對民居中隱性空間的特征和形成機制展開研究。本研究以建筑學、城鄉規劃、人文地理學和宗教學的多學科研究視角對傳統民居隱性空間的空間特征和形成機制進行研究,具有較好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圖9 寶山石頭城民居建筑內部實景
2 傳統民居中的神圣空間與成因
2.1 一般空間特征
(1)神圣與世俗的兩分
宗教信仰地區的聚落空間格局主要是以宗教建筑物或構筑物為聚落的中心或重心,進而衍生出日常性的生活空間,形成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兩分的空間特征。具體在傳統民居中,神圣空間主要指與宗教信仰、原始信仰緊密聯系的空間,如燒香臺、中柱、經堂等;世俗空間主要指與日常生產、生活相聯系的空間,如臥室、儲物間、陽臺等。在傳統民居空間中,神圣空間往往占據著空間格局的核心,而世俗空間則退居次要地位,成為附屬性空間,由此,傳統民居空間構成了神圣與世俗兩分的世界。
(2)神圣與世俗的共生
滇西北地區擁有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人神共生”作為該地區人居環境的一般空間特征[15],普遍存在于宏觀尺度的山水格局、中觀尺度的聚落和微觀尺度的民居中。“人神共生”的空間特征,在傳統民居中主要表現為世俗空間與神圣空間相伴相生的特征,也即“人神共居”的特征。具體在傳統民居中,神圣空間更多地承載著人們誦經禮佛禱告等信仰活動,世俗空間更多則是承載著起居會客等日常活動。人作為既高級又普通的動物,日常生活空間是人最底層的需求,而信仰空間則是人性更高層次的需求,兩者相互影響、相伴相生。
2.2 形成機制
(1)內部矛盾:對信仰的渴求
人是唯一具有高級思維和自我意識的動物,面對生存與死亡,只有人會深刻思考其價值問題,并力求通過某種途徑尋求到一種終極關懷。這種終極關懷在很大程度上與信仰相聯系,其實現途徑便是宗教。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欲求這一矛盾體是人必然面臨的痛苦之源,而關注彼岸世界的宗教信仰恰可幫助人們戰勝痛苦,到達彼岸世界,得到精神上的解脫[16]。故此,信仰是人內心的無限渴求,它在世俗與神圣、物質與精神、此岸與彼岸之間給人以生命的價值。
(2)外部矛盾:惡劣的物質環境
滇西北位于青藏高原的東南邊緣地帶,其高山峽谷眾多,海拔高差大,氣候高寒,垂直地帶性特征顯著,溫差大,含氧量低,自然地理環境十分惡劣。即使滇西北的自然環境對于民居的形成和空間特征等有較大的影響,但終究不是必然因素。在滇西北地區,當基本的物質條件難以得到滿足時,人們會轉而將自己的注意力投放于精神世界,用富足的精神世界去填補物質世界的空缺。此時,信仰便成為影響人及其周圍環境的重要因素。
3 滇西北傳統民居“隱性空間”的空間特征
3.1 藏族民居
《后漢書》所言:“壘石為室,高者至十余丈,為邛籠。”邛籠,即為碉房,在滇西北地區的藏族民居中是最主要的建筑類型。在藏族民居中,源于宗教信仰的“隱性空間”也普遍存在,并與顯性的物質空間共存。
藏族是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藏傳佛教是其主要的宗教信仰。在藏傳佛教中,理想世界的圖景是一個壇城,認為世界是由中心的須彌山作為支撐,再以日月星辰圍繞。跟隨須彌山可以到達神靈居住之所,故高處、上方是尊貴之處,在藏族聚落中,寺廟、宮殿等往往位于地勢的高處。世界圖景是民居隱性空間產生的內在邏輯,在藏族民居中,也普遍存在著與世界圖景聯系的隱性空間。
龍雙村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支巴洛河北岸(圖1),是一個典型的藏族傳統村落。整個村落坐落于河谷的山前沖積扇上,總體地形北高南低,平均海拔1980m,年平均氣溫10℃,以種植業為主。全村共有83人,全部為藏族,故其民居建筑具有典型的藏式特色。該村的建筑多為兩層藏式民居,以高低錯落的方式布置在臺地上,墻體厚實且自下而上有明顯收分,使得整棟建筑顯得穩重敦實。負一層為牲口圈,在房屋的兩面分設出入口。地上的兩層是最核心的生活空間與信仰空間,分別有堂屋、廚房、儲藏室、臥室和經堂等。

圖1 龍雙村衛星影像
堂屋可供多人在一起聚會、吃飯、睡覺,節日時甚至還可圍跳鍋莊舞。占據堂屋最中心位置的是一對雙中柱(有些民居為單中柱),柱身粗大,且有一定的裝飾物。在藏族文化中,中柱象征世界圖景中的須彌山,是溝通天地人神的通道,在筑屋時都要挑一根粗大的柱子作為中柱,且中柱明顯要比屋內其他柱子粗,還要用五彩帶、哈達、紙花等作為裝飾。即便中柱在建筑結構上沒有任何必要,或是其體量遠遠超過了結構受力的要求,藏民在建造時還是會保留,甚至是越來越大。此時的中柱已不僅僅是建筑結構的一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的體現,是人們信仰的象征。火塘一般靠墻并正對雙中柱布置,形成一個明顯的軸線關系。火塘周圍的空間不僅是藏族人吃飯、睡覺、聚會的世俗空間,更是一個神圣的信仰空間。火對于眾多少數民族來講都具有生存、希望的神圣意義,火神也處于藏傳佛教的信仰體系之中,而火塘作為火神的載體,亦是尊貴而神圣的。
民居的二層房間主要是用作經堂、臥室和廁所(圖2)。這一層的空間很少被主人使用,只有念經或者當家中有尊貴客人或者喇嘛來時才會使用,這也體現出了藏傳佛教世界圖景中以“高”為貴的觀念。經堂是藏族民居中最神圣的禮佛空間,內部裝飾有各種佛像、經書、唐卡等,極盡華麗,與簡樸的臥室空間形成鮮明的對比。對于經堂的內部裝飾,藏民往往愿意投入大量資金,使這一神圣空間在整個民居中具有強烈的異質性,成為其理想世界圖景中彼岸的象征。一般而言,從外立面來看,經堂的開窗最大,且裝飾有充滿藏族元素的精美窗套,具有很強的可識別性(圖3)。經堂的內部空間一般較大,有精美的梁柱雕飾,并在正對門的墻上供有佛像,在側面的墻上放置經書或掛置唐卡。經堂是藏民家中最重要的信仰空間,即使在建房期間沒有固定的經堂可供使用,藏民也會搭建起臨時性的房屋作為經堂,待房屋建好后將經堂裝飾得極盡華麗再開始使用,足以見得藏民對于經堂空間的重視。

圖2 龍雙村民居建筑平面圖

圖3 龍雙村民居外觀
3.2 傈僳族民居
分布在滇西北地區的傈僳族普遍信仰原始宗教,它認為萬物有靈,自然界的任何一物都被賦予了靈性,遭遇疾病或災害時,通常會以牲口祭祀。近代以來,大量傳教士進入滇西北地區進行傳教活動,基督教和天主教也由此傳入該地區,由于其教義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有很好的契合,部分傈僳族民眾也開始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
同樂村,位于云南省迪慶維西傈僳族自治縣葉枝鎮,是滇西北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傈僳族傳統古村落。其地處高差極大的瀾滄江東岸坡地上(圖4),共有123戶人家,564人,是當地村民口中的“同樂大寨”或“海頂”[17]。

圖4 同樂村整體風貌
同樂村民居多為兩層建筑,一層為牲口圈,二層為人的生活空間(圖5)。建筑內部空間布局極其簡潔,只有一大一小兩間屋子,小屋為儲藏室,大屋則為集吃、住、休息為一體的多功能空間,類似于藏族的堂屋。其中,火塘占據了堂屋的中心位置,門正對火塘,床、桌、柜子等都四散于周圍,各項活動也都圍繞火塘展開。整個堂屋空間沒有窗戶,在還未通電的年代,火塘就成了屋內唯一的光源,即便如今家家戶戶開始用上了電燈,但微弱的燈光遠不及火塘明亮耀眼,此時以火塘為中心的隱性空間就成為了建筑內部最具神圣感的所在。

圖5 同樂村民居建筑二層平面圖
3.3 納西族民居
納西族人信仰東巴教,并有著濃厚的自然崇拜和鬼巫崇拜的色彩,在自然認知的基礎之上,逐漸形成了納西族的世界圖景,即“三界五方”。三界代表天上界,地上界和地下界的縱向空間格局,五方代表以神山居那什羅或稱花珠山為中心,以白銀山、黑鐵山、綠玉山、和黃金山各為東西南北位的平面空間格局。其“三界五方”的理想世界圖景在納西族傳統民居中也有所體現。
寶山石頭城是一個納西族的傳統聚居地,位于金沙江流域的高山峽谷之中(圖6),距離麗江110km。由于上百戶的納西族居民聚居于金沙江岸邊一座獨立的巨石之上(圖7),石頭城由此得名。其所在巨石面為三角形,其中兩邊是懸崖絕壁,另一邊石坡向金沙江傾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一處建城的寶地。城內民居鱗次櫛比、古樸自然,巷道蜿蜒崎嶇、縱橫交錯,令人嘆絕。城中的石頭房子是最古老的建筑,承載著當地人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其內部空間也體現著信仰對于納西族人的影響。

圖6 寶山石頭城外部空間關系圖

圖7 寶山石頭城整體風貌
寶山人的石頭房子極為簡樸,建筑平面僅有一層,建筑內部沒有明確的空間分隔,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共存于此(圖8)。其中,“蒙杜”—火塘—“格咕魯”的空間組合是納西族傳統民居空間的核心,此處的“蒙杜”指中柱、“格咕魯”指神龕[18]。這一信仰空間組合成為納西族民居的統一空間格局,成為內部空間布置的定式,彰顯著其民族文化與精神內涵。

圖8 寶山石頭城民居建筑平面圖
在石頭房子的內部空間中,中柱—火塘—神龕的空間組合有明確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的導向。中柱一方面起到了建筑結構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承載著人神溝通的媒介功能。中柱位于房屋的中心位置,雖不如藏族民居的粗壯,但裝飾有動物羽毛等物件后,便被賦予了神圣的意味,在納西族人的空間圖式中中柱上通于天上界、下達于地下界,支撐起了整個宇宙空間,而人則居于其間的地上界。火塘在各個少數民族民居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麗江的納西族住屋中,火塘是日常生活和社會性活動的中心。初建火塘時,要擇吉日舉行升火儀式并祈禱火永遠不會熄滅,保佑主人居住平安。納西族傳統民居一般都會使用高腳火塘,在其周圍分設男女床鋪,平時的餐飲、議事、娛樂、禮儀活動等都在此處進行。神龕通常會設置在房屋墻內的一角,當地人稱之為“格咕魯”。神龕往往祭祀著祖先神靈,納西族人每天用餐前都必先祭獻,可見其虔誠的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由此,中柱—火塘—神龕的空間組合就成為了整個住屋的核心區域,它不僅是可供日常生活需求的顯性空間,更是溝通人與神靈的隱性空間。
3.4 小結
在滇西北藏族、傈僳族、納西族的民居建筑中,都存在著有一定象征意義的隱性空間,它們以不同的形式時刻影響著人們以特殊的方式認知世界,形成自身特有的世界觀。這些隱性空間總是內藏于心、外顯于物,成為少數民居傳統民居空間中的重要內容。
4 結論
4.1 隱性空間在傳統民居中普遍存在
“隱性空間”不僅僅存在于某一民族的民居建筑中,更是在各民族民居建筑中廣泛存在,并且具有較長的發展歷史,在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上都具有廣泛性。滇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眾多,由于其宗教信仰各不相同,“隱性空間”在滇西北少數民族民居中的空間特征表現出總體一致、局部微差的特點。
4.2 不同民族的理想世界圖景影響著各自的民居空間
理想世界圖景是人們對于內心所向往的世界觀、生活方式的再現。傳統民居與聚落相似,其空間特征表達了該民族“理想世界”的圖景,而不同民族有著各自獨特的宗教信仰,這就決定了理想世界圖景各有其側重點,具體在傳統民居中則表現為各自隱性空間的差異性。藏族的經堂、傈僳族的火塘以及納西族的中柱—火塘—神龕空間組合,同作為隱性空間卻各有其特殊性。
4.3 “信仰”是傳統民居的重要研究維度
信仰,作為人類基本的精神需求,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崇高性。它回答了諸如“人生”這類終極問題的思考,以信仰為中心的“隱性空間”也因此普遍存在于各民族傳統民居中,不同程度地影響建筑空間布局。在既有的傳統民居研究中,偏重“器物”層面的物質空間已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注重“精神”層面的文化空間的研究還稍顯不足。“重功能導向,輕文化因子”成為了當前建筑學研究的一個普遍問題。而以信仰為傳統民居的研究維度,一開始就把人這一復雜性動物置于研究的中心,圍繞人性本身來對民居空間進行探討,更全面地解讀民居空間的生成機制與發展演變,將拓展傳統民居的研究視野,豐富傳統民居的研究內容。
資料來源:
圖1:谷歌衛星影像;
文中其余圖片均為作者自繪或自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