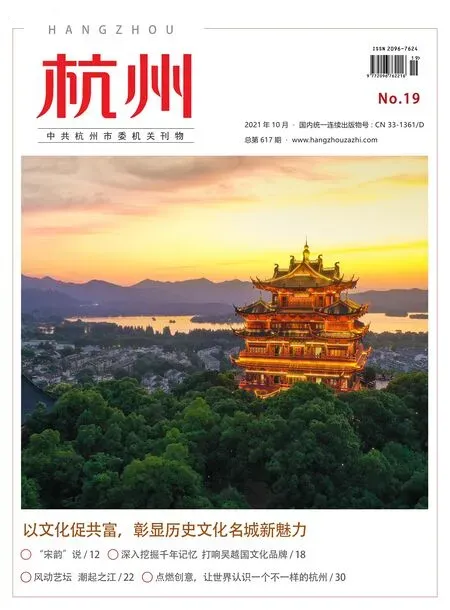《紅樓夢》中的悲秋, 與手部脂肪缺失有關

很多人感懷歲月,都在同一個層面上——同齡人的去世,記憶力的衰退,兩鬢初染秋霜,牙齒的松動,眼的昏花,所謂星轉斗移,物是人非,是矣。
很多人感懷歲月,也有在另一個層面上的——悲的,中年喪妻,老年失子;喜的,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世百態,莫衷一是,所謂悲也是喜,喜也是悲,是矣。
還有人感懷歲月,卻在很隱私、很離奇、很富歧義的一隅,如,川端康成的看到蛾的自毀與蟲的化蝶,想到死亡;曹雪芹的見及海棠與雪,等于見及了擬人的空和擬自然的肥美;以及馬爾克斯說的“空房子就是夢的連接處”和博爾赫斯的說“三條歧路中必有一條受命于命運”,等等。
友人送我一文集,上有川端康成的《花未眠》,川端在那上面說,有一年歲暮,他在京都觀晚霞,突然想起了田中長次郎制作的稱之為夕暮的名茶碗,這只茶碗的黃色帶紅釉子,的確就是日本黃昏的天色。
比利時人菲茨伯特,是個生物學家,他對世界的貢獻幾乎可以說就是像MBA教程那樣,用生物學實例來解釋文學個案。比如,他認為:中國名著《紅樓夢》中眾人物的悲秋情緒,都與這些女子“手部脂肪缺失導致的白皙程度不夠與觀感單調”有關——他說:“處于亞熱帶的中國沿海,秋季受東亞季風影響,多秋高氣爽的天氣,雨水少,蒸發大,因而容易發生裸露的手部與臉部的水分缺失,繼而導致肌膚肥腴度的不夠和觀感的單調……”
他認為,中國人有句名言叫“一葉知秋”,不過,那是男人的感懷,不是女人的;與男人感懷對稱的是,男人感懷的往往是“天”,女人感懷的往往是“手”;男人于天感懷的是政局,女人于手感懷的是姿色;男人于天感懷的是政局之始末,女人于手感懷的是姿色之春秋——他說:“歐洲近十年來,隨著女性對護手油的需求激增,意味著女性對政治與經濟的關注度日益減少以及對家庭關注度的正在加強。”——這,也正好說明了“手”是感懷歲月老去、姿色不再的觸體。
也就是說,有些人感懷歲月,就是通過人對自身身體的感懷和身體置于某個場景中被參照的感懷——譬如樹梢、荷葉、蕉株中的“朝露”,感懷人的生命短促與“去日苦多”;譬如公交車特定的報站聲與行駛中車體哐哐的撞擊聲,感懷城市特有的馬路情結與短時間的人群變幻;譬如海棠、君子蘭、藜蘆肆無忌憚的肥厚,感懷周一的寫字樓恐懼癥以及腹部日益茂盛的贅肉;譬如一只自由傲慢的爬行動物,感懷瞬間的職業壓迫與婚姻曠日持久的無趣,等等。
前不久,路遇一少時的玩伴,他說:“還記不記得,當時你舉著一支菖蒲的劍,站在橋上,大聲高喊‘上下求索與‘吾生吾世?”我說:“不記得了,不記得了。”他又說:“當時,你即將赴邊陲,我即將去南疆;你在逢人打聽哪里有帆布的一人高的大袋子可買,我則在搜羅所有可讀的印刷物……羅曼·羅蘭、杰克·倫敦、狄更斯、曹雪芹、湯顯祖,都在搜羅之列。”我說:“啊呀呀,也不記得了。”少頃,他又說:“人如蜉蝣,朝生暮死;人有時都不如蜉蝣,終日無所事事或終日魂不守舍。”我連說:“是的,是的。”繼而無限感慨。
現在想來,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人能看著自己的手說:“宇宙之大,生機勃發;生命之小,垂垂老矣。”這人就是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的作者;世界上大概也只有一人能窺見植物要脫離時間和土地的不安分的靈魂,并把它畫了出來,這人就是文森特·梵高,畫11幅《向日葵》的那個人。
梵高將向日葵的歲月,感懷成了自己的命運,其實梵高是通過葵花的表情看到歲月的表情的,所以,我們被稱之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東西,在梵高眼里卻是一種憤怒、抓狂甚至窒息。